一一四十年前的另类回顾
其二,民主墙失败的原因
民主墙失败了。责任是多方面的。
一、首先,我当然要批评以邓小平为首的所谓改革派。取缔民主墙无疑是他们犯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戊戌维新不遭镇压,清朝的改革就可能成功;戊戌维新既遭镇压,清朝的改革就注定不能成功。……事到如今,中国社会是危机重重,面临着崩溃解体的巨大威胁。这对于中国人民是灾难,对共产党自己何尝又不是灾难。中国共产党已经失去了自我改造(变为社会民主党)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中国不改革是不行的,也是办不到的。然而,当年荣禄禀告老佛爷的话“改革能救中国,救不了大清”,是不是已经适用于共产党了呢?当然,如果中共领导人并不关心民族,并不关心明天,他们一心一意追求的不过是昔日毛泽东的那个无限权力,如果他们抱定了“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的心理,那么他们做的一切就都是对的。我不想对他们多加批评,因为这种批评太容易了。
二、我要批评那些具有自由民主倾向,但当时未能有力支持我们的人。本着春秋责备贤者之议,我不能不为他们当年的失误深感遗憾。有人说,民主墙不值得重视,因为参与者没什么名人。这刚好把话说反了,我们不能责怪民主墙的参与者不是名人,我们要责怪的是那些名人为什么不去参与民主墙。请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众多的有名气、有地位而又热爱自由民主的人们,当时能出现在民主墙下;如果他们的用心之作都发表在民间刊物上,民主墙地位又将是如何?民间刊物的命运又将是如何?既然一小批当时藉藉无名的热血青年尚且能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机中,把民间刊物这个自主的阵地创造出来并且维持了长达一年以上,那么我们就该相信,凭借着一大批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投入,这块独立自主的阵地就完全可以巩固下来,最终演变为民主运动的可靠基地。这里并没有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危险,而危险又总是和影响、声势、规模成反比的。他们缺乏的主要不是勇气,而是见识。
不错,借助于官方给予的位置,借助于现成的官方言论阵地,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更广大的名声,你可以使自己的思想更迅速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但是,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要真正获得独立,倘若中国要真正实现自由民主,我们就一定要放弃这种“搭便车”的思想,宁肯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地走路。独立自主是要付出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使你不能迅速地成功成名。所以,索尔仁尼琴要说:“要做一个独立的人,需要的条件是太多了!”
有人说,在大陆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人要想成功成名,要想做一些好事,甚至包括你想更有力地去争取自由民主,你都必须进入既成的权势集团才行。不对,要知道,那正是极权制度给你设下的诱饵和陷阱。我们的责任正是要去改变它而不是去适应它。唐太宗在视察考场时说过一句很得意的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矣!”科举制下的知识分子,建功立业的捷径是去科考做官,否则只好当一名隐士与草木同朽。其实,要是有稍多一些人硬是不去考那个试,做那个官,皇帝不可能把大部分天下之才网罗在自己手下,他也就不可能长久地垄断全部政治领域了。更何况,古代的隐士还可以凭诗文传世,极权统治下的人要想立言,似乎也非要经过党的过滤。那为什么不去努力冲破这种约束呢?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着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我们真的都是鱼吗?当时机不允许的时候,选择那种借用官方规定的方式去活动,或许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然而,当我们有了开创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机会时,我们却不去开创它,而依然热衷于借助官方规定的方式活动,那就是愚蠢的过错了。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总是在循环而绝少突破,原因就在于:即使到了可以选择的关头,太多数人仍然愿意走老路。我要强调的是,1978一1979年间分明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惜大家没有充分地把握它。
前面说过,官方刊物信誉扫地是民间刊物应运而生并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官方刊物的信誉回升会造成对民间刊物生存的巨大威胁。让官方刊物有更宽的言论尺度,正是逼死民间刊物最巧妙的一招。一旦官方刊物能发表不亚于民间刊物的尖锐文字,谁还会对民间刊物格外关心呢?在那段期间,官方刊物越办越好,这使民间刊物处于两难的困境:如果你要提高你的尖锐性,你会赢得读者,但会失去安全;如果你不去提高你的尖锐性,你会保持你的安全而失去读者。可是,失去舆论的普遍关心,意味着失去民众的保护,到头来仍然会失去安全。毕竟民刊的参与者人数不多,他们不足以自己保护自己。他们必须吸引民众的广泛注意,那是弱小者唯一的自卫手段。由于官方刊物日益夺走了市场,民刊的生存日益孤立。在民主墙民间刊物初起之时,它几乎是北京等大城市关心政治的人们的共同的热门话题。然而,到了最后一份民间刊物《责任》被封闭,王希哲、徐文立等若干人被捕时,连最敏感的首都知识界都很少有人知道,更谈不上引起普遍的异议了。民间刊物的最终消失几乎是无声无息的,因为广大民众在此之前许久就对它不大关注了。结果,唇亡齿寒,在民间刊物被取缔后不久,官方刊物就收紧了。
1979年夏天,政治气候似乎转暖。说来有趣的是,在那些较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中,愿意参与我们搞民间刊物的人极少,而劝说我们抛开民间刊物而在官方刊物上发展的倒不少。他们说,既然你们能在民刊上说的话,略加修改后在官刊上也可以说,何必还要在那里惨淡经营呢!……我提醒说:越是民刊看来没必要的时候(那意味着官刊的言论较开放),我们越是要关心和加强民刊的存在地位。否则,等到民刊消失后,官刊的控制又再度加紧,人们要重新恢复搞民刊就更困难了。不过在当时,考虑到这一点的人很少。
三、民刊参与者自身也不是没有弱点的,他们的弱点基本上是在策略上而不在原则上、方向上。大多数参与者对当时形势的特点缺乏冷静而周详的思考,对我们在现阶段的基本目标没有明确、准确的共同认识。虽然大家都从事开创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英勇努力,但是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自觉意识。大多数人并没有把开创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这件事本身当作我们当时奋斗的主要任务。一个缺乏牢固地基的建筑是经不起风暴袭击的。
我在民主墙期间写的文章,几乎全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一一言论自由。自从1970年我完成了自己的思想转变后,我所苦苦思索的问题就不再是什么是民主自由,什么是极权专制,不再是对现实中各种丑恶现象的批判,而始终是集中于一点:那就是,我们怎样才可以摆脱极权统治?我们将有什么样的机会?我们应当从何处取得突破?我在民主墙所作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在那三年前准备好的。我相信,在历史提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面前,我们有可能做成两件事:一是让言论自由的原则深入人心,使之成为普遍的共识;二是让民办刊物这种形式巩固下来。这样,我们就好像是下围棋做成了两个眼,从此赢得了一片自主的活地。政治,在我看来,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而是我们要先说些什么,先做些什么。
我在《论言论自由》和《论同仁刊物》两篇长文中,尽可能地阐述了我的思想。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民主墙朋友和读者,包括一些党内高层知识分子的赞誉。但可惜的是,对我在文章中透露出来的战略设想,读懂者寥寥无几。……一般人显然更关心的是那些披露了若干小道内幕的文章,是那些批评更直接、更尖锐的文章,是那些提出了某种特殊概念、惊人论点的文章(我一向主张在论据上下功夫)。我和民主墙的朋友也曾有过一些讨论,不过,等到有较多的人开始接受我的想法时,那已经是民主墙被封闭之后了。……到了1986、1987年,争取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新间自由)成为大学生游行的最主要的口号,许多知名的理论家也主张应把争取言论自由作为争取民主的第一步,我并不感到特别受鼓舞。因为我认为,赢得这种自由,也就是创造这样一种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间的最佳时机已经不可挽回地过去了。……
不结束语
要讲清楚民主墙的历史,那需要不止一本专著。十年来中国民主运动的进程,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参与者,是不可能了解清楚的。在专制机器依然控制了一切传媒的情况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被隐没不彰!直到今天,一般人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又知道些什么呢?有些人也许掌握了比如民间刊物的全部文章,但是,他能知道在文章背后发生的事情吗?他能读懂这些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作品吗?我们不能迷信历史。因为历史学家只能知道实际出现的事情,很难知道可能出现的事情。而人生、政治,却正是可能性的艺术。
让我们紧紧抓住现在吧,趁未来还是有可能性的时候。
1988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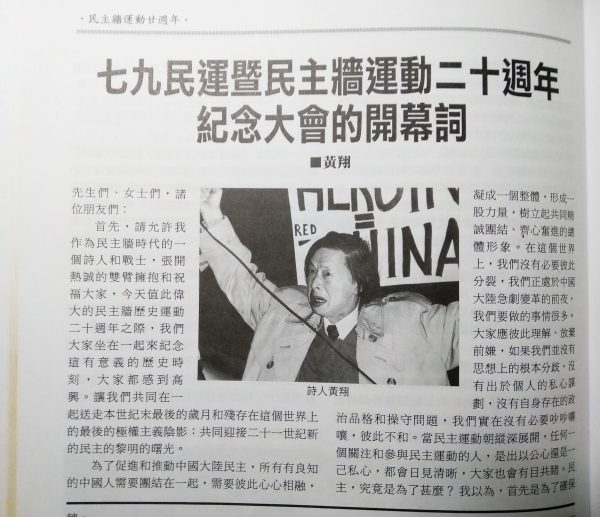
(荀路摘录于2018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