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房龙的大作《宽容》,写了三篇名为“什么才是‘宽容’”的读书笔记,觉得言犹未尽,又把《宽容》浏览了一遍,有些章节反复研读,甚觉精彩,于是再接着写起来。
《宽容》一书在封一向读书介绍道:“人类从远古中走来,一心要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然而,在无可奈何的叹息声中,他们不得不面对眼前的粗陋不堪。怎样拯救这个世界,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一宽容。《宽容》是一部人类思想的解放史,它以犀利的笔触勾勒出了人类思想的嬗变轨迹,清晰地呈现了人类心灵深处的隐秘世界。”
非常赞同以上评语。思想宽容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既是宽容的对象,也是宽容者。纵观人类历史,宽容产生思想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也需要宽容。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多样性会导致思想混乱,进一步引发社会动乱,只有与论一律、思维整齐划一才能消除纷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类大同的理想世界。
可惜,人类历史上至今没有出现这种万众一心的社会现象。有这种思维的人不妨冷静地想一想,应该按什么人的标准来统一人的思想?是你的,还是我的?是本国伟大的领袖,还是外国英明的导师?估计这世上谁也不愿意只能说别人允许说的话,写别人允许写的文章。没有人会甘愿被别人强制,谁也不愿意做学舌的鹦鹉,也不乐意当被人操纵的傀儡。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吊诡的是,尽管谁都认为“我”不应该被人管制思想,但有的人却又认为“人”的思想应该“统一”。
在房龙看来,宽容是对所有的“我”的一视同仁。宽容意味着人成其为人,而不是任何权贵的奴仆,每个人都不会因为自己的思想见解不同于统治阶层而受到压制、歧视、迫害。宽容就是每个人都能抛去心口不一的伪装而回归本性;宽容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像神只一样接受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凡夫俗子。
那么,人类怎样才能实现理想中的宽容呢?房龙对此感到为难。他尝试用如下文字来表达他的思路。
我可以列举一些以公平和正义的名义犯下的、实际上却是不宽容导致的恐怖罪行。
我可以描绘出人类所经历的把不宽容推崇为最主要的美德之一的那些苦难的日子。
我可以谴责、嘲弄不宽容,直到我的读者齐声高呼:“打倒这个可恶的东西,让大家都宽容起来吧!”
说清楚怎样才能达到“宽容”这个美好的目标,这件事我却难以办到。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有各种各样的手册作为指导,……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提到能用40课时或者4万课时把“如何变得宽容”解释清楚。
的确,人们可以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谈论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和哥特式建筑的形成和发展,因为这些都是非常明确、具体的事物。即使没有任何别的材料,至少我们还可以研究自由贸易、奴隶制、死刑和哥特式建筑的那些宣扬者或者反对者的生平故事。……
但是,在宽容问题上,从来没有职业的倡导者。那些热情地致力于这项伟大事业的人,都是偶然为之。宽容只是他们的一个副产品。他们所追求的是别的事情。他们是政客、作家、国王、医生和谦虚的工匠。在做国王、行医或雕刻的闲暇时光,他们为宽容美言几句。但为宽容而斗争,却不是他们毕生的追求。他们对宽容的兴趣,就像对下棋或拉小提琴的兴趣一样。而且,由于他们属于形形色色的人(想像一下斯宾诺莎、腓特烈大帝、托马斯。杰弗逊、蒙田怎么会是朋友!),几乎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发现致力于同一事业的那些人一一无论是当兵、探测水深,还是将世界从罪孽中拯救一一一般都有的性格上的共同点。
作者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去求助于警句。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都可以用一个合适的警句来应付。但在宽容这个特殊的问题上,《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甚至老贝哈姆,都置我们于不顾。我凭记忆引用一下最接近这个问题的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观点。他说,大多数人有足够多的宗教信仰使他们憎恨自己的邻居,却不足以使他们爱自己的邻人。遗憾的是,这一真知灼见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目前的难题。有些人具有无人能及的宗教热情,却对周围的人充满仇视;还有的人对宗教毫无兴趣,却把爱心倾注在野猫、野狗,以及所有的基督徒身上。
房龙在这里用调侃的笔调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说清楚,怎样才能达到“宽容”这个美好的目标。一是因为在宽容问题上从来没有职业的倡导者。既使是热情地致力于这项伟大事业的人,都是偶然为之。这个现象虽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房龙点出这一点却意义重大。它使我们明白,要争取宽容的实现,有赖于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当我们在从事我们各自的事业时,都能自觉地把宽容当作“副业”,身体力行,宽容才有可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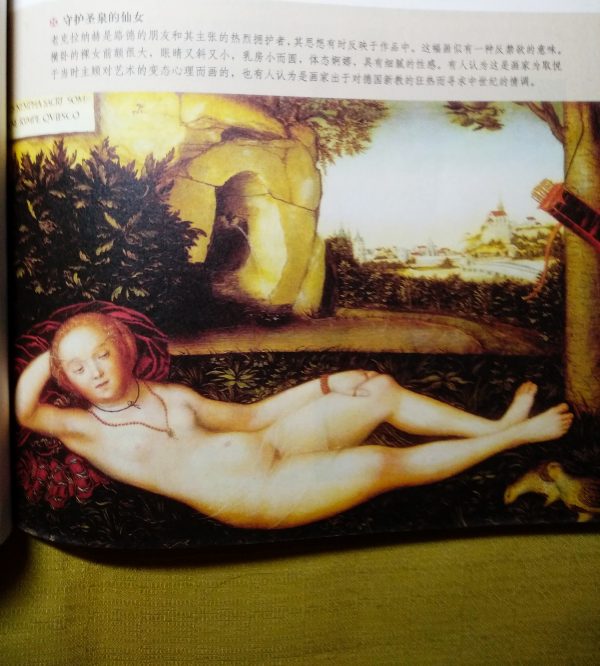 第二,房龙认为,任何哲言睿语对于宽容来说都不能贴切地包容其内涵。他以斯威夫特的观点作例,其实是在揶揄一些基督徒表现出的伪善。矛头所向,仍然是宗教不宽容。
第二,房龙认为,任何哲言睿语对于宽容来说都不能贴切地包容其内涵。他以斯威夫特的观点作例,其实是在揶揄一些基督徒表现出的伪善。矛头所向,仍然是宗教不宽容。
房龙接着用事实说话,试图找出自己的答案。
不,我必须找到自己的答案。经过充分的思考之后(但我并没有多大把握),现在我要说出所认为的事实。
那些为宽容而战的人,无论他们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信仰被怀疑弱化了;他们可能真心相信自己是对的,但他们从不让怀疑转化为绝对的信念。
如今是一个超级爱国主义的时代。当我们热情地大喊百分之百这个,百分之百那个时,我们不妨关注一下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它似乎天生地反感所有标准化的东西。
纯种的猫和狗都是人所共知的傻瓜,如果没有人愿意把它们从雨中抱走,它们就会死掉。合成的金属钢早已取代了百分之百的铁。没有哪个珠宝匠答应用百分之百的纯金或纯银打造首饰。再好的小提琴都必须用六七种不同的木材制成。如果完全用百分之百的玉米做一顿饭,那就多谢了,本人实难下咽!
简而言之,世间所有最有用的东西,都是杂合而成的混合物,我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信仰应该例外。我们“肯定”的基础里如果不包含一定的“怀疑”成分,那我们的信仰听起来就会像用纯银做的钟一样叮当响,或是像纯黄铜的长号一样刺耳。
宽容的英雄与其他人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人品的正直、信仰的虔诚、职责的忠实上,以及在其他人所共知的美德方面,他们就是在清教裁判委员会眼里,大多数也是符合要求的。我说得再清楚一点,如果他们不是在殊殊的良心倾向驱使下,成为那个自称拥有把普通人升为圣人的特殊机构的公开敌人,按原来生活和死亡的方式,他们中将至少有一半人进入圣人的行列。
然而幸运的是,这些英雄具有神圣的怀疑精神。
他们和他们之前的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都清楚要面对的是一个任何头脑健全的人都不指望能解决的极大问题。他们可以期望并祈祷自己所走的路最终能带他们到达安全的目的地,除此之外,他们从不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路,不认为其余所有的路全都是错误的,不相信那些吸引了一些头脑简单的人的小路是通向毁灭的歧途。
这一切听起来与我们的《教义问答手册》和伦理学教科书上表达的观点截然不同,那些书宣扬的是被绝对信仰的纯洁火焰照亮的世界所具有的绝对优良的美德。可能就是这样吧。但普通的百姓在被火焰照得最亮的这几个世纪里,生活得并不能算是十分幸福,也不怎么美满。我并不主张任何激进的改革,但只是为了调剂一下,我们可以试试宽容的宣扬者观察事物的一种眼光。我们还可以在这种试验失败以后,随时回到父辈的传统体系去。但是,如果这种试验可以给社会带来一缕温暖的光亮,使社会多一些善良和克制,少受一些丑陋和贪婪的仇恨侵扰,那么我敢肯定,和我们将得到的相比,所付出的代价是微乎其微的。
一点忠告,仅供参考。……
房龙的忠告实在是深刻隽永。我从不认为世上存在着一种终极真理,我也厌恶现实中有人常常以真理的代言人发话,显得高人一等。我对此很担心,也很害怕。我难以理解,那些以真理代言人身份要求大家众口一词的人,为什么要把精神生活搞得那么单调枯燥呢?
美国开国先贤杰斐逊说过:“我的邻居们是说有20个上帝还是说没有上帝,对我毫无伤害。”同样,我也可以说,我的亲朋好友说马克思是德国人,或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为何许人,对我们任何人也没有什么伤害。没有谁有义务必须有某种信仰,必须要掌握某种理论;没有人有权力要求我们必须崇拜任何东西。
思想宽容意味着,即使双方意见截然对立,针锋相对的争论也不会超出讲理论辩的界线,不会升级为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仇恨,不会由口舌笔墨之争变成牢狱监禁乃至大刑伺候。宽容精神的核心是思想自由,这是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而强求思想言论的统一是对基本人权的践踏。
房龙认为宽容就是“我活,你活,他活,大家都活”,而且活得惬意、自在。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别人走的路也不见得是错误的。人虽然要有自信心,但还得在“肯定”的基础上包含一定的“怀疑”成分。否则,必然要导致不宽容的发生。
房龙在书中将不宽容划分为三类:懒惰导致的不宽容;无知导致的不宽容;私利导致的不宽容。让我们琢磨体会他的分析论述是否符合社会现实,我们对此是否有同感。
先说懒惰导致的不宽容。
其中第一种最为普遍,在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阶层都能遇见。在小村子和古老的城镇最常见,而且不仅仅限于人类。
我们家有一匹老马,它一生中前25年是在考利镇的一个温暖马厩里平静度过的。但它不喜欢西港同样温暖的牲口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一直生活在考利镇,熟悉考利镇的一草一木。……
……如果我们能知道老马杜德对它考利镇的老邻居说了什么,我们将会听到它的最猛烈的不宽容的大发泄。杜德已经不年轻了,所以它对自己的各方面都习惯了。它的各种习惯多年以前已经形成,因此,考利镇的所有礼节、习俗和习惯对它来说都是对的;而直到死它都会认为西港的礼节、习俗和习惯完全不对。
正是这种不宽容,使父母对孩子的愚蠢行为直摇头,造成了“过去的好日子”的荒谬神话,使野蛮人和文明人都穿不舒服的衣服,使世界充满大量多余的荒谬想法,使具有新思想的人一般都会成为人类的敌人。
房龙在这里以一匹老马的思维作例,嘲笑了那些思想因循守旧而导致不宽容的人。这种不宽容的现象最为普遍,“我们大家注定或早或晚都要成为这种不宽容的受害者”,但房龙认为,“这种不宽容相对来说还是无害的”。因为,这些九斤老太大都是一些行将就木的老朽,他们的不宽容常常遭人讥讽,成为笑料。所以,房龙接着对无知导致的不宽容则要鞭辟入里地剖析了。
第二种不宽容则要严重的多。一个无知的人由于自身的无知,将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当他试图为自己缺乏智力而寻找借口时,他就成了一个神圣的恐怖人物。他在自己的灵魂中建立了自以为是的花岗岩堡垒。从这个可怕堡垒高高的尖塔上,他可以向所有的敌人,也就是那些没有他那种偏见的人,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有这种毛病的人,不仅残酷,而且卑劣。由于他们总是生活在恐惧中,他们很容易变得很残忍,喜欢折磨他们不满的人。正是在这种人中间产生了“上帝的特选子民”的观念,而且,有这种妄念的人总是假想自己与不可见的上帝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来鼓舞自己。这就当然为他们的不宽容赋予了神圣的赞许色彩。
比如,这样的人从来不会说:“我们绞死丹尼。迪弗尔,因为我们认为他威胁了我们的幸福,因为我们对他恨之入骨,因为我们就是喜欢绞死他。”哦,不会的!他们会庄重地召开秘密会议,为了决定丹尼。迪弗尔的命运,他们要筹划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当判决最终宣布时,可能只是犯了小偷小摸这样小错误的可怜的丹尼,却被庄重地宣判为最可怕的人。他胆敢违抗上帝的意志,这意志只能是私下地传递给上帝的特选子民,只有他们才能理解。因此,处死他就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那些法官也因为敢于宣判这样一个撒旦的盟友,而得到极大的荣耀。
忠厚老实、心地善良的人和野蛮粗鲁、嗜杀成性的人一样,很容易被这种致命的妄念所吸引。这是历史学和心理学的一个常识。那些兴致勃勃地观看一千位可怜的烈士遭受折磨的人群,当然并不都是罪犯。他们是正派的、虔诚的老百姓,并确信自己在做一件在他们的上帝看来是值得称赞、值得高兴的事情。如果有人对他们提到宽容,他们会认为宽容是道德软弱的可耻表现。也许他们是不宽容的,但他们为此自豪,而且振振有辞。你瞧,在潮湿阴冷的晨风中站着的丹尼。迪弗尔,穿着桔黄色的衬衫和饰有小魔鬼的马裤,缓慢而坚定地走向集市,在那里被绞死。而他们自己则在绞刑一结束,就会回到舒适的家里,吃一顿丰盛的烤肉和豆角。
这本身难道不足以证明他们做的和想的都是正确的吗?否则,他们怎么会在旁观的人群里呢?他们和死刑犯为什么没有调一下位置呢?我承认,这是个很站不脚的观点,但却很普遍。当人们深信自己的思想就是上帝的思想,当他们不能理解自己怎么可能是错误的时候,对这样的观点是很难辩驳的。
宽容是用讲理论辩来表现的,因此,宣扬宽容者必须在学识上高出一筹。而无知的不宽容者如果有权势为后盾,肯定会用压制、迫害来对付宽容。在房龙看来,无知的人往往具有“自以为是的花岗岩堡垒”头脑,这种人如果作祟,后果很可怕。在一个由“上帝的特选子民”主宰的社会,任何违抗上帝意志的人都会遭到残酷的迫害。我们只要回想起“文革”年代,在捍卫“革命路线”的幌子下,发生的兄弟阋墙、朋友反目、父子成仇的悲剧便可知其为害甚烈。与宗教不宽容相比,革命的不宽容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法国中世纪巴托罗缪之夜的血腥,中国文革中红卫兵的“红色恐怖”,依然是警策人心的历史教训。
 给当年的红卫兵戴上一顶“上帝的特选子民”的桂冠很贴切,因为他们自诩为“革命路线”的捍卫者,“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如房龙所指出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灵魂中建立了自以为是的花岗岩堡垒。从这个可怕堡垒高高的尖塔上,他可以向所有的敌人,也就是那些没有他那种偏见的人,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对于自己革命事业无比自信的中国红卫兵,当年曾大言不惭地叫嚷,将会亲手“埋葬帝修反,建成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结果呢?
给当年的红卫兵戴上一顶“上帝的特选子民”的桂冠很贴切,因为他们自诩为“革命路线”的捍卫者,“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如房龙所指出的,他们都“在自己的灵魂中建立了自以为是的花岗岩堡垒。从这个可怕堡垒高高的尖塔上,他可以向所有的敌人,也就是那些没有他那种偏见的人,质问他们有什么理由活在世上”。对于自己革命事业无比自信的中国红卫兵,当年曾大言不惭地叫嚷,将会亲手“埋葬帝修反,建成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结果呢?
接看房龙对第三种不宽容的论述:
剩下的就是第三种不宽容,即私利导致的不宽容。当然,这实际上是一种嫉妒,像麻疹一样常见。
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并教导人们说,靠屠宰十几头牛和羊,是不可能买到万能上帝的欢心的。这时,所有靠神庙中的祭祀仪式生活的人,都谴责他是个危险的革命分子。在他还没有对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造成持续的损害之前,他们就设法把他处死了。几年后,圣保罗来到以弗所,宣扬一种新教义。这种教义威胁到了靠卖当地的女神戴安娜的神像而赚大钱的珠宝工匠的生意。于是,金匠行会差一点私刑处死这个不受欢迎的入侵者。从那以后,依靠某种既定的崇拜形式维持生活的人,和那些会把人们从一个神庙拉到另一个神庙的宣扬新思想的人之间,一直存在着公开的战争。
当我们试图讨论中世纪的不宽容问题时,必须时刻记住,我们是在处理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这三种不宽容中的某一种。更多情况下,在引起我们注意的迫害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三种不宽容同时并存。一个享有巨额财富、管理着数千英里土地、统治成百万农奴的组织,会把全部的怒气和精力发泄在一群试图建立朴实无华的地上天国的农民身上,这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在这样的例子中,消灭异端分子就成了经济上的必要,这属于第三种,即私利导致的不宽容。
私利导致的不宽容过去和现在都是最大的不宽容。房龙的《宽容》中心思想是恐惧导致不宽容,恐惧的原因在于其利益受损害。罗马宗教祭司唯恐自身利益受损而对基督徒压制迫害;基督徒得势后为维护既得利益反过来又对罗马多神教徒进行压制迫害。在房龙看来,人类历史的铁的法则就是,任何人为了生存都得服从现实。因为每个人天生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那怕是神圣的信仰也得屈从于私利的需求。房龙对此作了以下论述:
从创世之初起,有一件事就似乎不可避免:少部分聪明的男女统治,而大部方不太聪明的男女服从。这两类人在不同时代所下的赌注,有不同的名字。一方总是代表力量和领导,另一方代表柔弱和服从。……它常常以奇怪的形式和伪装出现。它不止一次披上寒酸的外衣,大声宣称自己对人类的爱、对上帝的忠诚和给绝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卑微愿望。但在这悦目的外表下却一直隐藏着将继续隐藏着一个真实残酷的原始法则:人的第一任务是生存。……
就我个人而言,我奉劝他们还是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这样,也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有朝一日变成对人类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一伙从种族偏见、部落不宽容和绝大多数同胞的无知中获利的人所结成的联盟。如果有人怀疑这种观点,就让他研究一下教会在最初四个世纪的伟大领袖的生平吧。他会发现,这些伟大领袖无一例外地来自古老异教社会的某个阶层,他们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接受过训练,只是后来不得不选择了一个职业时才进入了基督教会。当然,他们中有几个人是被新思想吸引,全心全意地接受基督的教诲。但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从效忠尘世的主人转变为效忠天国的统治者,是因为后者晋升的机会要大得多。
总而言之一句话,人的生存第一,在私利的诱导下,任何信仰都可能成为谋生之道。对此,房龙写道:
……过去几个世纪一直为国家效力的优秀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只剩下一条晋升之道。这条晋升之路就是教会生涯。作为西班牙的基督教大主教,他们有望行使地方总督才能行使的权力。作为基督教作家,只要他们愿意全心投入理论课题的研究,他们就能赢得广大的读者。作为基督教外交官,只要他们愿意在君士坦丁堡皇宫里代表罗马教皇,……他们就能很快晋升。最后,作为基督教的财务官,他们可以管理迅速增加的地产,从而发大财。那些地产已经使拉特兰宫的教皇成了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最富有的人。
房龙就是这样用历史事实给我们展示出社会中的人谁也不能免俗,在利益面前谁也不会无动于衷。过去,虔诚的宗教徒表现出的不宽容根源在于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现在,坚定的革命者的不宽容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未完待续)
荀路2019.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