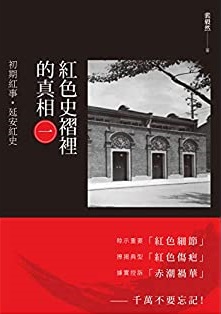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5)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5)
“左联”作家经济状况一瞥
报刊界——左士聚集地
报刊界向为左士聚集地,「辛亥革命时期的《太平洋报》,几乎全部是南社中人。」[1]维新党、同盟会、国共两党高干亦多出于文化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邹容、陈独秀、陈布雷、戴季陶、陈公博、于右任、吴稚晖、叶楚伧、邵力子、乔冠华、杨刚、宦乡……浪漫的文学总是缘起不满现实,因此也总是革命的起点。
党国重臣邵力子弃文从政前,长期任《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编辑,1919年3月4日~1929年1月20日,长达十年。以新文学驰名的创造社,几乎「集体加入」中共。瞿秋白、沈泽民、胡也频、蒋光慈、丘东平、陆蠡、叶紫等文学青年,先后成为著名共党分子。
彭家煌(1898~1933),1919年毕业于长沙省立一师,1925年入商务印书馆,助编《妇女杂志》、《教育杂志》、《民铎》等,月薪40元。1930年3月,彭家煌加入「左联」,参加中共地下工作,任中共《红旗日报》助编及通讯员。1931年被捕。出狱后,到宁波教中学,一面教书一面搞赤色宣传。[2]
1929年6月,1925~26年国共合作期间的留俄生开始回国,国民政府刊布广告,以月薪200银洋召募他们报到。谷正伦、谷正纲兄弟就是此时进入国民党中枢;张如心等为追求马克思主义,回沪后住棚户、当码头搬运工,甚至吃不上饭,过了一年艰苦生活,1930年才与中共接上关系,1931年6月加入中共,8月参加红军。[3]
1930年1月,留苏回国的朱瑞(1905~1948),上海街头偶遇两位莫斯科中大同学,两位已「消极」(不再参与赤色活动),「现漂流上海,以写文稿费度日。我们会见时已二、三日不食,饿得面蜡黄,仍在等他写作之〈墨子问题研究〉的稿费以解决食住问题。」回国时领得六七百元路费的朱瑞,「为争取他(怕他们可能卖我),给了他们一些钱,结以感情。」[4]
殷夫退还兄长的钱
殷夫(1910~1931),出身浙江象山怀珠乡大户,13岁考入上海民立中学。长兄徐培根大他15岁,浙江陆军小学毕业,升入保定军校、北京陆军大学(1922年第6期毕业),1927年1月宁海之战后得蒋介石赏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1926年,殷夫入团,1927年「四·一二」后被捕,入狱三月,差点被毙,殷夫贿赂狱卒送信给大哥,及时营救出狱,即转党。1928年秋,殷夫第二次被捕,大哥在国外,通过大嫂致函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保释出狱。
殷夫一度想留俄,苦于无钱。1929年4月,兄长徐培根公差赴德,行前寄给他300元,殷夫接到钱:「他还可怜我,他自己才可怜呢。我宁肯饿死也不用走狗的钱。」殷夫退回钱,写了那首〈别了,哥哥!〉(1929-4-12),结束段: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的阶级交了战火![5]
周扬、夏衍不用组织的钱
周扬(1908~1989)晚年谈及抗战前在上海:
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我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费,党并没有给我钱。[6]
周扬号称周瑜后裔,家道衰落。发妻吴淑媛(1908~1942),湖南益阳大户之女,周扬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活动,全靠岳家经济援助。1934年暑假,周扬爱上光华大学女生苏灵扬,与之同居,送发妻回益阳,断了岳家接济,经常上胡风处告贷,求借三五元菜金,「周扬经常来借钱,很少归还。」[7]1936年苏灵扬临盆,阵痛难忍,周扬身无分文,没法送医院,急得团团转。其女周密:
最后从郑振铎伯伯处借回20大洋,才使我免于落生在那间不满十平方米、整日不见亮光的亭子间里。有了我,您和妈妈的生活更加拮据了。不得不设法挣点稿费来糊口度日,列夫·托尔斯泰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中译本,就是在那种境况下问世的。[8]
《安娜·卡列尼娜》译酬约800元,周扬经济状态大大好转。[9]
1928~1934年,夏衍(1900~1995)搞日文翻译,「译稿费大概是每千字二元,我每天译2000字,我就可以有每月120元的收入。这样,在文艺界的穷朋友中,我不自觉地成了『富户』。」[10]夏衍还有编剧顾问的「车马费」、电影剧本编剧费,两项月入至少200元。夏衍1924年入国民党、1927年5月入共产党,文化界的红色职业革命家——
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中央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生。
1950年代初,中共评职级,人事干部问夏衍供给制时每月领几斤小米,夏衍说从来不吃小米,更没领过,那位人事干部一脸惶惑。后来,华东局与上海市委根据夏衍党龄与职务,评了个「兵团级」,书生从政的他「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11]。
阳翰笙、于伶经济状况
1928~1935年,阳翰笙(1902~1993)稿费加编剧费,每月收入200元。1935年春被捕,10月由柳亚子、蔡元培保释出狱,仍靠稿费与编辑《新民报》「新园地」副刊为生,月得百余元。1929年,鲁迅推荐柔石编辑《语丝》周刊。柔石的小说《二月》、《旧时代之死》亦由鲁迅作序和校订出版,20%版税,月收入80~100元。[12]
1933年5月,新婚夫妇于伶、王季愚租住上海亭子间,于伶担任中国左翼剧联组织部长,整天奔波在外。夫妇俩无职业无固定收入,经常吃上顿愁下顿。王季愚在家翻译一些苏俄短篇文艺作品,写一些小小说,向《大美晚报》等副刊投稿,于伶也写一些影评挣稿费,养家糊口。王季愚为商务印书馆标点《二十四史》,每万字仅得四角报酬。夏衍有时上门找于于伶谈工作,发现他们还没吃饭,临走时留下几毛钱,让王季愚去买一碗阳春面充饥。天冷了,夏衍从家里拿来妻子衣服给王季愚御寒。阳翰笙也不时给予一点补贴。[13]
1934年,左联责任人任白戈与徐懋庸的交通关露(女诗人),蹲居小亭子间,穿着虽然摩登,但生活甚窘,没有职业,写诗换不了多少稿费,有时连吃饭的钱也没有,靠妹妹的接济才维持下来。[14]
这一时期,于伶撰写影评换稿费,千字二元,很高了。一天下午,于伶上白薇家叫窗,正在写作的白薇推窗一看,于伶要她扔两角钱下来,说是借钱去看电影,电影快开场了,他没时间上楼。白薇掷怨:没钱看什么电影?于伶说:正因为没钱,看了电影才有钱!白薇掏出两毛钱,顺手旧报纸一包扔下,于伶接钱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电影散场,他跑到附近小面馆,边吃边写,既解决晚饭也写完影评,然后直跑报馆,稿子丢进信箱。江苏省委遭大破坏,于伶、王季愚先后代课于中国中学、正风中学,有了稳定收入,方能四处搬家,以避抓捕。[15]
草明、关露、二萧很穷
1933年,广东女师生草明(1913~2002)因「红」暴露身份,上了通缉名单,逃亡到上海,加入「左联」——
我们这些年轻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找不到职业,生活是很艰苦的,稿费也很低,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有时实在吃不上饭,鲁迅先生和左联的一些同志热情地从他们有限的生活费用中匀出一小部分来接济。我住在租界里房金最便宜的亭子间里埋头写作。[16]
1934年,女诗人关露(1907~1982)任「左联」领导人任白戈与徐懋庸的交通,住亭子间,穿着摩登,生活却很困难,没有职业,写诗换不了多少稿费,有时连吃饭的钱也没有,靠妹妹接济才得以维持。[17]
1934年11月初,萧军、萧红揣着朋友给的40元钱搭船赴沪,搬入月租九元的亭子间后,二萧手里已不足十元,他们买了一袋面粉、一只炭炉、一些木炭,以及几副碗筷、盐醋,食油已买不起。每天白水煮面片,外加几个铜板的菠菜青菜。一天,朋友张梅林来看他们,萧红留他吃饭,梅林甚感不忍,因为那袋面粉在渐渐瘪下去。因须复写《八月的乡村》,萧军当了萧红的一件旧毛衣,只押得七角,坐车就不能买纸,买纸就不能坐车。萧军走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购回日产美浓复写纸,由于皮鞋不跟脚,脚后跟走得又红又肿。1935年3月1日,《文学》杂志第四卷第三号刊出萧军第一篇小说〈职业〉,稿费38元,算是将二萧从窘迫中捞救上来。[18]
亭子间作家
红色文士中也有靠稿费坚持写作的「亭子间作家」。1935年3月中旬,系狱两年半的陈白尘出走苏州反省院,上海《文学》杂志主编傅东华答应每期用他两篇稿子,以支持其生活。陈白尘:
这可大出我的意料:原本一篇稿子的稿费就可以维持我两个月的生活了。于是我便有了信心,做一名所谓的「亭子间作家」。[19]
亭子间里的左联文学青年,早餐三分钱,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点白糖);中餐七分,小饭馆里的米饭豆腐、猪肝菠菜汤;晚餐四~五分,喝粥,一碟小菜,每天不到二角,每月伙食费五~六元(合2003年150~180元人民币),城市贫民生活水平。[20]
贾植芳(1916~2008):
没有住过上海亭子间,怎么可能成为艺术家?三十年代的时候,我和黄永玉都住在亭子间里,开荤的日子就是吃碗阳春面,上面漂着几滴猪油花。那会儿,唉,黄永玉穿的西装裤子上哪里去烫啊,还不就是折了一条线,压在枕头底下,睡觉的时候把它压一压。到关键的时刻,才舍得拿出来穿啊。……上海的亭子间,可了不起呐!出了多少人啊![21]
1932年陈白尘回江苏淮阴老家闹红,秋天被捕,次年押解镇江,判刑五年。1933~1934年,他在狱中写下50多万字作品,大多为控诉黑牢生活,两块大洋买通看守,稿件秘密寄往狱外,陆续发表左翼刊物。独幕剧《虞姬》发表《文学》(1933年一卷三期),稿费50元。狱犯十分红眼,陈白尘惴惴不安,不得已用此款去买「外役」(牢内较自由的义务劳动),将钱花在狱中,别人也就不怎么眼红了。[22]
托派卖稿为生
1928年,随着托派留俄生陆续回国,他们中许多人在上海卖稿为生,托派经费亦靠此维持,尤其靠翻译稿酬。他们依托上海的文化环境,这批耍弄笔杆的托派文人,趁时托势,形成一点小气候,宣扬托洛茨基主义。
以卖稿得来的稿费维持个人的生活和托派组织的经费,这是当时上海托派分子之所以能聚集较多,搞成一点小气候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没有这个条件,那些离开了文字手段难以谋生的人,很难较长时间聚集在一起,中国托派运动也就很难搞成那样的声势。
卖稿为生的托派分子有的也很穷,如没出过国的北大毕业生陈其昌(托派中委),为报刊写国际政治社评,一家三口,妻子家庭妇女,做点临时帮佣,全家穷到「三月不知肉味」。但「他从不发一句怨言,不向人诉苦,也不轻易向人告贷,不影响对托派工作的热忱,以此赢得托派同志的尊敬。」[23]
下狱的郑超麟等人,狱中译出的稿子,也能很快发表、出版,「而且收入不少稿费,有的人还可以拿去养家。超麟译得多,译得快,他的稿费也多。」[24] 1930年,托派青年王凡西(1907~2002)被中共开除,生活无着,且卧病在床,妻子又近分娩——
惟一可以找点生活费的是卖稿子……于是口译了普列汉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由妻子笔录,居然卖到120元(约等于五个月的党内生活费),如此才算度过了被党(中共)逐出后的第一个难关。
王凡西后来编译了一部《插图本俄国革命史》,稿酬三元/千字,三四十万字,稿费千元左右。
我在1931年5月被捕以前,生活来源完全靠了此项稿费。不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按:托派)干部分子,只要是能够提得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文稿解决生活问题。不但各人自己的生活,甚至当时各小派(按:托派内部小派别)的经费,以及每派中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的生活,也取给于那些卖文者的收入。[25]
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其时稿费都不算低,也是那些「亭子间作家」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译家梁实秋翻译莎剧,不按字数,一齣剧本一千元。卞之琳这样大学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子,最低译酬五元∕千字,也相当高了,卞晚年仍记忆清晰。[26]
张春桥被辞退
1935年,十八岁的山东中学生张春桥(1917~2005),寻出路于沪上。上海杂志公司张静庐(1898~1969),录聘张春桥为助理编辑,试用期月薪30块,让他校点清初拟话本小说《豆棚闲话》,标点了十几页,张静庐接过一看,都是破句,发现此人根本不懂古文,便对张春桥说:
张先生,我们本想扩大营业,你看得起我们,来帮我们忙,可现在市面不景气,生意很萧条,所以我们只好让张先生另谋高就。以后等市面好了,再请张先生回来帮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实在对不起。张先生来了一个礼拜,我们按一个月的工资付给你三十块钱。现在市面不景气,外面的工作也不太好找,我们再付给张先生三十块钱,以备找工作期间开销。 [27]
精明的上海人都不愿得罪人,一周付两月工资,今天都无法达到的人性化层次。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上海出版机构的质量。对张春桥来说,一周挣回两月薪水,也划算得很。文革一起,张静庐深遭迫害。
四个等级的沪上作家
据1930年代上海杂志《宇宙风》,沪上文化人分四个层次:
一等:资历深名气大,稿费之外还有版税等其它收入,主编刊物的编辑费通常100元,丛书编辑费通常200元,每月总收入400元以上,如鲁迅、徐志摩(不仅教书、写作,还开新月书店)、邵洵美(盛宣怀孙女婿)、郁达夫、胡适、田汉、巴金、茅盾等。这一阶层属于高收入阶层,饮食丰盛,居住宽敞,出入有车。
二等:已成名,稿酬三~五元/千字,可住二~三间房,房租20元以上,生活费约160元,月收入达200元,进入中产阶层;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等。
三等:小有名气,稿酬二~三元/千字,独立出书,有版税收入,可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房租15元左右,生活费120元,月收入约150元;如刚刚从四等升上来的阳翰笙、胡也频、丁玲、萧军、萧红等。
四等: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稿酬一~二元/千字,住亭子间,房租10元,每月伙食费40元,月收入80元以下;如柔石、沙汀、艾芜,属普通贫民阶层。这一阶层的作家一旦成家,每月生活费需60元左右才能对付下来。[28]
2011-12于沪·三湘
[1]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页453。
[2] 赵景深:《我与文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125、268。
[3] 沈漪:〈怀念张如心同志〉,温济泽等编:《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88~189。
[4] 朱瑞:〈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4年,页238。
[5] 张小红:《左联五烈士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85~211。
[6] 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七十年代》(香港)1978年9月号。朱鸿召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36。
[7] 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1年,页117。
[8] 周密:〈怀念爸爸〉,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578。
[9] 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1年,页123。
[10]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页87~88。
[11]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页610。
[12] 陈明远:《才·材·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60~161,158。
[13] 赵劭坚等:《平凡人生——王季愚传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页24、44。
[14]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一年,页194。
[15] 孔海珠:〈于伶的左翼戏剧生涯〉,《世纪》(上海)2010年第3期,页52。
[16] 草明:〈回顾与前瞻〉,载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当我年轻的时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79。
[17]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94。
[18] 秋石:《两个倔强的灵魂》,作家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81~83,118。
[19] 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页480。
[20] 陈明远:《才·材·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57。
[21] 彭小莲:《他们的岁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1年,页100。
[22] 陈白尘:《对人世的告别》,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页470。
[23]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东大图书公司(台湾)1994年,页133、178。
[24] 楼适夷:〈《玉尹残集》序〉,参见《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699。
[2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32~133、165。
[26] 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全新增修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213。
[27] 贾植芳:〈上海是个海——我在上海的生活史〉,《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页34~35。
[28] 陈明远:《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1年,页101~103。
陈明远:《才·材·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55。
原载:《上海作家》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