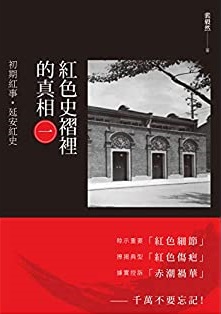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6)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6)
中统要员说“中统”
徐恩曾(1896~1982)回忆录《我与共产党战斗底回忆》撰于1953年,1950年代由美国新闻处在香港发行英文版《Invisible Conflict》(看不见的战斗),中文本延宕至1985年才出版,作者已离世三年。徐恩曾回忆录详述1930年代上海中共地下党一系列大案,与大陆中共史述有一定出入,虽然其间难免种种自塑英姿、遮遮掩掩、甚至「莫须有」,但徐作为国民党方面当事人,其叙其述,至少值得备考。
拙文结合中统主任秘书万亚刚的《国共斗争的见闻》《细说中统军统》(均为台版)、提供一些「中统」细节,至少对大陆有相当新鲜度。
陈立夫接命
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认为中共地下党行动诡秘、组织严密,需要专力对付。徐恩曾:
深切地感到这批曾受外国严格训练的赤色破坏分子,已非普通的治安工作人员所能应付,故于192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中设立一个机构,集中一批智慧较高的干练人员来专责防御。我于1930年初接受任命,主持这个新设机构。
1928年3月,国军总司令兼国民党中组部长蒋介石指派陈立夫主持这一专门对付中共地下党的新设机构,同时接受「清党」后逾万中共青年「自新」。1925年回国的留美工科生陈立夫(1900~2001),时任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机要科长,认为自己个性与兴趣并不适合此任,且无这方面任何知识经验,从对物不对人的采矿工程到专门琢磨人的「调查统计」,弯子转得太大,一下子转不过来。他去请教戴季陶,戴回答——
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调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公正的人,才能管得住他们而不出乱子。你看寺庙中两边站的十八尊罗汉,个个都是浓眉怒目三头六臂的,但是中间坐的那位如来佛,却是何等的慈祥雍穆,惟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蒋先生要你去做,就是这个道理,我看你还是从命罢!
陈立夫被打动,于是接任。最初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成立调查科,成员都是留美生,工科生文科生都有,没一个懂美国的FBI(联邦调查局)与苏联的格别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初称契卡,后称克格勃)。调查科成立之初仅十七、八人,后拨来十名中央党校毕业生。不久,调查科就有了工作成果,破获中共地下机关,劝归中共青年也很顺利,每月数百名归顺国府,总计1.6万余名。[1]「四•一二」清共后,中共奄奄一息,确为扑灭赤祸最佳期。中共《中央通信》第13期(1927-11-30):
党员的数量自从国民党反动以后有极大的减少,从五万余党员减至万余党员。[2]
1964年3月,毛泽东忆曰:
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当时有五万余党员,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被杀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敢干、逃跑了,只剩下一两千人。[3]
1925年秋加入中共的「创造社」成员李一氓(1903~1990):
大革命最高潮的中共党员有七万人,到1928年就只剩下一万人,减少了85%,这还包括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的党员,他们恐怕比在城市里坚持地下工作的党员的人数还要多。[4]
1928年1月初〈中央致湖南省委信〉——
(1927年)5月与10月失败之后,农民协会的会员由五六百万减少到数千。[5]
1929年6月25日〈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
中央回国工作的时候(按:1928年7月中共六大结束后)……各省组织不断的破坏,党的积极勇敢的干部,牺牲在五百人以上,同时自首叛变的现象普遍发生,在两湖特别表现得严重。[6]
中共政治局委员黄平(1901~1981),1932年12月14日天津被捕,1933年1月6日写下〈自首书〉,宣布脱离共党,随即释放,教书为生。
1932年任江苏省委沪西巡视员并被捕的刘顺元(1903~1996):
仅1929年上半年,不到半年之内,上海被捕的共产党员约600人左右。[7]
陈立夫上任不久,由中组部调查科主任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调查科主任由张道藩(留法生)、吴大钧(留美生)、叶秀峰(留美生)先后兼代,1928年12月移交徐恩曾(留美生)专任。
中央调查科到1931年7月最盛时也不过50人左右。[8]
1931年,调查科破获顾顺章案,深受蒋介石重视,指示二陈扩大调查科。于是,在调查科基础上成立「特务工作总部」(南京道署街132号),直至1938年撤销,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特工总部不挂牌,对外用代号——正元实业社,各省市党部成立下属「特务室」,南京、上海秘设「行动区」,也各有代号,公文往来均用代号,一年一换,「特工总部」1936年代号「华统」,抗战爆发后改为「鲁黎」。[9]
1932年「军统」出现雏型,中统发现委员长侍从室有人在做相同工作。中统人员愤愤不平,认为蒋公可能不信任中统。经陈立夫安抚,众渐悦服。陈立夫与蒋介石之间,也捅开存在军统这一事实。陈立夫认为如不向蒋汇报「有人在干相同工作」,蒋会轻视他们,认为中统耳目不聪。蒋介石最初有点不好意思,只承认要戴笠调查一二案子,并无专门组织。
1938年,陈立夫调任教育部长,国民党正式成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长朱家骅、副局长徐恩曾。军统局长贺耀组、副局长戴笠(旋升局长)。「二统」分工:中统对付中共地下党,军统对付军事上的共军。[10]
1947年秋,撤销中统,改组为隶属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的「党员通讯局」,迁台后改属司法行政部。
徐恩曾
陈立夫虽为中统创始人,中统长期实际负责人为徐恩曾。徐恩曾,浙江吴兴人,出身富门大户,上海南洋大学电汽工程系毕业后留美,学的工厂管理。青年徐恩曾认为中国落后源于贫与愚,救国之道首在生产与教育。毕业回国前,一个国民党籍同学的一番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
从发展生产而发展交通而普及与提高教育,以达成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目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目前没有这个条件。因为任何的建设,需要一个安定而健全的政治环境,目前中国因政治不清明,军阀时常混战,一切都在混乱中,不容你有从事生产建设的机会。所以要实现建设救国的机会,首先要改革政治,建立一个足以保障一切建设事业的安定社会。[11]
徐恩曾听闻大为感动。这个同学回国未从政,徐则一步步走向国共政争第一线。1925年徐恩曾回国,第一份职业上海南市私营水厂总工程师,一年后因感于无法进行希望推行的任何改革,转身投入如火如荼的北伐。1928年,出任国民党中组部总务科长,12月接手中调科,1931年兼中调科长,1935年升任处长,同年11月国民党「五大」,徐恩曾进入中执委。
徐恩曾根据古训知己知彼——「必须从敌人的基本理论研究起」,发动所有部属学习马列主义、熟悉俄共党史、了解中共组织活动的方法原则,同时要求部属深入研究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务使每人都具备克服任何最雄辩的敌人而不为敌人所难倒的能力」。徐恩曾使这种研究常态化,「这在以后的工作表现中,证实是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转变」被捕中共人员的过程中,徐恩曾将三民主义解释为与马列主义殊途同归,只是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即三民主义认同马列主义无国族无阶级、无贫富差异、无剥削压迫的大同目标,但三民主义走的是和平缓进、建设互助的途径,马列主义则用暴力激进、破坏欺骗的手段,走的是「斗争道路」。如此这般,既适当保持对方尊严,亦降低对方抗御的程度,容易打动他们心弦,从而达到「政治说服」,认同接下来的核心观点——「解决政治问题可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则不能用革命手段。」
国民党史家认为:三民主义与马列主义「趋同论」,实为国民党理论战线一大失着,等于给马列主义发放合法证,致使马列赤说日益扩张,成为相当一部分青年的价值标准。
中共叛徒
徐氏回忆录中,中共叛徒乃一大内容。事实上,中共叛徒渐渐充斥中统,成为不断注入的「新鲜血液」:
这些人(被捕中共党员)经过「招待、说服、转变」三部曲,最后总是由敌人变成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由于这些新血液的注入而迅速增加。这些新手加入之后,每人多少都从他们的「娘家」带来一些礼物——共产党的秘密,所以更予共产党继续不断的破坏,使共产党在赤区以外的各地地下组织,濒于不能维持或重建的窘境。
徐还观察出中共被捕者思想转化起于一声叹息——
轻微的叹息,这是一个共产党徒恢复人性的开始,也是他的感情最脆弱的时候。[12]
徐恩曾第三任妻子,即顾顺章秘书费侠,北平贝满女中生,留苏期间加入中共,中共特科成员,相貌出众,爱好文学,口才极佳。1931年,顾顺章被捕叛变,费侠在南京被捕,在顾顺章劝说下「转变」,1938年嫁徐恩曾,中统机要员;1948年国府立法委员。
中统主任秘书万亚刚(1909~?)提供资料,截止抗战前中统战果丰硕(符合中共史书「白区工作损失90%以上」)——
抗战以前,中统和中共进行的地下斗争,战果丰硕,捕获中共高级干部计有:总书记二人——陈独秀、向忠发;中央委员四十余人(其中包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13人);省级干部八百余人。其中除少数不肯转变外,大都转变后为中统所罗致,以致在中统成员中,「转变分子」占有半数,而且他们全都担任业务工作,成了中统的主干。中统的成绩,都出于他们的贡献,这是中统同仁都承认的事实。[13]
进入中统的著名「转变分子」(不完全统计):顾顺章、张国焘、罗章龙、徐锡根、卢福坦、李竹声(以上为政治局一级);
中委:黄平、余飞、袁炳辉;
省级:盛岳、汪盛荻、王云程、孙济民、袁家镛、朱阿根(以上为「二十八个半」);杜衡、杨天生、周光亚、廖划平、姚蓬子、卜士奇、张应龙……
「转变分子」渐增,中统训练股,除组长、万亚刚及图书女管理,清一色全是「转变分子」:罗章龙、姚蓬子、卜士奇、余飞、王云程、袁家镛、汪盛荻、李士群,「人才济济」呵!中统作风及内部生活无形中也渐受中共感染,如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培养集体意识、过小组生活等。[14]
叛徒只有利用价值,不可能再有政治信誉。徐恩曾虽「重用叛徒」「以毒攻毒」,但他主持「中统」时期,对中共叛徒设有底线——「既用又防」,科长以上职务从未授予「转变分子」。蒋介石也训示戴笠:「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15]
罗章龙「转变」后曾入中统,尚未进入「组织视野」。中组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罗章龙」词条就未有「入中统」这一笔。
顾顺章死因
对于中共党员的叛变,中统专用词为「转变」。1931年5月顾顺章「转变」前,中统对破获中共地下组织进展不大。抓到顾顺章后,徐恩曾干劲极大,三天三夜不休不眠连轴转。
顾顺章「转变」后,虽因钱壮飞「卧底」,周恩来等要角得脱,但沪宁平津及汉口、苏州等中共地下党还是遭到重大破坏。顾顺章首先供出狱中的中央委员恽代英(1930年5月6日以「共嫌」被捕),顾顺章知道恽代英所用化名及监号。周恩来仅差一刻钟得脱。顾还招降中共特工胡大海、胡洪涛、王国栋等。[16]
徐恩曾记载:
他(按:顾顺章)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时,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破获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致无法恢复组织。
中统倚靠顾顺章立了大功,蒋介石召见徐恩曾与武汉特派员蔡孟坚,特予表彰,备加勉慰,升调查科为调查处。[17]
鉴于钱壮飞通过公开招考来到徐恩曾身边,中统从此不再公开招考。对来历不明与不了解者(尤其中共叛徒),始终存在戒心。入口收紧,似再无中共特工渗入。[18]
关于顾顺章之死,一直扑朔迷离。徐恩曾证实顾顺章1935年被国民党处决,徐恩曾认为顾顺章「转变」后并不安分,四处寻找政治出路,又想回头再入中共,被徐恩曾发现——
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待他,日子一久,他仍感到不耐,要找政治上的出路。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又去和共党勾结,向共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现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虽然他在这一时期对我们的贡献,是永不该抹杀的。
1928年即为调查科助理干事的张国栋说:顾顺章虽卖力叛变,徐恩曾对他并不放心,派人暗中监视,且只让顾顺章干培养特务的活儿,编了一套培训特务的教材《特工丛书》(六本),分别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察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约50万字。顾顺章因得不到徐恩曾信任,欲投靠另一头的军统,为徐恩曾不能容忍,一次酒席上拍出手枪要杀顾,被阻拦。徐恩曾便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名,先软禁顾顺章,后送苏州反省院,1935年秘密处死。[19]
按常理,顾顺章对中共欠下如此血债,不可能再叛回中共。徐恩曾为杀顾找借口,推说顾欲叛回中共,似合逻辑。同时,徐恩曾未能列示顾顺章欲叛回中共的客观证据。
万亚刚晚年撰文驳斥老上司徐恩曾上述「评顾」,有一段值得引述的深入分析,结论是顾被杀乃「冤假错案」——
这番交代前后矛盾,不近情理,令人难以接受。例如说他(按:顾顺章)日久生厌而起异心就不对。顾顺章被处刑,应在1933年春季以前,因在这以后顾顺章就消失了。自转变到处刑不过一年半,时间并不久。而在这段时间内,顾顺章正忙于协助破案,日子过得非常紧张而惬意,怎会感到不耐?其次,聪明如顾顺章难道不知自己这套本领,市场有限,除在中统吃香外,换个地方就派不上用场。那有另找出路之想?第三,顾顺章和共党之间已仇深似海,即使他要另找出路,也不会重投共党。第四,即使顾顺章已和共党重新勾结,共党也必定要他做第二个钱壮飞,绝不会要他提供什么情报或逃往苏区。第五、前面说他「重新和共党勾结」,这是说已和共党勾结上了,但最后又说「又想回到敌人怀里」,多了一个「想」字,又意味着想和敌人勾结而未成其事。究竟顾顺章是已遂犯还是未遂犯?这里无从认定,岂非自露马脚?
根据以上分析,肯定顾顺章未曾重回共党怀抱。这是一桩冤假错案。
万亚刚认为顾顺章死于才高招忌,并说操办顾顺章后事的一位老中统(也是中共「转变分子」)证实这一判断:
到底顾顺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招人忌是庸才」,正因为他不是庸才,而且锋头太健,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
顾之被杀确出于中统人员的妒忌陷害。[20]
罗绮园、杨匏安被捕
据徐恩曾记述,王明回国后不得志,挑拨中共成员内部矛盾,借国民党之手翦除瞿秋白、李立三派重要干部。1931年7月,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罗绮园(曾任国民党中委),就是王明利用一桩桃色案件进行「挑拨」而被捕。
留苏生胡君回国后,分配江苏省委工作,其妻陈小妹年轻漂亮,也是中共党员,一同派江苏省委妇女部,夫妻感情很好。可中央突然指派陈小妹「住机关」。所谓「住机关」,这一时期中共地下党专用术语,即扮假夫妻组成家庭,一则不易引起注意,二则上海房东都怕惹事,不租给单身汉(地下党员多为单身)。陈小妹要住的机关为中宣部副部长罗绮园,假扮罗妻,以为掩护。胡陈夫妇万分不情愿,但必须接受组织安排,忍痛分手。陈小妹「住机关」后,多次向丈夫胡君哭述种种「不方便」,包括对罗绮园的不满。胡君本就对这种「乱命」不满,求教老同学王明。王明密语:「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胡君十分震惊王明的点拨,最终「小资产阶级温情」战胜马列主义「阶级情」,向中统告密。
王明原设计匿名告密,事前将陈小妹约出,以免同时被捕,做得不露痕迹。胡君则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告密了,就不想再与中共保持联系,自己出头举报。
1931年7月25日清晨,胡君将中统特工领到法租界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华丽巨宅,接出爱妻,罗绮园被捕。中共中央监委、中央农民部副部长杨匏安(曾任国民党中组部代部长、中常委),因住宅内一起被捕。8月28日,两人被毙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21]
向忠发被捕
关于向忠发被捕,党史界一直说向贪恋舞女小妾,冒险回去看她而被捕,顾顺章派中统密探早已守着这位小妾。徐恩曾的记述则完全为另一版本:向忠发的被捕乃一中共党员告密,而且直接告至徐办公室,最终发现这是一位「特别告密者」。
接到告密,徐恩曾最初不相信,但还是派员跟他走一遭,结果在法租界霞飞路一家珠宝店楼上抓到向忠发及相好(舞女)。见是一土头土脑五旬糟老头,不太懂政治。向忠发一开始不承认自己是中共总书记,加上中统并不信任那位告密者,还以为抓错了。正在为难,一位中统成员说曾与向忠发原是船上同事,向忠发当年嗜赌,为戒赌明志,自砍左手一截无名指。被抓老头左手无名指还真少一截,向忠发见无法抵赖,这才承认身分。
此前中共高干被捕后不少「转变」,中共中央赶快放出空气:
过去许多党员的叛变,乃小资阶级动摇善变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现,向忠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无产阶级有对革命忠实到底的优良质量,决不中途动摇转变,所以相信向忠发一定不会向敌人投降,一定会替共产党牺牲。
奈何向忠发贪生怕死,为向国民党示诚,跪地求饶,「可怜相」大大超出此前叛徒,「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供述自己只是普通工人,实为傀儡,并供出四处重要机关位址。徐恩曾说按中统规矩,向忠发既然真诚「转变」,理应满足他的求生愿望。但当他在南京接到向「转变」报告,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已枪毙向。徐说:「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
既然举报为实,徐恩曾发给那位告密者一笔奖金,并于中统机关安排职席。不料,一个多月后,此人突然失踪。徐恩曾:
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前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向忠发一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走还等待什么?[22]
「特别告密者」、「借刀杀人」,向忠发的被捕多了一种说法,扑朔迷离起来。中共之所以一直回避此说,亦合逻辑:如斯内斗,不利于党的形象呵!
丁玲被捕
1933年5月~1936年9月,丁玲被捕,软禁南京。这段历史成为她终身无法甩脱的包袱。1940年延安就流传丁玲是「叛徒」的小道消息,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甚至在会议上提及。[23]1943年延安抢救运动中,老党员夏大姐称「已经不以丁玲为同志了,因丁玲政治上已失了节。」[24]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罪据之一就是这段很难说清楚的「历史问题」。1956年中宣部复查小组六改结论,有人认为被捕后继续与叛徒冯达同居育婴就是叛变,小组会上争执不休,字斟句酌,最后一稿达成妥协:「丁玲被捕后有变节行为」。[25]1957年中国作协大会宣布丁玲为「右派」「历史上可耻叛徒」。[26]
丁玲后半生很大精力用于辩诬。1978年,丁玲流放山西,丁女上京找周扬,周扬还坚持:现在你妈妈的历史疑点可以排除,但污点还是有的。对丁玲历史问题持这一观点的人为数不少。[27]
笔者出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一直关注丁玲被捕细节。丁玲对这段历史长期回避,语焉不详,寥寥数语笼统概括,缺乏具体描述,只承认「一时软弱」。根据常识,不愿细说必存不便。读了徐恩曾回忆录,方知丁玲确有「相当不便」。
徐恩曾证实1933年4月逮捕冯达、丁玲夫妇时,冯达即「转变」,并一直替中统工作。丁玲也写了〈自新书〉——
她也表示愿意放弃过去的道路,并完成了书面的自新手续。
徐恩曾十分看重丁玲的写作才能与社会影响,生活上极尽优渥,不仅为丁玲夫妇安排「金丝笼」,还提供生活经费、安排上莫干山避暑、从湖南接来丁母,并让他们完全自由居住在南京中山陵附近别墅,只是嘱他们不要离开南京。1936年夏,冰心夫妇路过南京,特意去看丁玲,划船玄武湖。
丁冯夫妇与徐恩曾来往密切,徐恩曾喜欢郊游,丁玲常常一起去。
在她完全自由地住在南京的时期,我和她们夫妇之间的正常友谊的关系,逐渐建立起来,我到他们家里去访问,她也常到我家里来玩,和我底家里人也玩得很熟。
1935年春,丁玲生下一女,冯达因肺结核长卧病榻,丁玲久侍床边,十分烦躁,情绪低沉。徐恩曾给了她一笔钱,让她上北京玩了一个月。丁玲后借口赴沪治病去了陕北,徐恩曾挨了批评,说他对待「政治敌人」比对自己同志还要还优容。徐恩曾:坚信丁玲内心一定会对当年的「优待」长存感念,午夜梦回。[28]
1986年丁玲去世,中统骨干万亚刚(1909~?)亦撰文:
丁玲死了,报上刊出很多追悼文章,都同情她坎坷多难的一生。其中关于南京生活的一段,都说是坐了三年多牢,吃了很多苦,完全与事实不符。本无更正的必要,只因丁玲生前她自己对记者说过,国民党要杀她,所以才逃离南京,投奔延安,丁玲这样说,实在太无良心,为明是非,不能不揭露其中真相。……三餐茶饭,招待丰盛,丁玲自称这样的舒适生活,从未有过。到了夏季,南京炎热,又将她夫妇送往莫干山别墅避暑,入冬才回南京。这时,丁玲除不能离开南京,行动已完全自由。中统在中山陵附近筑有一所洋式平房,名「苜蓿园」,环境幽静,为中统领导人周末休闲之所,中统特将她夫妇和姚蓬子一起,安置在那里,待她不谓不厚。多有应她的要求,将她母亲从湖南接来同住。……这是丁玲在南京三年多的生活实况,既没有坐牢,更不曾受苦。她所受的优待,使许多中统同仁羡慕之余,还有怨言。她说国民党要杀她,只要看她的丈夫××如今还健在,就可粉碎她的谎言。笔者是苜蓿园的常客。[29]
徐恩曾、万亚刚为「丁玲被捕」提供了相当重要的细节。按1950~60年代红色氛围,徐著如「及时出版」,对丁玲相当不利。尤其徐证明她写了〈自新书〉、与徐家打得火热、长期给予自由、给钱上京散心,那还得了!
1984年,丁案彻底平反,晚年丁玲(1904~1986)对「被捕」详细自述,载王增如、李燕平编《丁玲自叙》(团结出版社1998年)。虽然丁玲自叙仍以「辩诬」为主,处处明显利己——迫不得已、与冯达保持距离、始终想回「家」(中共组织),但重大细节上,与徐恩曾、万亚刚之说相当吻合:一直未入狱、提供高级香烟(白金龙牌)、相当自由、丁母接宁、上莫干山、上北平、冯达任职(翻译)等等。根据常识,丁述显存删隐:与徐恩曾的关系、赴北平的费用、为什么长期不「回家」?如果始终被监视,如何赴沪脱身?
笔者综合判断:即便根据丁玲自叙,自新书上写下「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30],按1950~70年代意识形态标准,丁玲确存污点,至少「革命立场欠坚定」「一时迷失方向」,加上与冯达继续同居且生女,未与叛徒划清界限……但丁玲毕竟并未实质性叛变,未供出机密,「不参加社会活动」为屋檐之下权宜之言。此后,丁玲投奔陕北,其红色文艺活动与晚年赤左言论,完全证明她对中共的忠诚。中共当年死抠丁玲被捕,除了宗派因素,也说明红色气氛过于严苛,意识形态太偏,必须彻底纯洁,不容斑点瑕疵;只讲党性不讲人性,好像党性可以离开人性基础。丁玲迫于那个时代的红烈氛围,不敢承认受到国民党的优待,生怕再授人以柄。
徐恩曾后悔
根据徐恩曾回忆录,1933~34年上海中共党员不过485名,其中暗暗向国民党「转变」并领受任务183名。中统为将潜伏者「送上去」,有意端掉几个中共机关,从而使「自己人」升职,参加中共中央会议,以掌握中共地下党一举一动。1934年6月14日17时最后收网,还特意保留一部分;已掌握的60余中共机关与接头处,打掉46个,保留十余个,以便潜伏者继续留在中共党内,掌握动态信息。这样,中统既不至于与中共完全脱节,还为「转变同志」提供升迁机会。
徐恩曾:
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甚至连莫斯科给它的机密命令,也常常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我们的档案中,曾保存着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些都是我们从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中搜获得来。
徐恩曾对再三破坏中共上海中央机关很后悔。因为从结果看,不如留中共中央在上海,反而容易了解并控制中共。中共中央挪入苏区后,反而无法接触,更无法控制。最最要命的后果是:给了毛泽东凭借武力从留苏派手中夺取党权。
徐恩曾认为抗战期间允许中共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给了中共一个合法宣传视窗,「实在是大大的失策。……新华日报所发出的纸张,给予国民政府的创伤,真无法估计。」还有新华日报资料室竟达80余人,「显系利用资料室的名义为掩护,进行搜集情报的工作。」
徐恩曾对陈独秀十分敬佩,「陈独秀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人中最值得尊敬的人物」。徐认为陈独秀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晚年主张至今值得借鉴。[31]
万亚刚提供重要信息
万亚刚的忆文进一步证明制延安不存在「特务大军」,因为派往延安的国民党特务很难站住脚,不是「叛变」就是「消极」了——
杜×(按:衡。中共陜西省委书记,出身红26军的「转变分子」)去西安办小型训练班,招训青年去延安「抗大」卧底,先后派遣二、三十人,都如断线的风筝,一去无踪。
万亚刚还留下一大悬念与一个问号:
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自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历年来出版很多有关中共的第一手资料,至今犹为美、日研究机构和图书馆所珍藏。但中共到了延安之后,线索全部中断,对中共的动态便一无所知。
那么,混入中共内部(从中央到各省)的奸细是谁?中共现有党史可是一个都未提及,是不知道还是出于避讳?至于万亚刚的问号,他认为按当时国民党政策,瞿秋白写下〈多余的话〉,符合「自新」标准,可以免死。「为什么杀瞿?」万亚刚认为至今为谜,故撰〈瞿秋白「就义」之谜〉:
他写这篇自白(按:〈多余的话〉),用这一番心思,他有求生的意念,却没有明白说出,只说已对政治极度厌倦,使人意识到他若重获自由,将和共党分道扬镳了。……瞿秋白这种厌倦政治的表示,已符合〈共产党员自首自新条例〉所订的宽赦条件,按往例可以不死。……瞿秋白被捕后的表现,既没有为求生而屈辱了身分,也不想做共产党的烈士。他写《多余的话》的动机,是想以退出政治来换取生命(这在当时是很可能的),是毫无疑义的,所以他既不是共产党的叛徒,也不是共产党的烈士,无以名之,就算他是时代的牺牲者吧!
当时的「中统」是全权处理共党案件的专职机构,处理瞿秋白,按照惯例必定建议将他押解到南京来审讯。瞿秋白一到南京,很可能成为丁玲之前的丁玲,因为保留一个瞿秋白,远比杀死他对国民党当局更为有利。所以瞿秋白之死,也出于中统的意外。[32]
结语
笔者久居大陆,长期接受共方讯息,近年接触台湾方面信息,多溅惊讶,解读出更多隐伏史褶的真相。研考国共之争,自应话听两面、史看两翼。偏听生暗,古训熠熠。
从结果看,国民党未能玩过共产党,「中统」未能玩过中共,共产党特工大批渗入国府机要部门。从战术上,中共利用青年对理想的忠诚,玩得好像更精细。1938年1月,董必武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密嘱即将进入胡宗南部的熊向晖(1919~2005):
要甘于做闲棋冷子,隐蔽党员身分,不发展党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表面上要同胡宗南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便受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1943年7月10日晚,周恩来在西安密嘱熊向晖:
要忍住,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胜利后再见。[33]
2015-3 上海;2018-1-25增补(普林斯顿)
[1] 王禹廷:〈专访陈立夫先生——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细说中统军统》,传统文学杂志社(台北)1992年,页8~15。
[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42、
[3]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红卫兵1969年8月编印,页475。
[4] 《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版,页91。
[5] 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47。
[6] 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页168。
[7]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页244~245。
[8] 周谷:〈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传记文学》(台北)第56卷第1期(1989-1),收入《中共地下党现形记》,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91年,页164、166。
[9] 张国栋:〈中统局始末记〉,《细说中统军统》,传统文学杂志社(台北)1992年,页14~15。
[10] 王禹廷:〈专访陈立夫先生——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细说中统军统》,传统文学杂志社(台北)1992年,页8~15。
[11]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底回忆》,天人出版公司(台北)1985年,序言,页2~3。
[12]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底回忆》,天人出版公司(台北)1985年,页77、41~46、57。
[13]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320~323、268。
[14]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305~310。
[15]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华书局(北京)1962年,页156。
[16] 张国栋:〈中统局始末记〉,《细说中统军统》,传统文学杂志社(台北)1992年,页11~13。
[17] 王禹廷:〈专访陈立夫先生——中国调统机构之创始及其经过〉,《细说中统军统》,传统文学杂志社(台北)1992年,页14~15。
[18]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底回忆》,天人出版公司(台北)1985年,页54~55。
[19] 张国栋:〈中统局始末记〉,《细说中统军统》,传统文学杂志社(台北)1992年,页13。
[20]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63~64、268。
[21]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底回忆》,天人出版公司(台北)1985年,页67~69。
[22]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底回忆》,天人出版公司(台北)1985年,页70~72。
[23] 甘露:〈毛主席和丁玲二三事〉,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页152。
[24] 萧军:《延安日记》,牛津出版社(香港)2013年,下卷,页222。
[25] 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页702~703。
[26] 马烽:〈历尽严冬梅更香——悼念丁玲同志〉,中国丁玲研究会编:《丁玲纪念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页192。
[27] 李辉:〈与陈明谈周扬〉,《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深圳)1998年,页106。
[28]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底回忆》,天人出版公司(台北)1985年,页95~98。
[29]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316~317。
[30] 王增如、李燕平编:《丁玲自叙》,团结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134。
[31]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战斗底回忆》,天人出版公司(台北)1985年,页91~94、158、95、165~166、76。
[32] 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台北)1995年,页272~273、14~15。
[33] 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原《人民日报》(北京),1991-1-7起连载。收入传记文学杂志社编:《中共地下党现形记》,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91年,第一辑,页11、24、27。
原载:《传记文学》(台湾)2016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