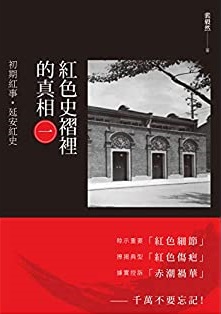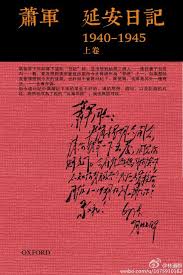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5)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5)
萧军:从延安开始的悲剧
辽宁义县人萧军(1907~1988),出身东北陆军讲武堂,当过张大帅的骑兵,身体健硕,性格奔放。1938年3月,萧军从临汾步行月余至延安。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康生等代表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宴请萧军及丁玲、徐懋庸、何思敬等文化人。席间,萧军发言不同意延安「为政治服务」的文艺倾向,认为这一倾向会降低文艺水平。随后,康生长篇发言,详细阐述中共文艺政策,不指名地批评了萧军,萧军听不下去,中途退席。[1]萧军一到延安,立即格格不入。
舒群一同到达延安,周扬欢迎舒群前往自己主持的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却不要萧军。[2]1942年春整风以前,萧军是延安「四大怪人」之一,其余三怪为翻译家王实味、艺术家塞克、音乐家冼星海。毛泽东邀请塞克谈话,竟遭塞克拒绝,说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毛泽东撤去岗哨,塞克这才由邓发陪同前往。[3] 那会儿的毛泽东,还不是「伟大领袖」。
整风开始后,萧军遭到「典型待遇」。1942年6月初,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大会,萧军与王实味素不相识,但十分不满会场上的蛮横混乱,归途中发了几句牢骚,被一女人听去,向「文抗」党组打了小报告。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四名代表向萧军抗议,要他赔礼道歉,萧军拒绝,写〈备忘录〉呈毛泽东。1942年10月19日,延安召开「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萧军当众宣读〈备忘录〉,公开为王实味鸣不平。党内外七位作家——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党外陈学昭、艾青,与萧军车轮大辩论,从晚上二十点一直到凌晨两点,两千多名与会者无一离场。主持大会的吴玉章见双方僵持不下,便打圆场:
萧军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我们一定有什么方式方法不对头的地方,使得萧军同志发这么大火!大家应当以团结为重,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应当检讨检讨!
萧军听了吴玉章的话,气消不少:
吴老的话还使我心平气和,这样吧,我先检讨检讨,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
丁玲斩钉截铁顶抗:
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也没错,百分之百全是你的错,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都没关系!
萧军气极:
百分之九十九我都揽过来了,这百分之一的错误你都不承认,既然如此,你尽管朋友遍天下,我这「一毛」也别附在你这「牛」身上,从今以后咱们就拉、蛋、倒!
萧军用手势重重地顿了三下,怒冲冲拂袖而去,大会不欢而散。深受刺激与侮辱的萧军,「审干」开始后受中组部招待所蔡主任挤兑,1942年12月3日下乡务农自养,脱离中共供给。
1944年3月,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接回萧军。萧军入中央学校,向副校长彭真提出入党。彭真表示热烈欢迎,但认为萧军自由不羁、个性好强,找萧军谈心:
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领导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强,你能做到具体服从吗?
萧军立答:
不能!我认为不对我就反对!更不能服从、照办!谁要是命令我、支使我,我立刻就会产生一种生理上的反感,这是我的弱点!难以克服的弱点!看来我还是留在党外吧!省得给党找麻烦![4]
萧军在「鲁艺」讲课:「小说是美丽的撒谎。」舒群阻拦:「你这样讲不对。」萧军一拧脖:「不对,我就不讲了!」柱着他的枣木手杖扭头就走。1945年夏,全院师生员工大会,萧军讲话时突然说:「艾青的诗是盲肠。」[5]
保持五四个性的萧军,对服从「生理上反感」。1948年7月25日,萧军才向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递交入党信。中组部长彭真汇报毛泽东。8月,经毛批准,东北局正式通知萧军——可参加党小组生活。此时东北局秘书长刘芝明领导、宋之的主编的《生活报》批判萧军的《文化报》,发生「两报争论」(引起国民党中央社关注)。[6]8月26日,《生活报》抓住《文化报》一句「各色帝国主义」,指责萧军影射「反苏」。[7]11月下旬,东北局定性萧军「三反分子」——反苏反共反人民,撤销一切职务,接收他的鲁迅文化出版社与《文化报》。萧军未能「参加党的生活」,终身留在中共之外。
萧军日记:
有一时期学生以骂「萧军」为进步。(1948-6-10)
夜间想到共产党对于我这种种的侮辱,我心甚寒凉,我如今什么人也不怀念了。(1948-9-23)[8]
此后,萧军人生坎坷三十年,差点成为个体行医户。
1980年代初,笔者在黑龙江大学亲聆萧军演讲,他指着陪伴的女儿说:她都30多岁了,江青竟不让她结婚,说这种黑子女结什么婚?难道要她去多生几个小反革命?1979年10月31日,萧军在全国四届文代会上发言:「从1949年起我就被埋土里了……我整整冬眠了30年!」[9]
萧军一生确实不服管教,1930年在东北陆军讲武堂因带头反抗暴政而被开除;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首日,毛泽东致开幕词后,萧军第一个发言,宣称政治、军事、文艺辈分平等,谁也不能领导谁,要像鲁迅那样绝不写颂扬文章,自己不仅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还要做世界第一作家。[10] 此言一出,即遭耻笑。
一生受压的萧军,这么一位敢于公开冲撞的反骨分子,1982年似乎仍被「改造」过来了:
我们能有今天的局面:祖国独立了,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了,以及开始走向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历史上每一寸小小的改革和进步,那全是由若干革命先行者的热血和头颅、生命和汗水、辛勤劳动、艰难忍耐……而换得来的。……我们不想到这一些,我们就渺小……一个人能够在这伟大与渺小之间的镜子面前照一照自己,那种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自负」的尾巴也可能会翘得要低一些,或者狠一下心自己动手割掉它,——总的说来人民并没有亏待您!……——一切以人民革命利益为依归。 [11]
晚年萧军看来还是被「党化」了,无法挣脱「时代局限」,全是那个时代的红色逻辑与「标准用语」,认为1980年代「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相对宽松的环境,已经千好万好,完全满足了。[12]「延安出身」的萧军,思想上尚存重大局限,认识不到个人自由才是现代民主最重要的地基。青年时代对服从「从生理上就会反感」的萧军,晚年稍得「社会承认」,便完全认同左倾逻辑,转身要求青年割去翘尾巴的「自负」。
延安一代绝大多数很难走出青年时代认定的价值范畴,很难对赤潮左说产生价值质疑,甚至不可能看到马列主义的反现代性。当然,1980年代的社会环境尚未为延安一代的整体反思提供历史可能。在信息封闭的条件下,无论早期红军的烧杀、苏区大肃反、1960年代初的大饥饿、文革大屠杀等,还是反思所需的西方现代思想,均被阻断。正因为如此,李慎之、李锐、胡绩伟等「老延安」的晚年反思鹤立鸡群、熠熠发光,可贵可敬。相形之下,萧军晚年「改造后」言论则体现了无法掩饰的悲剧性。
2006-11下旬于沪,略增补。
原载:《开放》(香港)2007年1月号
萧军《延安日记》的深度史料价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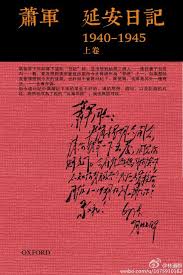
萧军(1907~1988),辽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人,1935年以长篇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鲁迅序)成名,与萧红同居六年,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首位「放炮」者。这位「鲁迅学生」反骨暴凸,1938年3月首赴延安、1940年6月再赴延安,久淹赤营,竟一生未入共党(想保持独立),成了性格决定命运的「时代典型」,最早吃瘪的赤士。1948年,萧军因主办的《文化报》「反苏」,在哈尔滨彻底倒掉,公开批判。文革后成为「出土文物」,1979年9月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讲演,笔者见过这位「不规则行星」,直观感受其赳赳性格,印象最深的一句,他指着陪行女儿——
她都三十几了,江青不许她结婚,说是右派的女儿结什么婚?难道再去生小右派?
2013年,得知香港出版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很有阅读渴望。凭着对萧军的了解——企图保持文学对政治的独立,《延安日记》一定「有货」!近十余年,笔者一直关注延安士林(2014年台湾版《乌托邦的幻灭——延安一代士林》),萧军《延安日记》对我具有专业诱惑。那份伸长脖颈的期待、那一个个深有意味的问号:这位个性作家最初如何呛水?如何不适应严苛「党性」?何以一直不入党?又如果被一点点党化、迷陷马列……
2006年,萧军《延安日记》首次露脸大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第333~453页,节选很小一部分。2008年,北京华夏出版社《萧军全集》,最后三卷日记,第十八~十九卷「延安日记」(有删节)。两次出版因不显山露水,未引学界关注,笔者亦未闻晓。2013年,香港牛津版《延安日记》单行本溅引海内外一些反响。不过,大陆评家囿于种种束缚,未能挖掘萧军《延安日记》深层次史料价值:萧军何以不适应延安环境?透露哪些重要信息?豁显哪些原点赤谬?对深析赤潮祸华有何独特价值?……
延安文化界热闹一时,红士云集,但留日记者甚寡,敢于直书者更少,萧军《延安日记》的真实度堪称独步,也是解析延安最典型的一只「麻雀」。
2015年1月,笔者访学港台,特购萧军《延安日记》。不料,31日回沪过罗湖边检被「滴」,随行拙妻、女硕士生均以「妨碍国家安全」遭搜身彻检,本人甚至被逼脱褪内裤。两本《延安日记》及刚刚出版的台版拙着《红色生活史》等十余册港台书刊被没收(还得写「自愿放弃」)。回沪后,只能托人从香港再购《延安日记》。
百万字萧军《延安日记》,最有兴趣的读者当然是作者同代人(尤其延安同事),一个时代终究首先属于那个时代的人。萧军对延安人事的品头论足、私言密语,关涉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一、感谢萧军及家人
日记的私密性真实性大大高于自传,公示于众的难度相应也高于传记。万事辩证,正因为如此这般的难度,日记才有晶莹珍稀的纯度。当年延安,保持「个性」不易,记录真实更难,完整保存下来难上加难。诸难相叠,形成萧军《延安日记》掂手的史料价值。
真诚感谢萧军的历史意识,详细记录每天活动及具体感受。《延安日记》最珍贵的内容就这些细节与心理活动,为还原这段被中共浓彩重抹的「延安时期」提供鲜活的第一手材料。
牛津版裸呈全貌,补上大陆华夏版删略部分——萧军自吹自擂及夫妇隐私。萧家犹豫再三,各种顾忌亦在情理之中。无论如何,他们最终决定「原始全貌」,应予致敬!经对比,华夏版删略部分不多,整段删略仅发现:1941年9月22日~12月29日。
直评他人不易,裸呈自己更难。没有萧家后人的配合,萧军这笔文化「存款」还将继续延宕「兑息」时间,无法在国家意识形态转型的档口利用这笔「积蓄」。如今,东风虽然落篷,检点赤潮祸华,阻力仍大。中共仍在屏蔽各种历史信息,大陆言论仍被规定「一面倒」,各种造假史料远未「正本清源」。萧军《延安日记》正好有助还原历史。
就笔者接触到的延安红士手记,陈学昭的「延安系列」(《延安访问记》、《延安岁月记》、《延安创作记》),李锐、范元甄的《通信、日记集》,以及其他各种延安回忆录,无论深广度与史料价值,均不及萧军《延安日记》。原因当然是萧军其时的劣势翻成今天的优势。萧军当年的「不规则个性」恰恰成为真实记录延安实貌的前提。不敢独立的随大溜者,身处方兴未艾的赤营,除了忍受延安阴暗面——既不敢想,更不敢做,万万不敢写。
1940年6月14日,萧军第二次抵达延安,慨怀澄清天下之志,自居「文学列宁」,不像其他青年在老红军前弯腰低眉,根本不敢平视「伟大的党」。桀傲不逊的性格、保持独立的自觉,萧军很快成为延安一怪。尽管「鲁迅学生」、成名作家,甚得中共重视,大大优待,仍严重水土不服,不久就在日记里再三再四叫嚷「离开」,一路叫到1943年「抢救运动」:
总之,我不宜于这地方,我不是政治化的人……我的目前唯一希望是离开这里,去过我的「小资产阶级」生活罢,让那些喜欢过这样的「新生活」的人来过这生活罢!(1943-6-5)
我知道我这样和他们分裂下去,对于整个政治影响是不利的,但对我却无什么不利(如果他们不用下流手段),如果他们没有很好的具体承认「不对」的表示,我决不和他们合作,对他们我决不宽恕。(1948-3-3)
如今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的时代了。(1948-3-6)
(东北局对他的「帮助会」)发言起始我是宣读了向共产党告别公开信。(1948-10-7)
共产党认识一个文艺工作者,使用一个文艺工作者,那只是为了装饰会场、写新闻纪事、晚会娱乐而已!这是一种悲哀!不管是封建、资本,以至社会主义时代——更是在中国,一个文艺工作者几乎仅是一种奴隶地位、装饰的废物……他们毫无独立、自尊的主张和「主人」的地位,同时也有一些自卑自贱的人,甘心安于这样地位,甘心做「婢女」!我是不容许这样被看待的,我要做个独立的真正的作家,因此我被他们看为不驯者,就引起了战斗!但我至死也不会屈服于「婢女」或「弄臣」地位的。我宁可永远放弃这生涯。(1949-6-26)[13]
不肯放弃独立性,刻意与中共保持距离,又对中共抱有幻想,还以为赤区会有保持独立性的空间,萧军在赤区只能「自找苦吃」,1942年就边缘化了,1943年底排挤下乡「自食其力」,1948年在哈尔滨彻底「栽」了,东北局正式发文〈对萧军问题的决定〉,认定他「反苏、反共、反人民」,关闭他的《文化报》、上交出版社,公开批判「萧军思想」,下放抚顺矿山。1949年后,所有延安红士都「浮」上来,萧军却「沉」下去,不仅未「分一杯羹」,甚至不得出席1949年7月首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萧军离开东北,东北局连手续都不给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萧军沦落失业,一路吃尽「革命罪」。随着封闭私营出版社,其作品无法出版,经济上穷困潦倒(1956年7月竟无钱奔父丧),1955年被迫弃文从医,上了几个月的针灸班。[14]1956-7-19日记——
生活的困难日甚一日地向我袭来了,除开卖收藏的一些文物而外,再就是出去卖劳力,我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抵抗它,也不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弄到钱!凡是同情我的,能够帮助我的,也全是不幸的人,即使原来是幸福的人,一接触我也要成为不幸的,我几乎成了个不祥的人![15]
其后的「肃反」、「反右」,虽未打为「反革命」、「右派」,却一次次公开点名陪绑,《文艺报》活靶子,直至铜头皮带触及肌肤的文革,株连众多亲友三十年。1975年1月,幼女萧黛(高二生)不准入团——「未与父亲划清界线」,精神分裂,因尿毒症夭折。[16]
「出版后记」未交代日记保存过程,如何度过1949~1979年的「严寒岁月」。查大陆华夏版《萧军全集》第十八卷,其女萧耘卷首语:文革初期抄家抄走「日记」,萧军见形势太严峻,停止日记。[17]1960~1962年、1965年、1967年、1969年,全年缺失;1966年仅记九天。1979年2月8日,萧家与军代表大吵一架后,「今日下午耘儿终于把我五十几册日记取回……自从1966年8月25日他们把这些日记等抄走以后,到今天已经12个年头了。」[18]
原以为萧军与毛泽东、江青关系一般般,《延安日记》披露整风前两家一度走动很勤。萧军与江青、王德芬(萧妻)与毛泽东都跳过舞。萧军那篇甚遭诟病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解放日报》1942-4-8)[19],四月四日经毛泽东亲审。1949年后,萧军几次递函中南海,毛江对这位「延安朋友」置之不理,一点都不顾惜当年的「战斗友情」。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将并未「划右」的萧军与丁玲、罗烽、艾青绑在一起,指延安时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是「反党反人民的……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蒋介石反动派」。[20]
二、闪光直感
很快就从《延安日记》中看到「宝贝」——
我知道文化人如今是纷纷而来,将来一定要纷纷而去。(1941-2-16)
我预感到这个党是没有阶级基础的党,虽然它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它也想和这阶级成为血肉,但我总感到它是悬空的,它虽然新兴不久,已经看到了败落的现象,这使我很悲痛!(1942-10-3)
这是个充满封建性的党,很少无产阶级气氛。它必须要进步、改造,否则就有要替代它的。(1943-5-11)
总之,这里的人,慢慢他们将要自己不会思索了、个性消灭了——虽然这不会久长,他们正被一种政治的力强制地僵化着,但他们总要有苏醒底一天——这是可怕的!(1943-5-15)
这乡上的干部——乡长、指导员等——几乎全是流氓成分,鬼鬼祟祟,全无正气。因此我想到,共产党如果不认真励精图治,训练、筛选、提拔……像样的干部,它负起改造中国的大任是不可能的。(1944-2-25)
我知道无论什么党,他们唯一需要的是「愚蠢的忠心」,其次才是其它。他们决不愿意真正为真理而战斗的人在自己营内,这样一来他们就要咬死他。(1944-2-17)
半年后,萧军无法忍受延安缺乏批评的氛围:
延安无舆论,从我这里就要建立舆论。(1941-2-2)
没一点独立脊梁与思考能力,能留下如此「反动」墨迹么?能要求至今都同志尚须努力的「建立舆论」么?萧军如此不满现实,当然在延安「吃不开」。萧军终身未入共党,根子就在「主观障碍」:
我一生将不能随着别人任何指导而行走的,这也就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一个党员唯一的理由。——我要自己走啊!(1943-3-14)
其稍后的《东北日记》也有闪光点——
我也不急于去东北,我也知道共产党并不十分重视「作家」,也不理解我底价值,所以我也不需要加入共产党。一切让他们自己去弄好了,我还是静静走自己的路,等到他们真正认识了我、需要我时,那时再说。所谓「上赶着不是买卖」。……即使到东北,我也看情形,看共产党的态度,决定我底态度。能够合作到什么程度便到什么程度,太热情的结果常是相反的。浅薄和短视、势利,这是一般党人们通病。(1946-8-29)
这是个痛苦的而又哭笑不得的时代!(1947-8-18)
徐说了一些苏联军抢掠奸淫情形,令人为这社会主义国家感到羞惭!(1947-10-10)
夜间同芬去看《血海深仇》,这剧是长而又空,公式化、脸谱化,不管内容、形式、音乐、演技……全是一无可取。它总在企图勉强人底感情,一开始就哭、就哀求……很使人讨厌,他们对于东北农民性格是忽略了。这脱胎于《白毛女》(我是最讨厌这戏的)。每个人都看得打哈欠,尽义务。从这些演员和导演以至领导者们,他们全忽略了艺术的学习,跟着政治任务作文章。(1948-3-9)
中国共产党到一定时期一定会有分裂!世界革命阵营中也正在开始分裂!反革命阵营中也在分裂!就在这分裂、统一,统一、分裂中,人类还要被蹂躙近百年罢?(1949-8-6)
俄国人要做世界人类领导者这是一种传统思想和欲望,慢慢就会得到证明。因此我对人类前途不感到乐观。(1949-8-31)[21]
三、实貌细节
萧军《延安日记》扯下了「红色圣地」的罩衣。中共至今仍在重彩浓绘龙兴之地的延安,还想保持何其芳〈我歌唱延安〉(1938)的调子:
错误在延安不能长成起来……延安这个名字包括着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成天工作着,笑着,而且歌唱着。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的自由呼吸或者我们生来要把童话变成现实。[22]
笔者当然不相信红色文艺的神化描绘,凭常识也能推知延安必有阴暗面。但常识只能据以质疑,无法定谳。萧军提供了第一手证据——
这里开始制造「谄上」的传统。「当差」的风气在这里很盛行,一些人不是在革命、不是在工作,完全把自己的地位造起来,然后慢慢地爬。这种新兴的官僚主义是革命前途的一种暗影。(1940-8-15)
这里办事,无论什么地方全是庸俗,迟滞和凌乱。(1941-2-15)
对于这里的人,越来越感到难以容忍了,他们是自私而卑俗,官僚气到处浓厚!我真想离开这里了。(1941-2-16)
这里新兴的共产党人,他们大部分全具备着这社会本有的恶德啊!(1942-2-17)
下级干部贪污腐化,「老一套」……军队的纪律也不好了……人民逃避兵役,并不如报上所说「母送儿子去当兵」……这是仅有的偶然现象……人民对两个政权全是冷漠的……报纸只有区党部宣传科长看。(1942-10-2)
这里的居民只感到对公家尽义务的负担,却不见权利的享受。比方一些工作——除开要粮草及人工以外——其余的文化、卫生、教育……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从死孩子的惊人数目可知)这使我想起了一些外国传教士们底厉害了。他们在直观上只有布施没有需索,而且是「韧」性战的。这一点共产党是差得远的。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和政府是没有思想、感情上的连结的,他们只感到「谁坐皇帝给谁纳税」的义务感觉啊!(1943-12-10)
边区百姓对中共政权增加公粮的态度——
他(按:毛泽东)告诉我为了增加十万石粮,延安百姓跑了六百家,边境跑了四百家。(1942-4-4)
后来泛滥全国的形式主义,延安已习以为常,酿出术语「五分钟观念」[23]:
延安一些规定计划等全是虎头蛇尾,有形式无内容。这一回也无例外,不信任了。(1943-4-6)
「不宜居」,萧军《延安日记》主旋律之一,抵延两个月后就开始吐槽:
我的心受伤了!我感觉到这不是「八路军」,简直是一群低级的野兽!那是看不到一点教养的痕迹!我不信任他们对于老百姓不欺压!因为仅仅是在他们「中央」的门前,全是如此,其它地方不问可知。如果在别的地方,他们一定要殴打我,而后不认账,还要添上一些侮辱的东西!我虽然懂得他们,但我的感情再也不能原谅他们了,我要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给与我的侮辱与损害是别处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还不能发声!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宁可到外面去住国民党的监狱!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我不愿再在这里受「优待」了!啊!丑恶的东西们再见罢!让我到「地狱」里去生活吧!我愿意在那里战死,也不愿在这「天堂」里生活。……怀着耻辱和失望再投回到地狱里去罢!让地狱的火烧死我罢!我不愿再「卑下的」生活在这光照里。……他们还要革命,他们还要从事文艺吗?死亡了吧!(1940-9-7)
我渴念着离开此地去过一种「社会的」生活,这里的人群真使我厌烦了。(1942-9-10)
如今每个知识分子几乎全在度着心灵的炼狱的生活!(1943-5-13)
虽然是星期日,却毫无乐趣,生活在这里,简直是生活在无味的小客栈里,一切只是等待消磨旅程的日子!(1945-2-25)
「延安四怪」之一塞克私议:共产党比国民党还……(限制了他的自由)。(1944-8-29)
萧军评价「抢救运动」效果:
此次共产党的信誉,在知识分子中降落得甚为可悲,离心离德已经成了每一个知识分子党员——除开那些投机拍马者——心中的暗礁,只要遇到革命低潮时,它们一定要显露出来。我看了这现象,心情甚为闷塞!多少人的生命无声地死掉了!多少人的精力,无声地浪费了!多少老百姓的「公粮」不必要地浪费了!(1945-2-20)
1945年,萧军密友李又然(1906~1984)批评「鲁艺」:
教育无计划、行政无效率、领导人无能与无耻。(1945-7-23)
萧军可能至死都不知道,整风后期(1943年秋),他就被怀疑是「国特」或「托派」。中共社会部治安科长陈龙指派慕丰韵(1919~2012),跟踪调查萧军。陈科长对小慕说:
他对延安的生活、工作环境不满意,有时说三道四,甚至公开吵闹,嚷着要到西安去,但他又不走。机关群众对他有不少反映,要求中央社会部弄清楚萧军的是个什么人呢。你可以前方调干的身分住进蓝家坪招待所,每天观察他接触些什么人,都到哪里去就行了。但不能让他察觉,要掩护好自己的身分。[24]
三、延安特权
延安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高干仍有相当特权。王实味、丁玲的杂文稍撩一角,就遭打压。延安士林只准看「本质」的光明面,只能歌颂光明当「歌德」,必须忽略「非本质」的阴暗面,否则就是「缺德」。笔者当然很关注这方面——
遇见毛泽东的老婆骑在马上,跑着去高级干部休养所去了。这里连个作家休养所也没有,无论哪里的特权者,总是选择最好的肉给自己吃的。(1941-5-13)
下午去看芬,在医院中我听到了很多丑恶的事情!①李伯钊自带小鬼,每天做饭五次,罐头、牛乳、鸡蛋、香肠等应有尽有,馒头也是白的。②据小鬼说,杨尚昆买鸡蛋总是成筐的,每天早晨以牛乳、鸡蛋、饼干代早餐。③毛泽东女人生产时,不独自带看护,而且门前有持枪卫兵。产后大宴宾客。去看病人时,总是坐汽车一直开进去,并不按时间。④一个法院的院长女人住单间,彭家伦女人生产也住单间。⑤各总务人员总是吃香烟,买二十几元钱一斤的鱼,各种蔬菜由外面西安等地带来…… 虽然他们的津贴各种是四元或五元。我懂得了,这卑污地存在原来到处一样,我知道中国革命的路还是遥远的。……我应该离开此地了,虽然外面有政治威胁、经济的压迫……但在这里,我每天总被一种内心的痛苦啮咬着……(1941-6-24)
首长特权还是全方位的。1941-7-21「鲁艺」晚会,时间过了,观众拥挤着鼓掌要求开幕。主持人站起来:我们今天主要是招待首长的……你们着急也没有用……
主持人要求座位向后退三排,一会儿又报告:给首长打电话去,说坐汽车出发了,再等二十分钟。
半小时后首长仍未来,主持人只得宣布:我们开始吧,但我们还希望在节目中间首长能来……前三排座位还不要动!(1941-7-21)
首长优势更体现在性爱上——
高级的人可以依仗自己的地位等优越条件,对同志的女人实行引诱。常常是一个庸俗的意志薄弱的、情操卑下的女人被掠夺去了!男人便陷在无涯的苦痛里!这例子是很多的。我预备将来写一篇小说,名字定为《坟前》,以此为题材暴露这种可耻的东西。(1940-10-2)
延安作家的生活待遇亦等级森严——
这里的作家共分——
特等:如茅盾,小厨房、双窑洞、男勤务和女勤务,开销不限。
甲等:每月十二元津贴,不做正常工作。
乙等:八元。
丙等:六元。
工作人员:四元。
李又然为了丙等作家发脾气了。(1940-9-26)
四、人际关系
《延安日记》涉及延安文艺界复杂人际关系,延安士林乃历代士林人际关系「复杂之最」,1949年后影响至少上万「文艺工作者」的人生际遇。
抵延七个月,萧军统计左翼阵营中的仇人——「九面楚歌」:
①郭沫若系统;②田汉系统;③阳翰笙系统;④国民党系统;⑤成仿吾系统;⑥周扬系统;⑦萧三系统;⑧阎锡山系统;⑨茅盾系统。(1941-1-16)
这里反对我的人已经有一批可观的数目了:周扬、雪苇、何其芳、立波、丁玲。(1941-7-29)
这会场中几乎有三分之一是我的反对者。(1941-8-3)
1942年,十年铁杆「马仔」罗烽、舒群也渐离萧军。萧军鸣叹:「年来故友飘萧尽!」(1942-1-17)「对于任何党员,一定要保持相当距离,不发生友情关系。」(1943-3-4)
大骂者:萧三、艾青、张仃。萧三对萧军妻王德芬曾怀私情,萧军与之「不同戴天」。
贬斥者:王德芬、胡乔木、郭沫若、茅盾、柯仲平、刘白羽、杜矢甲、草明、陈波儿、李又然、高阳、陈布文、曾克、白朗、端木蕻良(卑劣的人)。
有失敬语:王明、凯丰、林彪、陈云、李维汉、范文澜、曹禺(庸俗剧作者)、丁玲(心狭情薄)、周扬、何思敬、陈伯达、艾思奇、张琴秋、南汉宸、陈企霞、金灿然、王子野、高长虹、杜谈、陈唯实、张如心、齐燕铭、宋侃夫、严文井、周立波、徐懋庸、陈学昭(老女巫)、成仿吾。
郭沫若有热情无理性,茅盾有理性无热情。鲁迅理性高于热情,而不奔放澎湃!所以郭只能成为一个不成功的诗人,茅只能成为一个无诗趣的小说家。(1939-12-21)[25]
下午成仿吾来,欲请陈学昭等吃饭事。我和这些人是不能相与的。(1946-8-15)
这位妇人(按:白朗)曾咬过我,如今也时时企图咬倒我,可怜的愚昧的人。(1948-2-16)
罗烽从大连回来了,但我们没见过面。如今过去的朋友全已变成了敌意地存在,因此我也就要不受任何感情牵制对待一切了。(1949-1-29)
从私方面讲我和他(按:舒群)已不想再有什么友情。(1949-2-7)[26]
表扬者: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江丰。
宽恕者:吴奚如、罗烽、舒群。
萧军对王德芬(1920~ )抱怨最多——
她给与我的总是不愉快,病、啼哭,她不会创造爱情,她没有灵魂。她总是一根木棍似的没有枝叶也没有花朵。我是忍受一个阴沉天气那样忍受地生活着。她已经失却了青年的心,一个呆板地中年乡村女人,而时时还要耍娇脾气,缺乏弹性。(1939-1-18)
她是一个只知道要糖果,而从不知道糖果来源的孩子。她是只想到自己的人。她没有人类的同情,也没有革命和追求的热情,她对我的劳力、精神、成就……是不了解、不爱惜……是冷漠的。她总在诉说自己的委屈、抱怨别人……我是不爱这样性格的人。她总是很少给过我兴奋、快乐和鼓励,她对于什么也不理解,也不求理解……我对芬是冷淡的,更是她那木然不能给人以活力的性格。女人病倒在床上时,那是再丑恶也没有的动物,而叫起来那更是丑恶。晚上五时又去看了她一次,她还是在流泪,这泪对于我只是憎恶。(1939-1-20)
一个男人不应该尽想在女人身上寻知己,这是最愚蠢的事!你只要在女人身上寻到你所要的就对了,不要非分。女人的智能和感情,大致的水平全差不多。知一个女人可以描写一千个女人。(1939-10-9)[27]
教育一个老婆何等艰难啊!(1942-10-15)
我们底心情感觉为何竟差得这样远,隔膜得这样厉害啊!……她是爱多自己享受,吝于助人的性格。我们底性格、思想、精神、作风……几乎全是相反的啊!(1946-8-3)
她既没有好的家庭教育,又没很好的学校教育、没有社会经验……有时狭隘固执得可怜。她是永远也不懂用灵魂思想的人。(1947-10-6)[28]
我们就这样没有心灵交感地生活了二十年!她怪我想得太多,我怪她想得太少,就这样周期地矛盾着……(1958-11-28)[29]
萧军甚感孤独寂寞——
在这里,连一个也找不到能够交谈交谈心情的人,更不必说谈艺术、文学。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吃和睡!(1944-7-24)
此地人无所谓「情感的互助」,只是「功利底交换」。(1944-12-20)
人心底险诈与卑劣竟堕落如此的地步了!所谓革命阵营之中。(1945-2-11)
群(按:舒群)也谈了一些关于红的事,他们全不满意她跟了那样一个卑劣的人(按:端木蕻良)。(1940-4-8)[30]
五、深度「爆料」
萧军评价一位东北女孩的革命动机:
她是十六岁就参加救亡运动的,看得出她们的潜意识里还是为了打天下将来「分一杯羹」,她们全等待着革命成功「作功臣」,可叹!(1941-7-6)
萧军也有「得胜」情结:
我是要承继这些人们(按:摩西、耶苏)底长处,准备我执掌中国政权的一天!(1941-10-16)
为救治邹韬奋,中共投入钜资——政治资本是为这里所看重的。听说为了邹治病,共产党不惜花费二十万元钱。我想他们对于一个无资本的穷作家,他们是不会如此的。(1944-11-23)
周扬对毛泽东竟有失敬语:对于毛……我早先是无条件五体投地的敬和爱……如今我有些怕和距离了……(1945-3-13)
敏感捕捉到江青的瞬间心理:蓝苹来,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她似乎还在怀念着章泯。她希望我们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也是这样希望着,他们的生活太枯寂。(1941-8-14)
1942年,延安有一场离婚高潮:
萧劲光的离婚、朱宝庭的结婚、郭化若的离婚等,这几乎成了近来新闻底高潮。(1942-3-20)
鲁迅纪念会,发通知近百人,仅来17位——我对于延安人这样形式底尊敬鲁迅,实质是敷衍、冷淡的,感到很气愤……这里的人,凡事全乐意列名而不工作。(1941-1-15)
萧军如此评价延安戏剧代表作《白毛女》:
夜间去看《白毛女人》,费去了六、七个钟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的最差的戏。(1945-5-21)
延安日常生活:开会学习、唱歌跳舞、演戏看戏、闲聚聊天,读写时间并不多。不少延安青年「有舞必跳、有牌必打、有喉必歌、有牛必吹、有会必到。」最初两年,萧军仅编一本《文艺月报》(发行不足两百),并无实质工作。(1943-4-9)
1943年底,萧军因受不了中组部蓝家坪招待所长的挤兑,下乡刘庄「自食其力」,四个月后返城「回公家」,萧妻说毛泽东派胡乔木「路过」接回。《延安日记》揭露实情:迫于生活压力(拖着一妻两儿),萧军呈函县委书记王丕年,表明放弃种地计划,决定「回公家」(1944-2-25~29)。[31]胡乔木来「请」,无非针对其性格,提供下台阶。
1948年7月25日,萧军在哈尔滨申请入党,8月12日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约谈:
接到我那入党信后,即与东北局交换了意见,他们是同意的,接着打电报去中央,前几天才回电。据说因我思想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很浓厚,本不合党底要求,但因我一直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决定接受入党……他说:「一些毛病可以到党内来改正。谁全是有毛病的,慢慢克服。在党内就是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要服从多数去执行,这在一个老党员也还不容易。」[32]
正要办理手续,因爆发「两报争论」(萧军《文化报》与宋之的《生活报》)及对萧军的批判,萧军彻底边缘化,入党流程中止,终身未入党。
六、评论毛、江
萧军敢于平视毛泽东,指说毛缺陷。
他存在着封建的东西,他看西洋小说太少,要在里面求知识。(1941-10-2)
他是爱荣誉容易感动的,但也容易飘忽过去。(1942-5-10)
共产党正在被一些无远见的、表面谦卑而实骄傲的人们统治着。毛泽东是个感性的人物,不是一个深刻、切实的人物,他是明敏有余、思考的远见不足。他们将来也会感自己的落伍。也许还要有一次很重的跌伤。他们的向心力是表面的、薄弱的……(1942-7-9)
据说毛泽东自己说他的知识等是从报章、杂志上得来的。这使我明白了他底深刻性底限制性了。(1943-9-14)
毛并不是思想周密的人。飘浮是他的缺点。(1943-10-5)
他高于他同人们一般的文化水平和天赋的聪敏是不可否认的,但他和马列斯以及鲁迅先生等比较起来,是还相差很远的。……缺乏有系统的学问……他缺乏一种雄浑厚重深沉的魄力……他给予人的印象是如此他的字迹一般,无力和不深刻。(1944-11-27)
评江青:
江青是浅薄的,有些地方不自然、矜持。她是并不理解毛底为人。(1941-10-16)
她是一切要充内行,因为缺乏教养和知识,结果要闹笑话。(1942-5-9)
萧军还有一则预判:
如果毛泽东一死,中共要有一次骚乱的分裂,那角色应是有人和周恩来争风。(1941-8-8)
七、萧军其人
评人露己。萧军意气自雄地评人论事,当然也得接受「被读」。这一点,正是萧家后人顾忌所在。萧军毛病确实不少,刚升入长春高小三年级(相当如今初一),因顶撞教师被开除;1925年(18岁)当骑兵;21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行伍六年,「九·一八」后从文。[33] 萧军相当自恋——
吟(按:萧红)是一个不能创造自己生活环境的人,而自尊心很强,这样人将要痛苦一生。
我有真挚的深厚的诗人的热情,这使我欢喜,也是我苦痛的根源。晨间在镜子,看到自己的面容,很美丽,更是那两条迷人的唇……清澈的眼睛,不染半点俗气,那时我的心胸也正澄清。(1937-5-15)[34]
萧军性喜热闹,交结甚广,潜心阅读时间有限,阅读书目及心得一般般,轻才小慧,也就中等知识分子,牛皮却吹得野豁豁(沪俚),大话不断。三十四、五岁了,莫说传统士子的含蓄自抑,最基本的谦虚都没有。自封「文学列宁」,想引导民族与人类的文化文学方向,确实没边没际,萧家后人都感觉太那个,大陆华夏版故有一些删略。
总是意识着自己总有掌握中国政权的一天,创造历史和写历史我应该兼着。(1941-10-9,华夏版删)
我相信我是有能力把中国人民领导到更好的生活路上去的。准备等待啊!我决不会仅是一个作家的。(1941-10-17,华夏版删)
读了一篇〈人底列宁〉,觉得他的性格有些地方很像自己。我将是文学上的列宁。(1941-11-4,华夏版删)
我要做一个整个人类的文化承继者和综合与开拓者啊!我的先生(按:鲁迅)他仅是民族的,我要是人类的啊!要由我这里把整个人类的文化、文学,导向一个正当的方向啊,给它以指路和奠基。(1941-12-19,华夏版删)
我是大美者。美是一切永恒的真理和宗教。(1942-1-21)
又把〈高尔基论列宁〉读了一次,觉得自己有些气质、作风、性格……确近乎这伟人、大孩子。可惜我只是个文学上的列宁。(1942-5-28)
我是王者之才而非臣者才。(1942-11-5)
我要为这个世纪思想、文学、政治底领导者之一。(1943-1-12)
我不独要赶过我一切同时代的人,还要赶过我的前一代。(1943-2-6)
我相信我的力量和精神。我知道我同时代的人是任何人也不能和我相比的。(1943-9-20)
萧军自我感觉超好,「前无古人」,自许长城都打不住。萧军欣然接受别人恭维:
「我们东方如果有最大天才的话,那就是你啊!你完全是对的!」ZH感叹地向我说。我愿意坦然地承受这寓言。(1942-1-22)
连最尊敬的鲁迅都只是「民族」的,惟他自己才可能是「人类」的!事实上,萧军也就三流作家耳,二流都不太上得去。鲁迅的思想倾向近年在大陆亦渐受质疑,但一流作家的地位仍难动摇。
萧军的历史观亦明显失偏,竟将张献忠列为崇拜对象(上卷·页357)。对中共革命也存在严重认识偏差:
革命却是一种真正人性底解放和提高。(1941-6-18)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底政策,我站在革命立场上,为小资产阶级甚至民族资产阶级主持一种「合理」的权利,使他们能自愿、积极地发挥出他们底力量,这才是对于政策与革命真正有力的。爱护革命决不是在「爱宠」革命中底缺点而加以合理化。更不是对于不正的作风加以褒扬。(1948-9-29)[35]
阅读趣味上,萧军深陷「阶级论」,斥清代名篇《浮生六记》为「寄生阶级的可怜相与无能生活的窘相」(1942-9-28)。其后的《东北日记》竟有一段缺乏基本人道的文字:
前天听他们说,已把一万人送到炭坑里去工作了。这些人大部分为小偷、流民,有很多是患花柳病者,虽然给他们充分的食物,但对这些人底死亡是并不可惜的。因为他们对社会除开害,再无用处。这是一种革命的「残忍」。[36]
不过,萧军之所以成为延安的「一个异数」,除了性格原因,也还有价值观方面的因素,多少保留了一点人性,未被革命性彻底俘虏——
我底道德最高的标准是给人以快乐,不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多助人、多谅人。(1946-6-8)[37]
萧军明知在延安格格难入,清晰认识到中共只要作家「公务式服从」[38],何以久淹赤营不去?除了老婆孩子等生活牵累(日记多处记载向组织要钱,东北时期则向东北局要「零用费」),关键还是延安红旗飘扬的马列主义。他认为「一直和共产党——这个进步的力量——保持着忠诚和『谏友』的地位关系。」[39]萧军为共产图纸所惑,虽与中共合不来,但愿从旁帮助中共。萧军进入延安一代十分普遍的认识误区——以抽象整体否定自己接触到的现实具体:中共代表进步力量,正在从事人类最伟大的事业(「我会终身拥护它」),仅仅自己接触的文化圈庸俗肮脏。[40]
对于整个共产党,它是代表进步力量的,我会终生拥护它,但对于个别人——更是文化圈这些人——是蔑视的,他们庸俗而无能、嫉妒而偏狭,官迷更甚。我由舒群和罗烽这两人是具体表现了。[41]
但中共怎么会容忍他的「独立性」呢?1949年2月13日,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当面批评萧军的《文化报》——
你看看,哪有一份像你这样的报纸?给你拿钱办报纸,供给你吃喝,让你来骂我们,如果我那时在,决不允许你这样干。
1949年2月23日,《东北日报》以大号标题及整版刊登刘芝明对萧军的批判文章。4月2日,《东北日报》刊出东北局对萧军的处分决定。[42]
对「性」的认识上,萧军也很超前——
健康的性生活,那是决定一切幸福的根源。我爱性的美丽,它是世界上最充实最美丽的东西。[43]
有认识便会有行动。萧军在私生活上相当「自由化」,一路犯错误。1947年春在哈尔滨与27岁女演员秦友梅有私,被东北局(舒群出面)强制离开哈尔滨,去了齐齐哈尔。[44]处理这一绯闻事件的罗烽,1948年7月居然也与秦友梅勾搭上,也遭组织处理。1948-7-25萧军日记——
……因找纸,(从舒群桌上)偶而发现一张纸头,上面写着罗烽和秦友梅恋爱事件,这我并不稀奇,我直截问舒群,罗烽对处理我和秦事件的动机?他惊讶我为什么问这问题:「你是否看了我桌子上的文件?」……他于是也只好把实情说了,罗烽此次调大连,就是第一步处分,将来处分还没决定,据说决不会轻。凯丰为此很气愤,其他人们也气愤。第一,他为领导者而不应有此行为。第二,关于恋爱事件他负责处置了若干人,首先是我,其次是徐、邬、林、柳、奚、赵……打击的打击了、处罚的处罚了……如今却临到了他的头上,而且依然和秦友梅在恋爱!第三,他声明断,但却未断。
我们推测,如果处分过重,他也许会走到自杀路上去。……一地的欺骗和虚伪,我不能原谅她了![45]
1953年在北京与房东张公度之女张大学偷情,育有私生女——萧鹰,1956年,萧军写信给已发配外地的张大学:「若有人追查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推到张公度身上,就说是他用你拉拢腐蚀我的。」张大学深受伤害。其父张公度(国民党少将)家风甚严,根本不知萧军与女儿偷情,事发后逼女堕胎并要女儿起诉萧军,张大学不肯,张公度赶女儿出门。接到萧军要她「嫁祸」于父的信,她不相信一贯自诩「不许人间摇尾生」的萧军也会出这样的馊主意。[46]可以想见:关东硬汉萧军若非政治压力实在太大,应不至于如此敢做不敢当,竟要小情人如此配合造假,留下人生重大瑕疵。不知何故,大陆华夏版《萧军全集》第二十卷「1950年代日记」,这段婚外情了无痕迹。看来,饶是萧军(或萧家后人),也很难全部端出自己。
1988年6月23日,萧军谢世。很幸运,未看到「六·四」与1992年后全面恢复私有化。同时,也很不幸,带着相当红色历史局限走人。1988年5月14日19∶30,萧军在医院病床前召集全家交代遗嘱,内有——
我平生的四个奋斗目标:求得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总算基本都达到了。我自己无论是用口还是用笔也尽了力,没什么遗憾了。[47]
萧军确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很「纯」的中共党员,「伟光正」确实冤枉了他大半生。这几句「政治遗嘱」清晰透射萧军重大思想局限,无论马列主义、中国共运、历史观,其识其见都停留于「初级阶段」,距离延安一代的「两头真」差了一大截。
结语
萧军抱着玫瑰色理想进入延安,又希望与中共保持一定距离,以文学抗衡政治,「成名作家」使他拥有记录真实的勇气,走出「性格即命运」的一生。延安红色士林一颗「不规则行星」,成了他一生价值的徽号。
《延安日记》精华在上卷,即萧军未被党化之前;下卷价值明显低下来,因为整风之效渐渐发酵,萧军渐渐自觉「伟大」起来——能够宽阔看待中共,「对于共产党能够原谅……过去滞塞的感情似乎得了一次沟通」(1943-7-5)。「还要顾虑到『党』的影响」(1943-7-7)。
1948年秋,萧军在东北被批判后,清晰意识到——
我在共产党人的眼中,虽然是它们一个忠实的乐队合奏者,而且具有相当高度的技术,但他们感到我常常发出不和谐的独奏或噪音,妨碍他们平板的统一。
1949年1月19日,萧军得知西柏坡中共中央复函东北局,认为公开批判他「有全国意义」,示意刚到东北的胡风不要「同情」萧军,这位「合奏者」仍保持相当「党性」——
只要对革命有利、对共产党有好处,我可容忍一切牺牲,任他们去做。[48]
当他从批判的「缺德」转为谀颂的「歌德」,漂离革命应为人民而非仅仅为党之价值中轴,记录内容从政治渐转生活,文字也就酸味渐浓。萧军自我感觉「伟大」之时,即《延安日记》价值递减之始。值得特别关注:1949年东北局公开批判并专门印行《萧军思想批判》,萧军日记中的「党性」反而大增,渐渐习惯从「积极面」看待中共,八股味渐浓,《东北日记》的史料价值大幅低于《延安日记》。
无论如何,萧军《延安日记》为延安研究提供了一份珍稀资料,为延安岁月保存了原汁原味的呼吸,裸呈萧军在「一元化」红色环境中扭曲变形的过程,最终人性输给党性——对「政治」从抗议到沉默再到有保留地认同,以至于明知中共讨厌他,对他的批判攻诘是「红色僧侣蹲在马克思主义上大小便」,他仍远远爱着中共——
(1949-2-26)夜间和芬谈,他们「批评」够了以后,我要正式向共产党表明我底态度——要平静地离开它们,我已不相信它们的「英明」和「公开」(以延安整风为例)。……我已放弃了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打算……我已经失掉了爱他们底热力,这是很难复苏的。……这是个「不幸」的恋爱,「遗憾」地离开。但我也还会远远地爱着他们……我相信,我也不会去寻找第二个爱人。
这里的「第二个爱人」,不外「社会理想」与「政治集团」。萧军此时还幻想中共十年后一定会承认他是「不可多得的『忠臣』和『功臣』」,为中共批判自己而损失威信悲苦着急。[49]萧军终身的痛苦都来源于他对马列的误信、对中共的误从。1955年,暴虐「肃反」正如火如荼,大陆急速滑向赤难深渊。1955-8-27萧军日记——
共产党在进步着,社会在进步着,人类在进步着,中国在变健康着……[50]
1980年代初,丁玲数次问美籍文学研究者李欧梵:「你为什么不研究我?我可以为你提供一手材料!」李欧梵不便回答,他对丁玲「没兴趣」。[51] 笔者对丁玲也兴趣不大,丁玲文学水平虽明显高于萧军,但大节上缺少萧军的「独立自由」,终身停留「嫁共不得」的低层次——打不醒的思想奴才,尤其整风后缺少萧军的「现代化元素」。如果不被打倒,丁玲也会像别人打倒她那样打倒别人。如此这般,亲萧军而远丁玲,也就成了中外红色士林研究者不期然而然的共同取向。
作家不幸史家幸。萧军虽然为「独立自由」支付很大代价,最终失之东隅收于桑榆,得到他最想要的价值——嵌名于史、留文于后,化个人生命为历史养分。作家萧军,其所有文学作品都不如这部《延安日记》斤量沉重,放射深远。
2015-4-25~5-26 上海(后增补)
[1] 徐懋庸:〈我和毛主席的一些接触〉,《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99。
[2] 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北京)1987年第4期,页106。
[3]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325。
[4] 王德芬:「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北京)1987年第4期,页110~113。
[5] 程远:〈我们的好院长〉,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87~88。
[6]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503。
[7] 张毓茂:〈重评「文化报事件」〉,《百年潮》(北京)2004年第11期,页70。
[8]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528~531、461。
[9] 萧军发言载全国四届文代会《简报》第49期(1979-11-5)。转引自秋石:《两个倔强的灵魂》,作家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206。
[10] 秋石:《两个倔强的灵魂》,作家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204。
[11] 萧军:《从临汾到延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
[12] 秋石:《两个倔强的灵魂》,作家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210。
[13]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397、399、512、704。
[14] 《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402~403、773。
[15] 《萧军日记补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553。
[16] 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301。
[17] 萧耘、建中:〈想说说这批「日记」〉,《萧军全集》第18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3~4。
[18] 《萧军日记补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749。
[19] 萧军此文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节有感〉,国民党印成反共小册,西安还将〈三八节有感〉编成戏上演。1957年反右,丁玲罪名之一即〈三八节有感〉。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958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9~20。
[21]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94、274、292、401、764、783。
[22] 何其芳:〈我歌唱延安〉(1938-11-16),《文艺战线》(延安)创刊号(1939-2);何其芳:〈论快乐〉。参见《何其芳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78~179、232。
[23] 萧军:《延安日记(1940~1945)》,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3年,下卷,页661。
[24] 慕丰韵:〈走进隐秘战线〉,《人民公安》(北京)1997年第23期。参见中国警察网,连结:http://www.cpd.com.cn/n3551/n3683/n76990/n76998/c346926/content.html
散木:《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谜案19件》,秀威信息公司2013年,页148~149。
[25] 《萧军日记补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281。
[26]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86、391、562、567。
[27] 《萧军日记补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93、96、210。
[28]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81、291。
[29] 《萧军日记补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599。
[30] 《萧军日记补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359。
[31]《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274~284。
[32]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490。
[33] 萧军:〈我的文学生涯简述〉(1978)、〈我的小传〉(1979),《萧军全集》第1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1~28。
[34] 《萧军日记补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8。
[35]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509。
[36] 萧军日记1949-1-5,《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338。
[37]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60。
[38] 萧军日记1951-12-24,《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660。
[39]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192。
[40] 萧军日记1949-1-25、31、2-5,《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349、351~353。
[41]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563。
[42]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570、580、619。
[43] 《萧军日记补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325。
[44] 萧军日记1947-4-1~7-1,《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22~53。
[45] 萧军:《东北日记(1946~19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481~482。
[46] 鲍旭东(萧鹰):〈父女如影——我与萧军的父女情〉,《看历史》(北京)2010年第7期。
[47] 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2003年,页345~346。
[48]《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370、347、356。
[49]《萧军全集》第20卷,华夏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406、371、402~403、414。
[50] 《萧军日记补遗》,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页528。
[51] 李欧梵︰〈读《延安日记》忆萧军 〉,《苹果日报》(香港)2013-4-13。
原载:《传记文学》(台湾)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