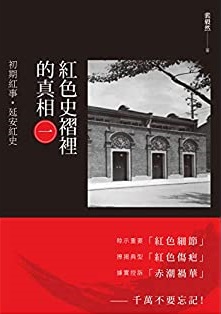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13)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13)
延安一代六十年
十年前,延安一代「两头真」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1923~2003),于国庆之夜撰下传世之文〈风雨苍黄五十年〉,对为之奋斗终身的赤色革命勇吐心声:
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二千前年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1]
中共当年闻之猛烈摇头,如今怕不得不暗暗点头了。岁月飞逝,又一个十年过去了,作为中共胜利的基干队伍延安一代知识分子,虽然整体凋零,但他们中的长寿者仍然健在,仍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艰难跋涉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老革命」的资格使他们在一定限度内享有对革命的反思权。
中共胜利的基干队伍
「延安一代」指抗战前后进入中共阵营的知青,一个抗大就出走十万(包括各地分校),「延安一代」总数估计在三十万以上。长征结束,西路军失败,南方抵陕红军仅二万余,若无延安一代的大量注血,中共不可能在抗战结束后具备与国民党争锋逐鹿之能力。从队伍构成上,仅有山上队伍的「枪杆子」,缺乏来自亭子间的「笔杆子」,也无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2001年,李慎之:
今年70岁到90岁这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当时都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人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民心,取得若干成就,这一年龄段的人的功劳是主要的。[2]
抗战第一年,八路军就从三万余扩至25万;抗战结束前,中共党员120万,军队近百万,国军亦不过200余万,初具对抗实力了。
中外史学界认为知识分子的走向预示着社会未来。抗战初期,国共都意识到谁抢到知识分子,谁就抢到天下。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三万,显然未能抢过共产党。
黄金一代
随着中共军政胜利,延安一代高调进城,「延安出身」成为进入新政权上流社会的入门券。文化界、思想界没有这一出身的昔日主角均退缩边缘,延安一代一统天下。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61人,主体即为延安知识分子,尤以延安中央研究院为核心。延安模式规范了数代人的思想,捏塑了数代人的价值观,也是文革之所以得以掀起的社会基础,最著名的文革要角(如江青、张春桥)均出自延安一代。1980年代,中共将延安时期视为「黄金时代」,呼延安一代为「黄金一代」。
抗战时期,延安一代中的精英陆续进入中共核心,参赞军机,成为中共各要角秘书,跻身梯队。1950年代是延安一代人生幸福度的最高峰值,「延安老干部」使他们拥有天然优越感,少年得志使他们志得意满。文革前,延安精英们大多升至省厅级。他们工作积极,整日忙碌,积极批评别人,认真检讨自己,活得好觉悟好辛苦,以为在为苦难的中国创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他们一个个热情高涨,挟革命以遨游,抱政治而长终。反右~文革,他们接受革命「淬火」,被打倒被批判,但未开始集体反思;文革后,延安一代从地方到中央全面接班。1980年代初最为艰难的改革初期,他们与红军一代中的开明派合力拱翻保守派,邓小平的改革思路主要依靠延安一代予以实施完善。随着改革深入,他们发现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别的,恰恰是自己思想深处最神圣的那些马列原则。
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往何处去」的焦点日益凸显,尤其「六四」后,大多「一二·九」学运出身的延安一代实在难以认同对学运的弹压,延安一代出现无可避免的分化。「六四」后中顾委本拟开除四人党籍,恰恰均为延安一代——李锐、李昌、于光远、杜润生。受打压的延安一代还有李慎之、任仲夷、梁湘、胡绩伟、王若水等。这一现象表明延安一代已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大革命一代、红军一代产生原则性分歧,无论价值理念还是政治判认均绽裂明显代沟。在中下层,大多数延安老干部震悚于六四枪声,开始思考肇因。他们不再埋头拉车,开始抬头看路。中央文件对他们思想的约束力明显大不如前。这一离心力的产生,自然大大加剧了起于1970年代末的「三信危机」——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信任危机、对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心危机。海外也出现被驱逐或「投奔自由世界」的延安人:许家屯、许良英、刘宾雁、王若望、戈扬、于浩成……
此前,延安一代也出现过大分化,如文革红人江青、叶群、张春桥、乔冠华、王力、关锋、马天水等,遭到延安一代的集体唾弃,但裂因局限于形而下道德范畴的好人坏人,这次大分化却是形而上层面对「主义」产生重大分歧,且不仅仅只是理论层面的「共产主义渺茫论」,更有对「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共同富裕」等实践层面的质疑。「黄金一代」出现的大分裂,注定具有「黄金」价值,从意识形态迅速扩渗经济领域,形成1992年回应「南巡指示」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
「两头真」
进入1990年代,延安一代分化加剧,出现一批思想上日益脱离官方主流的「两头真」——赵紫阳、李慎之、李锐、李普、胡绩伟、廖盖隆、杜导正、王若水、曾彦修、牧惠、穆广仁、安志文、彭迪、宗凤鸣、何家栋、何方……这批抵达「两头真」车站的延安人,实属极其痛苦的「意外」,或曰不愿面对的「意外」。他们十分清楚这一「意外」的历史内涵。因为,他们此时已清晰认识到:造成暴烈土改、惨酷镇反、悖谬反右、人祸大饥饿、疯狂文革、经济崩溃,最根本的致因乃是自己全力迎倡的赤色学说,这是比毛泽东都更强大的历史因素,也是更隐蔽更实质的祸祟。
有一些很简单的对比:1930年代,机关学校一说到蒋委员长就得并脚立正,华西大学的胡绩伟与几个同学故意在提问中多设「委员长」,去捉弄那位最讲究「立正」的教官。然而,委员长不过一个立正,不过几秒钟,「伟大领袖」则要戴像挥书、唱歌背语录、鞠躬请罪、无限忠于,万寿无疆、一日三次,远比「委员长」麻烦费时。怎么革了这么大一场命,最后竟是「胡汉三又回来了?!」 送走一位「立正」的委员长,迎来一位得「请罪」的毛主席,算哪门子事儿?!既然出现同一性的社会现象,出现「两头真」也就成了历史必然,因为他们最初的出发点就是「求真」。
这一次,「两头真」想得更远虑得更深,加之岁月催人,崦嵫日近,报国之心更切。如此这般,「两头真」成为推动中共政改的当代东林。京谚有云:「老年燃烧,青年取暖」,说的就是以延安老干部为核心的一批老革命在「关心政治」,青年一代则在尽情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历史发展角度,「两头真」的出现,含意重大。因为,较之延安一代当年的青年革命,老年的第二次「真情燃烧」可是带有经验沉淀的人生总结,不像当年青年革命仅凭理想去「绘图」,将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统统归结为政治黑暗所致,似乎换一种学说、换一批人,一切社会弊端都迎刃OK。此时的「两头真」对革命进行彻底反思,献毕生经验为政改薪禾,这当然不仅仅是「两头真」的最后成熟,也是中国社会整体理性层次的提高。能够认识到革命并非万能,革命可能要闯大祸,创新之时即可能出错之日,实在是一个世纪国际共运最沉重最核心的「人文遗产」。
演出结束盘总账
如今,左右两翼的延安一代的声音还很强烈,然毕竟都是九旬左右的老人了,演出基本结束,大幕即将垂闭。他们回首人生,不能不为自己与奋斗终身的「主义」盘盘账。左翼的巍巍、马宾等人,由于一仍旧腔,甚至要为「五人帮」平反,坚持已为实践证谬的马列原教旨,身后跟从者寡稀,日益成为延安一代健在者中的非主流,已无法与「两头真」对抗。真正能为延安一代自结账目的当然只能是「两头真」。
2008年,李锐先生说了两段大大超过〈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最后总结:
毛泽东们选择的「俄国人的路」,帮助中共党人经过共产革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是终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岂止是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简直就是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迟滞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运动不已,生灵涂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上亿人受到牵连,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间悲剧,使得国家、民族和社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迟滞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甚而至于发生「六四风波」,动用军队弹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导致了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场悲剧,所有这些,反思起来,都要从上个世纪「走俄国人的路」追根溯源。
无论是苏俄革命的经验,还是苏联的专制制度,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都是对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类普世价值的背离。十月革命74周年后,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事实证明,背离人类普世价值自由、民主、科学和法治,脱离人类文明依靠科学知识即智慧发展的规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都只能为自己敲响丧钟。这个结果,是中共早期创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国人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从一个错误的地方,移植了一个错误的样板。[3]
2007年,16岁赴延的何方先生也说:
应该说,我们的路就根本上走错了。我们建设的不但不是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而且连我们一直在批判的资本主义都不如。因为资本主义总还是在发展,而且发展得很快,我们却在后退,相对说来也退得很快。……1955年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的4.7%,1980年下降到2.5%。……2005年也仅占全世界总量的4.1%。这就是说,我们后来这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还没补够头二三十年的落后造成的差距,实在有点对不起祖先和后代。从这里也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来,我们究竟建设的是什么社会呢?
李慎之晚年迭发高论:
社会主义无非是争取平等,资本主义无非是保障自由。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追求。但是如果剥夺了自由,连追求平等的自由也没有了,所以自由先于平等。[4]
明确表述了追求自由先于平等,得先进入资本主义,然后才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真是完全背叛了国际共运的原始教旨——埋葬资本主义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前提。
无论左右两翼,延安一代都明白:三十年改革开放,国家经济起飞并非依靠「延安药方」,恰恰相反,正是放弃「延安药方」,改弦更张另起炉灶,才使国家得以挣脱左绳左箍,才得以遵循近在眼前的初级常识。
面对「两头真」否定之否定的自评成绩单,后人将如何评说呢?千山万水、雪山草地、头颅热血、改天换地,最后竟……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一位革命者顿足捶胸?价值取向上终一生而历二世,如此截然相反的大落差,石犹碎散,人何以堪!真是玩笑开大了,实在太大了。后人除了再发潼关长叹,除了从头收拾旧山河,从数代革命者的滴血经验中拣拾理性之结晶,还能怎样呢?
身系重望垂暮身
如今,「两头真」队伍不仅在悄然扩容,而且薪尽火传,身后跟上来解放一代、文革一代,终究是真神就有跟从者,是真理就有后来人。只是,垂暮之年的延安一代仍身系重望,成为海内外士林对中共改革托望之重心。以目前国情,他们由历史形成的地位声望,尚无人可替可代,还得指望他们发大声、放头炮,真是难为这些延安老人了。
延安一代六十年(仅指与中共建政同步时段),「两头真」以彻底反思之态评述这段尚带体温的历史,当然大大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的发展。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第一要素即取决于对当代经验的利用速率。「两头真」能够自裁其谬自检其误,实在是为延安一代挣回最后的历史地位。
2009-8-23于沪·三湘
[1] 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动态》(香港)2000年5月号。参见《李慎之文集》,2003年自印本,上册,页7。
[2] 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历史的先声》序〉,笑蜀编:《历史的先声》,博思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香港)2002年,页21。
[3] 李锐:〈《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序〉,王来棣采编《中共创始人访谈录》,明镜出版社(香港)2008年,页10~11、8。
《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8期刊载此文,删去「同人类文明背道而驰」与涉及「六四」两句,页44、43。
[4] 丁东:《精神的流浪——丁东自述》,秀威信息公司(台北)2008年,页335。
原载:《开放》(香港)2009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