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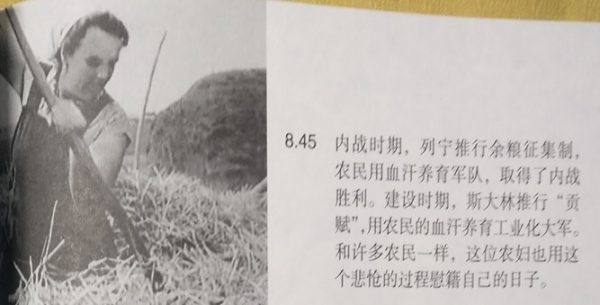
俄国各界的反思(31)
俄罗斯右翼政党对苏联解体的看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一些右翼政党联合成立“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联盟。“右翼力量联盟”于2001年5月26日召开了建党代表大会。在此之前,该党内部各派别组织(如“青年俄罗斯”、“共同事业”、“俄罗斯民主选择”等)按规定都宣布解散。该联盟的领导人为涅姆佐夫、丘拜斯、盖达尔。 “亚博卢”联盟中央理事会于2001年12月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政党法》的要求把该联盟改建成政党。该联盟的领导人为亚夫林斯基。2002年3月,另一右翼组织“自由主义俄罗斯”召开代表大会,正式组成政党。该党的领导人为谢尔盖.尤申科夫。
除了上述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之外,在俄国还有一些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极右翼政党,例如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主党”,以巴尔卡绍夫为首的“俄罗斯民族统一党”等。
关于苏联解体问题,俄罗斯右翼政党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
1) 从总体上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俄罗斯民主选择”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写道: “上世纪80年代俄国所经历的深刻危机是有原因的,其原因不应在外部力量的破坏性活动或国内敌人中去寻找,而应在本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本质是极权的)国家中去寻找。” “1917年十月政变中断了俄国的自然发展进程。民主思想的幼苗在20世纪初蒸蒸日上的俄国渐渐地集聚着力量,但却遭到粗暴的践踏。在苏共的领导下,国家塑造了‘我们时代的智慧、信仰和品格’,这是任何独裁者最大的理想。也就是说,国内的所有生活由一个统一的中心硬性地、经常是残酷地来决定和控制,形成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行为和统一的意见,等等。”
“苏共领导不仅靠石油美元和出卖原料为大多数居民提供微薄的工资和社会保障,使我国人民脱离了外部世界,还从意识形态上不断愚弄大众,制造稳定、公正和对明天的信心的幻想。事实上,任何一个庞大的社会纲领如住宅建设、粮食供应等都没有实现。”
“竭力在军事方面与外部世界相对抗(及直接参与阿富汗战争),彻底耗尽了毫无效率的经济。整个国民经济部门,如煤炭工业极其虚弱,没有为现代化积累必要的资源。输掉了与西方的‘和平竞赛’。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日新月异,在许多方面,如满足人的需要方面和科技领域先进国家都远远地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右翼力量联盟”在1999年发布的纲领的前言中指出: “20世纪是经历了很多悲剧性事件和巨大考验的世纪,是给全人类带来许多损失的世纪。我国在长达四分之三的世纪里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试验,试图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它建立了血腥的极权制度和变态的毫无效率的命令经济,以巨大的代价建立起了核强国。”
“本世纪末,由于军国主义化和泱泱大国自负心理所导致的严重的失调和过重的负担,由于对劳动和工作积极性的自然刺激受到了严重破坏,更由于大规模民主运动所施加的压力,共产主义制度破产了。我们作为俄罗斯民主派为对它的破产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1991年8月对于那些珍视自由和人权的人来说是需要永远铭记的日子。”
俄罗斯左、中、右翼无论有多么大的思想分歧,但都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扭曲变形、弊病百出的社会主义,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和轻重程度不同而已。右翼政党组织由于站在共产主义的对立面,当然对苏联社会主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价值判断是一种建立在大量历史依据上的事实判断。这种态度不是什么偏见极端,也不是缺乏依据的不实之辞,更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和“抹黑”。
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革命的清扫和复兴”新思维浪潮冲击下,苏联学者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用“兵营式社会主义”这一名词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它的本质特征;并同时以它的始作俑者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
当时有一位苏联学者B.基谢廖夫在一篇题为《苏联曾有过几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及其得到确立的原因”这样阐述: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出特点是:
——全面集中管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将行政命令方法与国家恐怖手段相结合,直至组织大规模镇压和建立强制性劳动的集中营。
——粗放和浪费的经济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完全取消了依据社会效益来评价(经济)成果。
——否认从前的民主化形式的价值,取消群众管理和民主制度的形式;否认(社会)自治思想;政权的神圣化直至到个人崇拜。
——社会生活甚至不受形式的民主程序控制;把党和国家的机关结为一体;执行机关监督选举机关;执法机关脱离法律和社会,其结果是独断专行。
大家只要将上述各条对号入座,衡量20世纪所有的“科学社会主义”国家,便会发现它们都是一母所生的畸形儿。
那么,这种变形的社会主义模式得势的原因究竟何在?哪些条件助长了这一模式?作者首先从历史传统的角度分析:
我想,应该从俄罗斯发展的历史特点中去寻找社会主义变形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落后。这种落后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遗产有关的发展途径的特殊性。
亚细亚的管理方式脱离了商品货币关系。尽管在效果上输给了西方文明发展的方法,但这种管理方式相当稳定。在这里取代物品关系而占优势的是非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主要的生产资料,首先是土地的集体(国家、公社)所有制是其客观基础。
这些同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有直接关系。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表明,类似亚细亚生产结构方式能够再现就是借助了“上层的”政府的社会制度变形。尤其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期望,以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似乎就能自然而然地导致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急速飞跃。斯大林放弃新经济政策后,加快了所有生产资料的全部国有化速度,并实现了强制农民的假合作化。然而,在生产资料过分集中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国家机关对全部生活资源的危险垄断。监督政权职能成为决定所有制的监督,而生产关系实际上被政治调节器所吞没。这种社会关系的过分政治化,一方面取消了真正的政治,而把其变成一部分人随心所欲和其他人的不问政治,另一方面,使发现和使用经济方法管理社会陷入困境。
……还不应忘记,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在欧洲文化的怀抱里。在原则上,社会主义理想,这是后资本主义的理想,它不能不汲取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成就,其中有人类社会生活的这样一些饱经苦难后得到的特征,如爱好劳动、人的个性具有的自身价值,个人的自由权利等等。可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不仅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化,不仅没有文明的基本前提,而且恰恰相反,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在有着亚细亚专制传统的国家里取得了胜利。按照某种一针见血的说法,在俄国总是有许多愿望,可是从来不曾有过自由。
这个“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看美妙无比,可是实践的结果却总是腥风血雨,难怪苏联解体后俄国的左中右翼都对它口诛笔伐,使它成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东西。特别是右翼,在反思苏联历史时把斯大林时代全盘否定,大有将其打倒在地使之永世不得翻身之势。
俄罗斯右翼政党都具有鲜明的反共色彩,而且往往从源头反起。如曾任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的丘拜斯最早提出把列宁墓迁出红场的建议,并得到自由派的一致响应。在2000年普京总统重审国旗、国歌和国徽,提出沿用原苏联国歌曲调的建议时,自由派一致表示反对。丘拜斯在2000年12月5日说,普京的决定是历史性的错误,普京和人民一起犯了错。他说: “在这时援引人民的意见是没有说服力的。总统不是社会学家,他的任务不是重复人民说了些什么,而是积极地对社会的观点产生影响。真理往往不在多数人手里,正如我们深知的我国历史那样,多数往往代表谎言、不公正和流血。”丘拜斯还说,历史将迫使普京作出选择,即使不改变决定,也应对损失作出补偿。他所说的补偿就是把列宁的遗体迁出红场。与此同时,右翼组织向普京发出声明,呼吁在列宁墓所在地修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20世纪因政治运动,包括革命、内战和大清洗而牺牲的人。应该建立一个相应的委员会,按照联邦宪法的要求解决公民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安葬问题。声明还指出,列宁墓在今天是违宪和非法的。在公共场所把国家的钱花在意识形态的偶像上直接违背俄罗斯宪法第13条: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作为强制性的或者国家的意识形态。” 供公众参观而展出的遗体违背了俄罗斯殡葬法第三条,该条规定殡葬方式只有三种: 土葬、火化和水葬。
极端民族主义的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声称,“共产主义的提法虽然好,但可惜不现实,即使采用暴力也建不成,所以对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应予以否定”。
日氏指出: “发现俄罗斯社会持续而深刻的体制(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真正深层原因是首要问题。……可以到伊凡雷帝时代、彼得大帝时代、十月革命时代,或者随便某个历史时代中寻找危机的根源。但是这不会提供什么,因为历史不能倒转,不是所有如此久远时代的事件都对当代产生影响。认识到下述方面重要的多: 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之后,苏联以巨大努力和牺牲为代价,不仅恢复了国家经济,而且使其迅速壮大,越来越广大的居民阶层开始逐渐享受这一成果。但是,到六十年代初,从生活中得到了一切、已相当腐败的党和苏维埃的上层人物失去了正确认识迫切的经济任务的能力,因为沿着平坦的道路前进比必须关心人民和国家的幸福更使官僚们满意。苏联学术界的上层人物宁愿继续按照已经失去现实意义的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观点生活,在因循守旧方面并不落后于最高管理者。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时代领导人的错误是对民用消费品生产的重要性估计不足。工业依旧是以生产资料的生产为目标。重工业的粗放式发展和萎靡不振的贪大求全,以及不惜任何代价追求总产值,导致苏联经济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没有效益。居民多年来不得不忍受生活必需品(从鞋子到灯泡)极端供应不足,为买到这些物品而排队。许多种类的产品质量始终极为低下,苏联终结之前苏共中央的任何口号都没有扭转这一趋势。” 自由民主党认为,“苏联存在三个缺陷: 民族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经济所有制形式单一(破坏多种经济成分)和根本没有民主”。
自由民主党虽然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现存体制进行修正和逐渐消除其畸形的表现,而不是把它全部毁掉”,但对苏联社会的弊病诊断正确: 民族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导致民族危机;经济所有制形式单一导致经济危机;根本没有民主导致政治危机。最后三种危机同时爆发,一个超级大国因此轰然坍塌。
一座巍峨大厦的坍塌都是因时间和结构的侵蚀而造成的。苏维埃帝国的解体是因为社会发生许多畸变的结果。对于这种畸形的社会主义,苏联学者基谢廖夫在分析其成因时写道:
可以这样说,不仅是制度能够决定社会风气和社会心理,而且,后者也能预先决定对制度的选择,或者至少能使这一制度变态。
新制度的确立显示了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这种特征,即把社会变革与工业化过程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落后的人民向着世界经济水平冲击。这种冲击是如此必要,但同时又令人痛苦,因为这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并要求把全部力量都高度集中在唯一的司令部——国家手里。
(当时)大部分人是文盲(约有75%的居民),群众缺乏民主文化和政治经验,对昔日生活的满腔憎恨和改变世界的激进行为、革命的急躁情绪、屈服于独断专行的悠久传统和专制的神话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乌托邦观点占很大成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途径的十分抽象的概念、“尝试和错误的方法”,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了国家的强化,而国家机关变成了有独立意义的机关”。这个为保卫人民免遭国内外敌人侵犯而建立的机关,甚至造成了马克思早已警告过的“阶级统治篡权”的危险。
新制度变形的另一个原因是执政党阶级成分的变化。加入执政党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因此,尽管进行过清洗,党还是不免要带些脏东西。列宁承认: “会有些野心家和骗子、吹牛和夸口的人,混杂在还不老练的革新者中间……” 由此看来,称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不是工人阶级的,而是使其利益变形的代表,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更为确切。这样,苏联官吏的官僚主义,专横跋扈和官架子急剧地膨胀起来了。列宁写道: “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官僚主义‘官厅’的臭泥潭里。” “CP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常见的情况: 不是机关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机关!”
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所取得的一切,都成了国家的力量和智慧。出现了对建立起官位等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崇拜: 那些管理人员成了不依赖于被管理的人了,被管理的人从属地位开始与管理者的无限统治权结合在一起。对纪律的需要退化为需要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即退化为要对社会进行严格的纪律训练。正如作家普拉托诺夫在一本书中指出的那样,权力机关开始制定和实行“使人丧失个性的原则,以便把人变成在日常生活每一时刻的行为都奉公守法的绝对服从的公民”。
站在政权这个金字塔最顶层的那个人的个人素质也起了其悲剧的作用。绝对权力的腐朽力量在斯大林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个人成了神话,而神话获得了现实的力量。对国家的崇拜变成了对个人的崇拜,即变成了宗教的社会代用品,变成了对那些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也是其所有成绩、整个过去,现在和未来人格化的人的崇拜。斯大林的至高无上权力还包括对列宁主义遗产的垄断和对国内思想的控制。
对千百万同胞的摆布也引起了权力机关对群众可能暴动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产生镇压制度的动因,这一制度只有在领袖死后才会结束。
历史学家还把在斯大林时代对社会主义和国家作出的重大和有益贡献,同他对国家和社会主义造成的危害区分开了。那些以各种理由认为,社会主义的成就至少可以部分地抵补斯大林及其亲信的罪过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第一,需要记住已取得成就所付出的代价,需要记住长眠在烈士公墓和成为“集中营尘埃”的人。
第二,已取得的成就是千百万劳动者,首先是军人和按那些年代的术语称作劳动战线的劳动人民的意志、劳动、鲜血和痛苦的结果。这是被社会主义思想唤起的极大热情和期望的结果,尽管在其体现时变形了。
第三,任何人也不能在斯大林亲自组织杀害大量农民、知识分子和列宁党的忠诚战士,在长达近20年间的大规模镇压和在卫国战争初期的悲剧责任方面为其开脱罪责。当然,应当考虑滋生斯大林篡权客观条件的制度,但不能把他的主观罪责溶于客观条件之中。戈尔巴乔夫指出: “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现象对党对人民所犯的过错是巨大的和不可原谅的。这是历代人的教训。”
作者在文章一开始就号召人们“从教条主义的梦幻中觉醒”,认为“不应把社会主义的当前问题硬塞入旧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教条死板公式之中”。他赞同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30至40年代的水平上”的指责,接着在文章里写道:
指责是公正的。对社会主义不加批判的、几乎拜倒的态度,早就把社会意识中广为传播的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与现实生活中日常的矛盾冲突很少有共同点的思想偏见。虽然俄罗斯诗人巴拉丁斯基称偏见为古老真理的残余,可偏见并非源于那么古老的历史,而是由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以革命摧毁原有社会制度的极端性、获胜阶级的代表人物陶醉于权力、确立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中的教条主义态度以及对社会意识的思想清洗等引起的。可见,社会主义不仅有其历史,而且还有其自身的错觉,克服这种错觉的困难并不低于克服敌对的观点,但需要克服,而且越快越好。只有在摆脱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辩护性,摆脱这一体系现在的代表者的自满情绪,同时缩小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差距,恢复在评价成绩时所需的最起码的诚实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位名曰基谢廖夫的苏联学者本人情况不详,但他的观点非常清楚: “在思想自由和‘思想烈火’(马克思语)面前感到恐惧,难道不是那些自以为有意识形态垄断权的人精神虚弱最明显的表现吗?如果社会科学今后仍然‘害怕接触到尚未作为政治决议的组成部分的那些问题’,对待政治决议还继续‘停留在注释的水平上’,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自知之明。”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一旦有了自知之明,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融入世界潮流之中浩荡前行,而剩下的那些货仍旧自以为是,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迷途知返。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