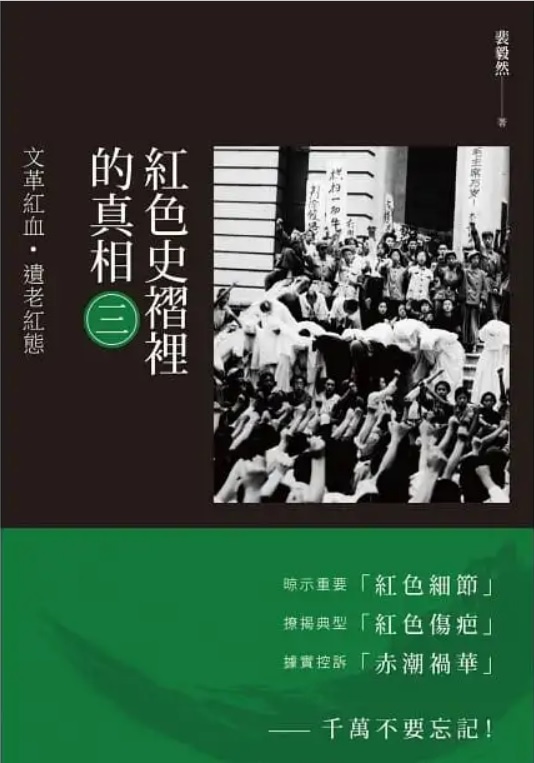《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五辑 : 文革红血(3)
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活耶稣
1949年大陆赤沉,中共很快发起对“精神鸦片”宗教的灭剿。1951年反梵蒂冈运动(历时一年半),驱逐梵蒂冈驻华公使黎培理。1953年“反帝爱国运动”,驱逐所有外国传教士。1955年9月8日夜,逮捕所有抵制“三自”(自治自传自养)的教士。上海地区,龚品梅、金鲁贤等三十余神父及300余教徒被捕,不少人判刑二十年或无期。
文革红色恐怖,取缔一切宗教,关闭所有寺观庙宇。红卫兵揪斗教士,游街示众,即便退至“爱天主也爱毛泽东”,仍被逼令呼喊“打倒天主!毛主席万岁!”教士只有一条路:“叛离天主,只爱毛泽东”。《圣经》、十字架踩踏于地,还须手持小红本(《语录》)高呼:“打倒圣母玛利亚!”“打倒圣子耶稣!”那些按要求呼喊者,得到革命小将宽恕——脱离批斗。不肯屈服者一个个乘坐喷气式(双臂反翘)、逼令下跪、拳打脚踢。
几小时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批斗现场,所有教士都屈服了,最后几位流泪叫了一声“打倒上帝”。仅剩一位盲人修士还在坚持,未让红卫兵取得“彻底胜利”。红小将们满怀革命义愤,撬嘴敲牙,逼他呼喊“打倒天主”,但从这张吐出鲜血与碎齿的嘴中,呼出的竟是:“蒋介石万岁!”盲修士认为蒋氏夫妇都是基督徒,如果他们主政中国,绝不会迫害教徒。红卫兵傻了,这位“不想活”的瞎眼教徒不是美蒋特务就是梵蒂冈间谍,那些凹凸不平的盲文肯定是秘密情报。
盲人修士金林生(1917?~1972),出生上海浦东教徒家庭,就读教会学校,终身侍神(不婚),奉职徐家汇天主教堂。29岁一场大病夺去光明,此后主要翻译宗教文献,独自呆在教堂阁楼,从不出头露面,数次灭教运动均“漏网”。进入文革,造反派逼他学《毛选》,遭拒绝;拖进学习班,仍唯读天主经书,殴打后坚不为动——只奉天主不奉毛泽东;只接受《圣经》教义,不接受毛泽东思想。他数次要求入狱,那么多兄弟姐妹都进过监狱,惟自己尚未“沾享”这份荣耀。
思想的力量确实很强大,许多教徒都把监狱当作考验意志的场所。他们坚信活着是暂时的,死亡才是永恒的,都愿杀身成仁,灵魂进天堂。
终于,金林生如愿进入上海第一看守所。冬天来临,金修士只有一套单薄修士服。狱卒有意折磨他,只发给一套释囚旧棉衣裤、一条薄被。深秋11月,外面教徒送给金林生的棉被衣服,次年4月才给他。狱方想要拯救这位不识好歹的迷途者,希望瞎子开口求饶。零下冰冻,金修士瑟瑟发抖,脸面发青,原本肺病就严重,阵阵咳嗽,数次高烧吐血,送提篮桥市狱医院抢救。盲修士就是不屈服不求饶。最后,狱方降低门槛,只要金修士写下放弃天主的保证书,哪怕只说一句话,表示向无产阶级专政投降,马上对他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提供病号饭、通知外面送药送物。偏偏瞎子不识抬举,每天正襟危坐,口念经文,心向天主。
一次,狱方诱惑金林生,打开一只外面教徒寄给他的邮包,除了衣服日用品营养品,还有一本盲文《圣经》。训导员要他认错,不再祈祷,便可领走这些物品,金修士摇头拒绝,只要求给他那本盲文《圣经》。训导员恼羞成怒,大发无产阶级义愤,狠狠撕扯盲文《圣经》,砸向瞎子脸上:“去你妈的上帝!去你奶奶的天主!”金修士颤抖双手,摸索着被撕毁的《圣经》,流下入狱后第一行眼泪。
狱中周五开荤,长期关押的囚犯,油水刮尽,一小块猪肉弥足珍贵,前一天就兴奋起来。1953年初被捕的《侍卫官杂记》作者周榆瑞(1917~1980):
旧历除夕,所有犯人在晚饭时都供给了烧肉……我还没有从盘中拿起一块肉时,便已在垂涎……肉烧得并不讲究,但是对一个六星期不知肉味的人,这已是很了不起。为了拖长我的享受,我慢慢地咀嚼每一块肉。当已没有肉时,我把馒头扯成一块块,沾着肉汁吃,由于一些肉汁仍沾在盘中,我便毫不犹豫地用舌头去舔盘。
甚至听到嗅到别人吃肉都反应强烈——
这间狱室的隔壁是厨房和警卫有膳堂,我经常嗅到他们烹调和饱吃鱼肉的味道,那对我是一种威胁,特别是因为我每餐只有蔬菜可吃,听到那些警卫一边吃一边咂着嘴的声音,真使我受不了。我垂涎欲滴,又因饥饿难抵,几乎晕过去。
狱中的食物实在坏透了。看看就感觉到不舒服,但我要活下去,我只可勉强地塞下去。装饭的小罐有三种……起初,我连最小的一罐也吃不完,但到后来,最大的一罐也不能满足我的整天感到饥饿。我越食得多,我的身体却越是瘦弱。我的衣服一天比一天的宽松,我想,我一定像一具稻草人了。[1]
但天主教周五小斋,不能食荤。金修士如仅仅为避斋日,可申请穆斯林餐。但狱方摆出条件:必须开口批判一声天主。这是他无法交换的筹码。每到周五,金修士便绝食抗议,自罚肉身,拯救灵魂,数年没沾一点荤腥。饥肠辘辘的狱友们无不感叹,敬佩不已。一同室难友回忆录中:“这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
瞎子病重,沉痾难起,狱方不愿他死在狱中,一难听二难弄,有意放他出去——保外就医,惟一条件就是低头认罪、放弃天主。保外就医,任何囚犯都不愿放弃的机会,狱友都劝他“写张认罪书先逃出地狱”,金修士还是拒绝了:
现在是假神取代了真神,我不能做叛徒犹大。我要保持信仰的纯洁,不要为了活命为了求生而糟蹋自己的人格,这是不值得的。其实死与生是一回事,天主是知道的,会安排一切。
他对狱友说:
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跟主走苦路,是主给我的恩宠。
难友以“韩信故事”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先低低头换取实惠。金修士摇摇头,认为那是对上帝的亵渎,罪孽深重,坚决不能为。难友都为他纯净正义的灵魂所感动,称他“‘一看’活耶稣”。
金修士从不责备别人,所有难友都是兄弟,不厌其烦向难友“传福音”,教他们祷告、要他们托付主跟从主,克服自身软弱。尤其对那些先利用后踢进来的造反派头头,金修士深为他们的罪孽痛苦不安,替他们忏悔、祷告。
记录金修士“一看”事迹的是小难友刘文忠。刘先生蹲“一看”四年余,详述狱方如何以食物控制犯人。1967年初,“一月风暴”刮进上海监狱,司法系统造反派夺权,“改革狱政”——进一步贯彻阶级路线,落实对阶级敌人的仇恨,绝不向敌人施仁政。同时,“节约闹革命”,三餐改两顿。上午9点三两稀粥,下午16点四两半干饭。每天1500cc开水节约至1200cc。
一早,犯人肚子就转起来,伸长脖颈等粥。送粥的电梯一响,粥香马上飘来,一个个端着饭盒守在囚室门口。下午16点开饭,21点睡觉,肚子早空了,叫个不停,只能巴望早点睡着,“放下”饥饿,奈何越饿越睡不着。
上海第一看守所分大中小灶,小灶两餐有荤,专供外籍犯人与著名人士,如陈璧君、龚品梅。中灶一餐有荤,供给有地位的犯人及处级以上犯官、揭发有功者,如著名右派王造时、孙大雨。大灶一周一荤,全狱犯人每周伸长脖颈就等礼拜五,那个兴奋那个激动,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体会。[2]
文革期间,翁文灏堂弟翁文漪(1907~1978),剑桥硕士,1949年前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总工兼香港大中国火柴厂长,1949年后上海轻工业研究所塑胶试验室主任,1963年出席国庆招待会(毛周接见),1968年因十分荒唐的原由判刑入提篮桥。一日开荤,见一小块猪肉落在饭架上,尽管饭架很脏,肉也沾了砂子,这位六旬高知还是捡入口中,遭同监犯人揭发,马上开他的批斗会,狱吏嘲笑:“剑桥大学高才生,你的绅士风度哪去了?还不是只狗熊?偷肉吃!你不怕脏吗?这种肉连狗都不要吃,你是连狗都不如!”会场上,大多数犯人敢怒不敢言,有人私下说:“如果毛泽东落到这地步,还不是一样!”[3]
“一看”关押的均为政治犯,意志坚强度不算低,但在盲人金修士面前都找到差距,一致公认他才是“精神不败”、道成肉身,目盲心明。在大陆红色教难的祭坛上,盲人金修士放上自己的坚守,让相当一部分人“失去重量”。
1972年,金修士入狱后第六年,死于“一看”。
2008-2-7于沪
[1] 周榆瑞:《彷徨与抉择》,开放出版社(香港)2015年再版,页79、89、160~161。
[2] 刘文忠:《风雨人生路》,崇适文化出版公司(澳门)2005年,页287、128、114、112、128。
[3] 陈文立:《沧桑岁月》,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委会(华盛顿)2002年,页119。
原载:《争鸣》(香港)2008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