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向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极为艰难,但始终得到全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关爱与帮助。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自北欧来到安东的一些丹麦基督徒在辽东地区传教,建立医院、孤儿院、中学、小学及园艺职业学校等慈善和教育机构,通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为安东的“现代化”发展做出了可观的贡献,给安东的城市建设与社会生活留下美好的印记与痕迹。然而,在中共政权下,这一切都被毁了。侨居安东的丹麦基督徒被诬构罪名,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以及传人,比如吴立身、郭慕深、崔锦章等,遭受多年迫害。这在中国其他省市都有许多类似情况存在。然而,在中共官方的历史记载中,这段真实历史被千方百计地隐瞒抹杀了。作者鸿路通过多年的努力,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采访,写成《丹麦人在安东》【1】一书,为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做了很好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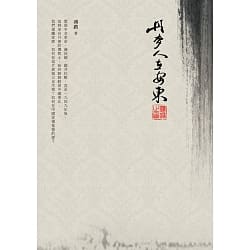
尽管丹麦基督教进入东北已有其他国家传教士在了【2】,但丹麦路德会传教士柏卫(Conrad S Bolwig)仍然怀着与其他基督传教士一样的坚毅和热忱携妻来到今天辽宁丹东一带。作者用他的生花妙笔,从柏卫肇始记述了一批丹麦和中国基督教信徒不凡的历史而又是可歌可泣的故事。
作为丹麦路德会进入中国,其传教士人数以及地域也远不及英美,但在中国基督教史上不可或缺。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3】以及姚民权的《中国基督教简史》【4】都提到丹麦路德会在东北的事迹。当然都十分简单,很可能他们都只是参考了《中华归主》一书。
而作者则是从实地、档案以及当事人的回忆,给了我们真实,而且是栩栩如生又读之趣味盎然的历史画卷。无需掩饰地说,任何一位想了解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这都是一本应该阅读的书籍。何况,在为数不多的中国基督教历史的书籍中,作为地域性的研究和记述的著作,应该说这是第一本。
柏卫于1896 年在安东开始了他传道的生涯,那时东北几乎处于无政府的状态。沙俄入侵,但它只是占领他们认为需要的地方,所以中国政府机构以及军队仍然在那里存在。为了防止中国军队的危险,沙俄不仅遣散了中国的部分军队,同时也收缴了他们的军械。【5】被沙俄解散的中国军队中部分兵士与原有的土匪合流,盘踞长白山山脉的丛林,打家劫舍,形成了大大小小各股匪患,官方基本无奈,有时只得联合沙俄军队共同打击,但收效近微。【6】
凶狠的土匪还会流奔数百里,直掠今天的凤城一带。对他们来说,劫掠安东一带应该并不太困难。【7】作者对那时的孤山镇写道:“早在乾隆年间,这里是辽东的水陆重镇。到了清末,又成了鸭绿江上游木材输出的商埠。南来北往,商贾云集。街市客栈酒肆,商号林立,娱乐消遣的去处有戏园子、烟馆、也有青楼。”【8】
安东的繁荣,不可能不引起土匪的垂涎,据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1901 年8 月8日)盛京将军曾祺等奏与俄军合力堵剿刘弹子、杨玉麟等股军情折:五月初六,贼首郑兰亭率领数十人潜至安东。“安东大东沟、大孤山皆水陆商贾凑集之区。当林七窜宽甸,各商民等已有戒心,或将货物移置船中,故一闻警信,便即纷逃……。”【9】
虽然这些匪情在都在义和团动乱之后,但在之前已经有之。当然柏卫有上帝依靠,不会怯弱,但我们可以揣测对其传教而言,绝非幸事。对其幸运的是,他逃过了义和团动乱的杀劫【10】,并回到自己的故乡。等他再回安东,正逢日俄战争。【11】随后多年,匪患更盛。【12】
柏卫与他的同道者仍然坚忍不拔,孜孜不倦开展传道以及与传道相关的事业,上帝的恩典逐渐地改变了一方。
虽然东北历经俄日侵占,满洲政权的统治,还加上匪患横流,但那里几乎没有发生教案。
这对在东北地域的传教士而言,也算是不幸中的幸运了。1840 年之后签署的各种条约,由于条约明确规定允许传教士传教,到1870 年,清廷刑部改定律例,废除了到内地传教的禁令。传教士不仅能在开埠的城市传教,也深入到内地,甚至是山区和农村,【13】自然信徒也是社会最底层的民众【14】。因为教案大量增加【15】,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天津教案,连同中国教民在内被杀五十余人。教堂被烧,财产被抢,传教士以及教民受伤甚至死亡时有发生。
对于那时签署的条约,对中国毫无疑问是个不幸,同样对传教士的传教和生命也是个不幸
【16】。所有的教案都在叙述这样的不幸,虽然清廷加大对发生教案的地方官员的惩罚力度
【17】,但仍然不能杜绝。虽然不能杜绝,但在官场已经形成害怕教案,甚至迎合传教士的现象。按照常理,这是传教士及其信徒大受欢迎的现象,但是有些具有理性的传教士产生了担忧,并看到了危险【18】。
教案从深层次来说,一个原因确实是在天主教传教士身上。由于条约明确规定传教士传教的自由,并受保护。当传教士遇见人为的阻扰以及受损时,他们势必会找到当地的官府请求帮助,同时也会申报其国在京的公使,特别在当地官府无作用的状况下,公使会出面寻找当时的总理衙门交涉。发展到后面,除去派兵严加保护传教士的人身以及教堂之外【19】,还赋予了按他们的级别可以直接寻找知县、知府、巡抚和总督等的特权【20】。由于有了这样的特权,一些传教士也会要求地方官处理教徒的一些事情。同时也会将其中某些事情直接报到在京的公使那里,让他们转交总理衙门。而那时的地方官员(特别是府厅州县)对涉外的事务几近一无所知【21】,挨了上司的训斥和勒令之后,除了唯唯诺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应付的办法。我们很难说,部分传教士为他们的教徒而出面的有些事情完全有理并公正。【22】
需要辨明的是,这样的现象几乎可以说完全发生在天主教传教士的身上,而基督教传教士从一开始就看到问题并极力想避免,而为自己传教铺平道路【23】。这点我们可以从《英教士在山东传教章程》看到一斑,将章程摘要如下:“本教放赈施医等善事,系遵本教爱人如己之训,非有意收拾人心。”“凡娶妾、赌博、吸鸦片,因教断亲,邪行法术,夜聚昼散,倚教弃族,恃教惹事,全不准行。”“教堂男女坐位具有定所,绝不淆杂。”
“古圣先贤劝人孝弟为善之语,本教士民无不钦佩,并劝习教者不准诽谤古训,侮慢圣贤。”“入中原,恪守圣言,顺从华礼。”中国教徒“倘遇讼事、国课、官差、杂税等件,具归地方管理,与平民一律。”
“遇中外失和之事,习教之人均应相助中邦,尊君亲上,常作顺民。”“凡人与教友涉讼,非实因教起端,教士并不干预。”“人欲进教,皆先细查其人,曾否与人构讼,事体清楚,方准入教。至进教后,倘恃教滋事,立即革除。”“本会建造教堂,甚为留意。如实在与土著有碍,请愿设想避让。”教士造房居住,“虽稍具西国款式,亦不甚高。总不建高塔高楼。”(《教务纪略》卷二下)我们从这些章程的条款看出,基督教传教士小心翼翼,极力避免传教中任何矛盾的产生,但遗憾的是他们还是受到仇外情绪骚扰,甚至是伤害。
当天主教进入中国,仇外情绪也就伴随而来。作为统治者以及其官员几乎都是在有意无意地煽起甚至加重这种情绪。长期以来,这样的仇外情绪不断在累积,当汇成普遍的现象之后,最终成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工具。而作为集权统治者从本能上和自己的利益上也从其捍卫所建立的政制方面出发,极为需要这样的仇外情绪,不仅作为自己治理上出现问题的借口,也是转移政治矛盾的法宝。长期官方施加影响,最终得到统治者的默许或支持,在有清统治的年代,这种社会仇外情绪的宣泄达到高潮,应该数义和团动乱了。但细细剖析,参与者的仇外情绪只是纯粹的个人利益的得失吗?对于上帝之教血腥冲击的二十年后,尽管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众多的仇外情绪,甚至准备再次产生类似义和团的动乱,但已经有了一定的理性成分的同时【24】,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政府还没有糊涂到忘记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25】,也就是说,这场几乎会酿成第二个义和团的动乱【26】,因为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默许或支持,最终烟消云散。尽管我们看到这场非基运动中含有理性的成分,但其中也仍然饱含满腔的怒火。
在此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引用了1922 年3 月9 日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不妨摘之如下:我们知道基督教及其基都教会在历史上,曾制造了许多罪恶,这且不要管彼。但是彼现在正在那里制造或将制造的罪恶,凡我有血腥,有良心,不甘堕落的人,决不能容忍宽恕彼。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一方面有掠夺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都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桀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都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各国资本家,……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基督教及基都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无非要养成资本家的良善走狗。……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第206-207 页)我对这样的文章不想加以评论,只是问一句,这样充满怒火的斗争行文,是否与文革的文章有着一脉相承的味道?教案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在中国官民对自身利益的认同。1840 年后,传教的禁令被冲破。
在平民百姓中,一个知县已经是天大的官了,既然最低级的外国传教士都能与知县平起平坐,所以称呼其为老爷也自然而然了。仅从这样的称呼,就可以揣出传教士在当时中国平民的认识中的社会地位。尽管这样的称呼,最后被中外禁止【27】。但对部分机灵的中国平民来说,立即看出了一个空子:他们信教,不仅可以拔升自己的身价,也可以让其家庭的声望在周围提高,还能得到与官府抗衡的保护,可以不受官府与豪强的欺凌和伤害。广东教民将入教的标志张贴在自家的门楣,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28】。而部分平民在犯罪的情急下,也愿意表示信教,以此逃避受罚【29】。而更有甚者,一些罪犯也利用信徒的身份,躲避官府的捉拿,传教士那里成了他们的逋逃薮。这样,从实际状况来说,已经形成了两种司法的现象。
这使我们想起英王亨利二世的时代,因世俗的法律与教会法律的不同的执行,导致其统治的危机和社会的不公,其几乎可以说终身为之改变而付出自己的努力【30】。传教士干涉司法的现象,不仅让中国官员深感无力,也使公使和传教士意识到不妥。关于中国官员的无力,主要是来至于朝廷以及官场形成了对外国事情为重的影响,特别是义和团动乱之时,清廷南方的封疆大吏已经将保护各国使者和在华洋人为头等要务【31】,冲淡了以前朝廷所颁布的处理内容,或者说根本不顾及了【32】。直到这种状况在清廷倒台之前愈演愈烈,中外都定出了中国人入教考察和调查的规定,并严格制止传教士干涉司法的弊病【33】,尽管如此,但仍然无法根绝。我认为有一个社会现象必须指出的:作为大部分中国人他们一旦觉得自己高于周围的人时,很容易爆出炫耀和自傲,以此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同样他周围的人会想尽办法来贬低并产生嫉恨。我认为这不但是构成许多教案最初的情绪的原因,也是产生许多人仇外的心理基础之一。然而这一点,我始终奇怪在教案的资料中没有着重提到,可能这是记录教案的官吏更着眼于教案具体事例所致。指出这样的特性,并非是对这个民族有意贬斥,而是直到今天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呈现类似的现象。当然其中一部分人与教民相争受屈,特别是一些披着教徒外衣的教民为非作歹,引起平民的愤慨将是肯定的【34】。
美国教授史维东(Alan Richard Sweeten)的著作《中国乡村的基督教》【35】━━该书以1860 年至1900 年在江西省发生的教案为研究━━得出明确的结论,所有教案中发生的冲突原因与宗教无关【36】。我们往往认为教案中冲突和对抗有部分原因可以从习俗和观念来解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从更深处来考察,只能归到利益的范围。例如风水的认识,而风水只是关系到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家庭的收成与子孙的兴旺。又如缠足,在那时几乎是全国的风俗,当传教士鼓励放足【37】,并没有引起任何阻扰,但是女性住进医院和进教堂与男信徒杂处却引起轩然大波。这首先谈不上习俗,而只是表现出中国男人一个肮脏的心态罢了,因为在他们的心里,女人是他们的禁脔,无法容忍他人染指,哪怕有莫须有的一丝可能。
对于教案在利益的问题上,可以说发生在义和团动乱中的山西尤为惨烈,而造成惨烈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同样令人愤慨。这个原因就是赛会迎神的世俗民众活动。我们知道,《圣经》明确规定只能敬拜上帝,当天主教进入中国后,在世俗生活上与这类赛会迎神发生冲突。
这个冲突很快就引起朝廷的注意,曾多次颁布规定甚至是谕旨,中国信徒可以不参与这类活动,更重要的是免去这类活动所产生的摊派费用。而作为地方,因为少去了不参与人的摊派费用,势必加重了参与者的摊派费用。从这点上说,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参与者的不满。但问题并没有这样简单,因为这类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地方上某些人捞钱的手段,而能在其中捞钱应该说是地方的“精英”了。甚至可以说,这才是赛会迎神因摊派费用而产生冲突的真正原因。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敦崇礼(Moir B Duncan)在《山西教案善后章程》写道:“山西仇杀教中人如此之惨,且多亦因平日教友不肯出演剧敬神之费,致干众怒,故演剧亦为山西仇教祸根。以演剧之颓俗,酿如此惨祸,上害君国,下害生灵,在上者必当力除积习。试言演剧之害:一、戏价在百串之外;二、绅社人等滥用分肥,多于戏价两三倍;三、阖村接待亲朋之肴馔,妇孺衣服簪珥之装饰,又多数十倍。更可恶者,演剧之场必有赌棚数十处,每棚有数十人之费用。此等匪徒,每到一村,必与绅社人等一定之棚价。绅社人等利其棚价,遂任其害人子弟,耗人资财。是以演剧不过数日,至令人民终年困穷。兼之优伶所演,多奸淫盗贼之恶剧。背礼贱义,伤风败俗,莫过于此。
近年中国公私耗竭,生灵涂炭,学堂不立,民智不开。每村居民或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无一学堂。
问其故,则曰贫不能读。试问此村每年敬神演剧之费当有几何?若将此有害无益之费改办学堂,则无一村无学堂,无一人不识字。”【38】
我之所以将敦崇礼建议引出,也想让世人看看一个西方传教士开启中国民智的苦心。在此我继续引用一个也因演戏发生的教案,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下发生的时间是在1899 年,在这之前清廷早就颁布过对教民免除因迎神演戏的费用摊派。此事发生在江西南城县的县城,有4名女教民开了一家商铺,街上管事的李某前去收取演戏的费用,遭到拒绝后,指使几个地痞不仅前去砸门,还抢走东西,临走再放火,导致二十多家商铺被烧,并烧死一人。女教民告到知县那里,李某早就贿赂了衙门,于是知县不仅将她们收监,还大刑伺候。传教士戴神甫与知县交涉也无结果,只得上告到北京公使那里,请求公使出面找总理衙门交涉【39】。尽管我在前面说过,部分传教士为他们的教徒而出面的有些事情不能说完全有理并公正,但从这个案例来看,在有地方官贪婪并妄判之后,教徒们所受的冤屈与不公也所幸传教士能让在京的公使出面干涉【40】。
至于上帝之教对于祭拜孔子和祭祀祖先的冲突,也许能看成观念与认识上的冲突。我更认为前者多少与自己以及子孙的功名利禄有关,而后者祭祀的同时,也在告诫子孙自己百年之后,万万不能将自己遗忘。关于这类冲突,从利玛窦(Matteo Ricci)到了中国他就明白了,他采用了回避【41】,但这类冲突是不可能回避得了。著名的康熙“礼仪之争”可以看成这类冲突的大爆发,但随着不平等条约的签署后,这类矛盾逐渐趋向平息,得亏于在中国的部分官员或有文化之人做出了新的解释的同时,传教士也表示对祭孔祀祖的尊重【42】。
尽管史维东在研究了当时江西发生的教案,而得出教案的根本原因与宗教无关的定论,但在众多的教案中,我们发现有极少的案例与宗教还是能扯上关联的,可能这样的教案在江西没有发生过。据《教务纪略》卷三下的《总理衙门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中的记载:民间订婚后,“入教者必令不入教者退婚,或父兄入教必指不入教之子弟凶忤,呈控到官,教士袒护。”又如“同治八年,四川殴毙教士李国一案,实由教民逼人退婚肇祸。”产生教案的这样原因应该是牵涉到天主教,而不是基督教了。
论起教案,无法绕过义和团动乱。这样疯狂荒唐又毫无人性的仇外动乱,不仅没有得到制止,而且还受到清廷以及部分官员的支持和纵容,在整个人类政治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仇外的情绪从当年利玛窦进入中国已经存在,那时更多的是将外国人视作异类,而统治者则是更喜欢他们的学识。当年利玛窦曲曲折折到了帝都,虽然供职于大内,但他直到死都没见到过万历。【43】我们称赞的康熙帝,可以使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免于一死,后又恩宠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但他有兴趣的是他们的历法以及制造火炮的知识【44】,传教士并没有获得传教的自由【45】,直到发生杨光先教难之后的二十多年才有所改善。尽管如此,我们很难说康熙喜欢上天主教了,更无须幻想他会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46】。
康熙的继承者雍正、乾隆只是把康熙的举措推到极端罢了。我们今天去阅读一下那时的文献,对于天主教传教士直接视作畛域来的夷狄【47】,充满了轻视与不屑。无论朝廷还是地方官以及乡绅,都将他们视作乱党分子,所传的教义也是邪教【48】。而中国的民众信从官府和皇上已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天性,雍正、乾隆中对传教士的打击,为当时以及以后的仇外情绪打下了基础。所以当1840 年后,各种不平等的条约的签署,在仇外的普遍情绪上不仅激起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又添上了自认为受辱和遭受不平的愤怒。于是教案迭起,轻则为些生活琐事发生争执,并告到官府,重则杀人放火。在所有的教案中,我们看到的是外国人被打遭杀,教堂焚毁,财产受抢。到了义和团动乱时,只要与外洋有牵连的人和物都在劫难逃,遑论一个的的确确的洋人了【49】。在这样駭人听闻的动乱中,作有一个有主权的国家的政府职能是尽快平息动乱,保护好外人的生命与财产,但慈禧和一些官员不仅不去履行政府职能,反而去支持与纵容动乱的暴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廷已经丧失了有主权国家的政府资格和职能,那么挨打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了。1840 年之后签署的各种条约,我们可以视作不平等和受迫,但毕竟签署了。虽然深感吃亏和有失尊严,但既然签署,遵守是必须的,而不是通过丧失理智甚至动乱来推倒自己的承诺与废除签署的条约。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过了一百年,当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之后,所有那时签署的条约就被废除了。
当清廷派遣使者到巴黎,为天津教案致歉时,当时的法国总统很有见地指出,并不希望中国杀掉多少肇事的凶手,而是希望中国能加强秩序和遵守条约。
1840 年后签署的条约中规定能允许传教,这成为传教的一个诟病也成了原罪。由于鸦片成为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传教士似乎也成为了向中国输入毒品的帮凶,因为他们是受益者,战争为他们打开了传教的大门。照理他们应该是毒品输入的鼓吹者和赞成者,但事实上传教士定下的入教章程,明文规定不允许吸毒【50】。特别是一些明达的基督教传教士不仅因毒品输入中国深感羞愧和难过,还准备放弃条约中给予他们的特权【51】。一些怀有医术的传教士还积极医治毒瘾,甚至还开办戒毒所【52】。他们不仅开办正规的医院,其中还有精神病院和麻风病院【53】。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也有不少医籍,但对于这两类病不知是否有记载?但更多的可能是遗弃,特别是麻风病。从天主教进入中国,就已经担负起纠正中国陋习的责任,禁止纳妾是成为信徒的一个明确规定【54】。至基督教进入中国,将纠正陋习与道德联系起来,大大扩大了范围【55】。我们把传教、办学与办医院看成是传教士热衷所在,无论中外人士都不避讳办学与办医院是为了传教,是为了让人感受上帝的恩典【56】。
我始终不明白,办学,为中国人开启民智,还为中国进入现代教育打下扎实的基础;办医院,拯救中国人的生命,治愈他们的病痛的同时,亦带来现代科学的文化。但进入二十世纪,却有不少人,认定传教士们办学和办医院是包藏祸心,在仇外的基础上又摆出一副诛心的架势。
在作者的书中,丹麦的传教士不仅开办学校、医院,还创办种植园、加工厂,让更多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过上正常的生活【57】。特别是作者为我们讲述的传教士于承恩(Johannes Vyff),自踏进丹东,创办教堂、医院、中学,呕心沥血,最终也命归安东的史迹【58】。我们要知道传教士所作的一切以及在中国的教堂、学校和医院等的创办,几乎都来至于他们本国民众的捐助【59】。而创办之后,对于中国民众至少在不短的时间内是免费的。在作者笔下的丹麦传教士也是如此【60】。一旦各地有天眚时灾,有能力的传教士往往会挺身而出,行善赈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但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在当时就连清廷也要表彰的传教士,但在数十年后却会遭到无端而又任意的指责。传教士受到指责最多的就是他们是西方各国的帮凶,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他们的方式来残害中国。按此理这些传教士应该是最不希望中国强盛,有趣的是沈迦在他的著作里为我们转引了一位浙江瑞安儒生林骏在当时聆听了李提摩太的演讲而写下的日记,我们不妨看看:“英儒李提摩太演讲良久,不外保国保种为主义,其言云,凡事业须以自立为主,彼列强之豪杰,如俄之大彼德、法之拿坡仑、德之威廉第一、美之华盛顿、日之明治,一时励精图治,遂为地球上之雄国。清国君自为君,臣自为臣,民又自为民,且上下交私,安问竭诚以报主,勠力以安邦?此中国所以衰,所以弱,而终致于不振。况又谄媚外人,苟安为计,吾知瓜分之祸即在眉睫。燕巢幕上,福祸不知,苟至极惨,灭国灭种,情将奚堪?呜呼,如李君所言,真药石之论也!”(《寻找苏慧廉》第206 页)而对于传教士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带着政治偏狭的指责,时至今天也不罕见【61】。
我们一般都把利玛窦看作天主教传进中国的先驱,而基督教则为马礼逊(RobertMorrison)。时至今日,通观其传进中国的历史,我们并没有看到良好的发展,更毋庸说其在政治上产生意义了。我们很多人认为上帝之教的教义会帮助人们对建立起一个平等国度的认识,甚至是奠定民主政制基础的一个重要文明因素。这几百年的历史,似乎并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么我们想问的是原因何在?如果我们从政制的视角来寻找这个原因,应该能得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解答,但问题是在上帝之教与中国这样的政制其冲突点在哪些方面?显然用教义不足以说明问题。在平常人那里以及到统治者,在他们的眼里上帝之教与其他宗教并无区别,正如在许多官方的资料中,我们可以读到,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其宗旨都是劝人为善。在他们心里传教士与和尚道士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正如早期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往往被安排进寺院,甚至穿戴也是和尚的服饰【62】。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传教士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建立自己的宗教场所,收取自己的信徒,但他们的历史证明了不是这样。这是因为他们传教有定期的聚集,并积极参与社会的一些活动。当在信徒不断增加之后,形成了指导宗教活动的组织,那就是教会。这里必须强调的,定期的聚集是按其宗教需要的规定形成的仪式,而教会则有强烈的自主色彩。当传教士们跑进中国,他们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很完整而且是高度集权政制和权力专一结构的社会,就已经注定了他们传教不会受到欢迎,无论是最高的统治者,还是底层的官员。从最高统治者以及所建立的政制来说,绝不会容忍一股无法控制而游离在外的社会力量出现,因为这不仅是对他尊严的冒犯,而更重要是有对现存的政制会产生倒塌之虞。对于官员来说,可能最直接的感受是传教士们的行为会对他们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63】。而真正遗憾的是不仅一般传教士没能从看透这点,他们之中的英彦也同样如此。利玛窦临死还抱着“皈化中国皇帝”的意念【64】,只是证明他并不了解皇权与王权的区别,或者说他把皇权当作王权了。清康熙与罗马教廷发生的“礼仪之争”只是这个本质问题一次呈现罢了。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加大了禁教的力度,几乎使传教频入了绝境。我们来看看雍正怎样看待传教士们的。对于传教士他与其先帝一样,在制历方面是需要的,其他则不仅是个很大的麻烦,也是从统治的意义上来说深恶痛绝。据沙百里(J. Charbonnier)的《中国基督徒史》记载:1724 年1 月礼部有奏章写道:“宫中的西洋人有益于制历,他所于宫中还做了出了其他效役。但居住在各省中的传教士,却毫无裨益。他们将那些无知的男女都吸引到其宗教中,以礼拜的名义而男女无别地聚集在一起。” 【65】雍正直接责问传教士:“尔等希望所有中国人都成为教徒,让归化的教徒只承认你们?”【66】从这两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官员们察觉聚集之害,而作为皇帝更有切身的感受,存在臣民有游离其统治的危险。特别是天主教还有一位教皇,更令中国皇帝深恐不安。沙百里写道:教皇发来的教令“使中国皇帝觉得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和有害的干涉,尤其是它们有损于本来可能会巩固帝国伦理秩序的准则。”【67】接着沙百里指出:“对基督徒的迫害属于皇帝的专制主义,对外国的恐惧,儒教的保守主义和对区域起义镇压的这种大背景。”【68】不得不说沙百里神甫见解极有见地,但遗憾的是过于笼统,也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也不得不指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真正思考到上帝文化与高度集中的政制是相冲突的,而这种冲突更多地是在上帝之教的教会本身上面【69】。通览中国上帝之教的历史,其中最能说明的,应该是蒋介石了。这位受过基督洗礼的国民党最高领袖,理应让基督教在中国完全兴起和发展,但他更赞赏的是基督教的道德【70】,而不是教会的真正作用,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一直钟情党国的集权政制的建立。所以在他统治之下,基督教在一些方面受限也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71】。
由于此文是作为《丹麦人在安东》读后记,谈一下满洲国统治时期东北传教的遭遇也是绕不开的,何况该书作者也谈到了这些情况。作者在书中写道:按照满洲国皇帝对学校的诏书,要敬拜太阳女神,并规定学校办公室悬挂皇帝的画像,师生每天得向日本天皇、满洲国皇帝进行鞠躬礼拜,传教士创办的学校也不能例外。由于于承恩创办的三育中学没有照办,一九四二年七月三十日来了日本宪兵队的头目、警察局长、县长、教育局长等人来到三育中学,师生们被赶到操场,勒令向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敬拜,“所有的中国人都深深地弯下腰去,唯有两个丹麦人仿佛两株伟岸的树直立着。”接着宣布三育中学不遵守规定而停办,校长被撤销职务并被吊销教师执照,全部学生转学到日本人开办的学校【72】。当我读到,所有的中国人都深深地弯下腰,只有两名丹麦人站立着。我讲不出内心的感受,是维京人遗留的不屈还是对上帝真挚的信奉?不得不让我想起多年前,浙江温州乡镇私宅房顶的十字架被强制拆毁,信徒们全都默默地接受了的事例【73】。我一直在问,是信徒们对上帝信奉的真诚心不够,还是应该从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中寻找答案?对天皇和皇帝的敬拜,实际上变成了当年传教士与祭孔祀祖类同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对满洲国来说并不会像明清那样处理起来棘手,所以满洲国的教育大臣很快表示,对天皇和皇帝的敬拜只有政治上的含义,而不是宗教上的仪式【74】。无论怎样的解释,上帝之教在一个帝制的社会不会受到欢迎,这是毋庸置疑的。自上帝之教进入中国,不是被禁就是任其自主传教。通过第一步抓教会人士,第二步冻结教会财产,第三步组成新的教会团体以及新的教会领袖等软硬兼施方式,真正以政治手段和意识来强制甚至是控制上帝之教的,是在日伪时期,特别是在满洲国开了先河【75】。
《丹麦人在安东》另一个极具特色是对中共政权下的传教士和教徒所受遭遇的记述,这不仅是显示作者怀有博爱之心,更重要的是通过案件、采访等材料来证明其真实性。这点也是我所见的关于中国基督史文章和著作所罕见的。在这段历史中,首先是上帝之教本土化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已经开始,首先是在学校和医院方面,到了中共政权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更加重大起来。不得不指出,这个问题变得重大,政治需要成了主导。
要做到并不难,因为本土化完全可以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解释,甚至成为爱国主义在宗教上的另一个名词。罗文藻成为主教,正如梁发一样,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本土化的开始。随着时间的流动,中国主教、神甫和牧师的人数都在显著增长【76】。作为有见识的西方传教人士不仅希望,也用实际行动来促进本土化【77】。我们知道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每一个举动,都离不开其本国的民间捐助【78】,这样的状况我们无法想象能永久的保持,所以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虽然是必然的趋势,但也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应该是平和自然完成,也同时是教会逐渐完善与成熟的过程。这对一个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权来说是无法也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只能不是排斥就是需要通过政治手段让其臣服【79】。中共选择了后者。
作者在其书中为我们提供非常具体而又令人动容的事例。东北与其他地方不同,中共政权的建立要早几年。虽然大孤山的教堂和学校在1945 年11 月已被中共军队占用【80】,但真正意义上中共政权的建立是在1947 年的夏季。此时丹麦女传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已经76 岁,她被绑着,与她一起的还有另两名丹麦女传教士。关押后,三人被告知:“你们要接受审查,交代问题。”1960 年7 月,中国最后一位外国传教士在孤独与凄凉中走完了她的生命岁月。在她生命最后的十多年中,因教产被当作安东最大的地主,颈上挂着满篮子粪屎游街;在“自治、自养、自传”的针对宗教的政治运动中成为运动的对象,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81】。在作者的书中,不仅仅是为丹麦传教士立传,也为安东的中国基督徒立传,其中特别是两位女信徒何柜纳和于桂春。假如是天主教的话,按她们的言行封圣也不为过。正当“三自”运动骤起,每个上帝之教的信徒都得签名表示拥护,但这两位断然拒绝,而且拒绝得非常彻底。当每个人要捐钱买武器“抗美援朝”,两位告诉他人,她们遵循耶稣要的是和平的教诲。教会再也不容她们,她们流浪于穷县僻壤,以“艰难当饼,困苦当水”,传播福音。何柜纳说:“为主活为主死,这是我的心愿。”于桂春说:“我的生活没有来源,就是靠主生活,凭信心生活。”当局终于耐不住了,两位在1958 年10 月被捕。在法庭上,何柜纳掷地有声告诉审判她们的法官:对于基督“就是杀头,我也信!”最后两人被以反革命罪各判四年。对于这两位女信徒的言行,能不起敬?故作者将记述她们事迹的篇章命为《孤山独不降》,宜哉!在作者的书中最长的篇章是《基督教医院的末任院长》,记述了崔锦章波折的一生。毫无疑问,崔锦章是位正直富有理想的医生,他热爱中共这个新的政权,也愿意为其贡献自己的才能。但中共政权并不会看重这些,它要求的是必须毫无折扣地承认和接受它的政治意识,也正是这种政治意识不仅是评判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是非标准,也是确定是自己人还是打击对象的尺度。不幸的崔锦章被列入打击对象的行列。打击崔锦章十分容易,因为他与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早期的天主教被归为白莲教等谋反的秘密帮派的同一做法,此时的传教士已经被定义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或者“帝国主义侵略的帮凶”,因为帝国主义早已被说成万恶之源。尽管这样的说法并非是新政权的创新,早在非基运动时已有这样的说法,新政权显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利打击上帝之教的政治舆论工具。在政治舆论宣传方面,新政权自有一套,他们先将某个名词下好定义,然后挖空心思让其成为一个“框”,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事物都可以装进去。新政权在制造好这样的“框”
后,采用政治运动形式,一面驱赶外籍传教士【82】,一面倡导中国的信徒以签名来表示拥护“自治、自养、自传”【83】,接着是要割断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的表态,而化为控诉与揭发的政治行为【84】。所以当帝国主义被定义为敌人之后,它的侵略工具或者帮凶的含义也就昭然明确。既然他们是敌人的帮凶,那么间谍、特务、破坏也就变得顺理成章【85】。所以我们在看崔锦章的遭遇时,凭想当然地认为他藏有武器或做间谍的发报机。当然,我们许多人喜欢认为新政权是无神论的政权,所以他们无法容忍有神的意识,而以此作为他们对于打击宗教的解释。但我更认为,完全是为了集权政治的需要,与他们的意识无关,尽管他们往往从意识方面来说事。最终崔锦章被投入狱中,历受各种磨难、侮辱和虐待。这点让我想起齐家贞女士回忆她父亲齐尊周,他与崔锦章尽管所长不同,亦是一位对新政权充满向往并倾注自己了一腔热情,更重要的亦是为人正直,因数事表现出不同的看法,而最终被投入牢狱。
正如很容易将崔锦章与传教士关系变成间谍特务一样,齐尊周因在国民党政府供职而成为一名有贪污嫌疑的反革命分子。也正如崔锦章的家属被威逼要交出武器和发报机,齐尊周的妻女被威逼要交出贪污的钱财【86】。这是一个热衷于制造敌人的时代,崔锦章也好,齐尊周也好,当他们本性与人品不能屈从这样的走势,悲剧便就注定了。
前不久,作者发了一个视频给我,该视频是某个大学历史教授谈历史学家的美德,显然该教授混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他将求实看成了美德,求实实际上只是作为一个史学家最基本的素质之一,而最重要的美德,是通过史实来惩恶扬善。我认为这本《丹麦人在安东》也有这方面的特色,可能作者只是无意识地做到了这一点。
是为记。
何永全2022 年5 月21 日写于上海注释(注释中,引用的书籍中,“基督教”一词多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合称。)
【1】《丹麦人在安东》作者鸿路,由台湾新锐文创于2021 年5 月出版。全书共计506 页,分为十大章,有附录《安东基督教信义会政治背景汇报提纲》、《齐保廉申诉材料》、崔世光撰写的《安东丹国医院的终结》、柏卫的《四十年回顾》和《丹麦人在安东之历史年表》。
【2】姚民权、罗伟虹所著《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年出版)第29 页记载:先有英国长老会的宾威廉(W. C.Burns)在今天辽宁海城市,其去世后,有爱尔兰长老会的洪约瑟(J.M.Hunter)、韦特尔(H.Waddell)、卡逊(J.Carson)、苏格兰长老会柏威力(W.Park)于1869 至1876 先后到沈阳。
【3】王治心说:“当一八九六年时,丹麦路德会派柏卫、外得劳二牧师到关东三省,经过岫岩、大孤山、凤凰城、安貔口、金州、旅顺等处与长老会在营口商议传教地点,沿海一带划为路德会布道区域。于是外牧经营旅顺,柏牧经营大孤山。一八九八年开始岫岩为第三布道区,明年开凤凰城为第四布道区。一九〇一年开安东为第五布道区,一九一一年季天申开工于绥化。一九二三年在长春向女界布道,同时,开大会于凤凰城,改称路德会为信义会。”(《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5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出版)
【4】“丹麦信义会1896 年派出传教士抵东北旅顺港,在此得到苏格兰长老会和爱尔兰长老会的合作,从旅顺发展到大连及金州周边城市。1899 年他们传教至南满铁路上的凤凰城。1902 年。传入安东,在安东开设一座小医院。1906 年来到宽甸和怀仁。”(《中国基督教简史》第102 页)
【5】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五(1901 年4 月23 日)吉林将军长顺奏联合俄员剿抚杨毓林等起事各股情形片:“前因俄人收我枪械,以致遣散各营多半中途逃散,土匪趁机勾结,盘踞山中,聚成大股。抚之无饷,剿之无兵,颇为棘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68 页,中华书局1985 年出版)又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二(1902 年7 月6 日)吉林将军长顺等奏俄员干预招抚请转商俄使劝导以靖地方折:说沙俄军队对清兵“收取枪炮,轰毁籽药,限我兵力,散我兵团。”(同前书,第78 页)
【6】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1901 年6 月14 日)吉林将军长顺奏杨毓林等声势大不服收抚片:“伏查吉林自俄兵入境,各营军械大半为其收去。现在防军裁撤,仅留捕盗队四千三百名,散布各区,饷械两绌,以之搜捕零贼尚嫌地阔兵单,一遇大股贼匪,其势必不能敌。”只得联合俄兵共同打击贼匪。又“近日谣传均谓俄国不日撤兵,各处土匪群思蠢动,且有毁铁路以泄忿之意。此言果确,则吉省安而复危,大觉可虑。此等情形,不独吉林如是,征诸所闻,……奉天及关内外一带更有甚于此者。此岂一省之患,抑亦全局之忧。”(《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70 页)
【7】光绪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1901 年8 月8 日)盛京将军曾祺等奏与俄军合力堵剿刘弹子、杨玉麟等股军情折:“张桂林匪至怀仁,其属下林七于二十九日突入宽甸县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73 页)
【8】《丹麦人在安东》第11 页。
【9】《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73 页。
【10】据王治心所说,义和团动乱最惨烈的为山西、直隶,其次就为奉天了。(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87 页)
【11】《丹麦人在安东》第13-16 页。
【12】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1906 年1 月24 日)盛京将军赵尔巽奏折:“奉省频年兵燹,民匪混淆,民间失业者愈众。乡里豪猾动辄啸聚,椎埋剽掠,视若寻常。每股动辄数百人,少亦数十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88 页)又,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908 年3 月1 日)奏折,奉省“积习相沿,寝成风气,遂至无地不有匪踪,无时不有匪患。”(同前书,第97 页)大股土匪近十,其中离安东最近的就有杨永山一股。其他散匪,“少则数十人,多或百余人。兵来则散,兵去则聚。聚则为匪,散仍为民。”(同前书,第99 页)
【13】特别是基督教的传教士。例如在浙江温州的英国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他认为传播福音要到乡村去,自己也身思力行。(见三联书店2021 年出版的沈迦《寻找苏慧廉》第74-79 页)再如:基督教传教士到云南傈傈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传教。(见《中国基督教简史》第95 页)又如英国循道会的裨士(G.Piercy)以广西梧州为基地,深入穷乡僻壤。(见前书,第27 页)在《丹麦人在安东》也有类似的记载。
【14】史维东云:天主教徒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既有乞丐,也有自耕农,既有工匠,也有从事贱业者,有男女老少,还有已婚者和单身汉。”(见《中国乡村的基督教》第47 页,吴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出版)沙百里说:法国司铎梅神父(Jean Martin Moye)在中国川东和贵州一带传教,传教的对象大部分是文盲。(参见《中国基督徒史》第215 页,耿昇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出版)天主教徒如此,基督教徒也是如此。贝德士说:“多数基督徒为平民,无知甚至是文盲,而且非常贫穷。”(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102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2017 年出版)
【15】据《中国基督教简史》统计,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动乱爆发,全国共发生大小教案约400 余起。(见该书第116 页)但这里需要关注是,从签署各种条约后,传教士深入内地,信教的教民遭到各种歧视和不公。这点可以从1861 年之后的十多年中清帝咸丰、同治下达的谕旨中看出。如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二谕旨:要求地方官员“持平办理。如习教者果系安分守己,谨饬自爱,则系同中国赤子,自应与不习教者一体抚字,不必因习教而有所刻求。”又如同治元年三月初十谕旨:要求地方官“不得心存偏重,以示一视同仁之意。”(清李刚己编《教务纪略》卷首,上海书店1986 年出版。)
【16】王治心说:传教士的不幸,与不平等条约发生了关系,所以有不少明达的西方传教士,曾经电呈他们的政府,表示愿意脱离条约的保护。(参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359 页)《教务纪略》卷四下《粤督陶(陶模,字方元)复李提摩太书》:“惟传教之约既因兵事而立,于是中国民人意为外国传教特以势力相驱迫,而疑畏之心遂生。”
【17】例如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一谕旨:“地方官仍前玩泄,致醸事端,既从严惩办。各省将军督抚等亦必一并严惩不贷。”之后几年中,不断下了类似的谕旨,而且惩罚愈加严厉。如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谕旨:发生教案,“定将该地方从严参办,并将该督抚等一律惩处。”再如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五谕旨:再闹出教案等涉外事的,“该管督抚、文武大吏及地方有司一律革职,永不叙用。不准投效他省,希图开复。”
同日复下谕旨:有“杀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各城镇摡停文武各项考试五年,以示惩儆。”(以上所引均见《教务纪略》卷首)
【18】马特牧师(R.M.Mater)在1898 年第二次山东传教士大会上宣称:“目前的处境是危险的,因为近期颁布的法令给予外国人非比寻常的威望,并且要求从速办理涉及他们的案件。官员们害怕引起外国人不满而可能使用高压手段。我建议差会联合行动,以防止总理衙门因为过度迎合外国案件而导致处理不当。”(《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180 页)
【19】如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电谕:“令各省保护各国教士。各该将军督抚务当严饬地方官,于教堂所在教士往来之处,一律认真保护,不准稍涉玩懈。”又如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五谕旨:“再责成各直省文武大吏通饬所属,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须切实照料保护。”(《教务纪略》卷首)
【20】《教务纪略》卷三下《奏定地方官接待主教教士事宜》中,总理衙门制定了地方官与传教士对应的接待规定:总主教或主教的品位与督、抚同,可见督、抚。“摄位司铎、大司铎准其请见司道,其余司铎准其请见府、厅、州、县各官。自督、抚、司道、府、厅、州、县各官亦按照品秩以礼相答。”
【21】《教务纪略》卷三下《传教洋人不遵约章请饬申以条约》中指出:“各省州县平日既不知条约为何物,临事岂能执条约以办事?”正因为如此,有些中国人为了糊弄官员,增删条约中的条文。(如《教务纪略》卷四下《耶稣教教士敦崇礼山西教案善后章程》有云:“尝见坊间所刊通商约章,有与英文原稿不符,随意加减者。”)。不仅中国自己,外人也借机增删修改条约的内容。例如,1860 年《中法条约》第六款,翻译加上了传教士可以租赁或购买土地而修建营造教堂与住宿的内容,而法国官方条文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内容。
直到五年后的柏尔德米协议才将这内容正式定了下来。(参见《中国乡村的基督教》第109-110 页)又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坦言,中国的官员闭塞又愚蠢,对当今世界事务一无所知。之后,有些见识的官员提出派遣学子外出留学的想法。
【22】《教务纪略》卷三下《总理衙门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举案例:“四川教民妇女骗赖平民租项,反戮平民,身犯国法。主教者居然行文说情,教民妇女竟不抵罪。”再如:“历年奸掳焚杀首恶教民王雪鼎、张添兴等虽已议罪,终不到案。其司铎覃辅臣纠众杀毙团民赵永林等二百余名,梅教士声称已赴外洋,不能查办。”沈迦说:“中国教案频发,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是传教士利用享有的条约保护伞,向官员施加压力,甚至直接发起挑战。这种保护伞效应也是政府、士绅乃至一般民众反对‘洋教’的历史原因。中国教会史上的诸多悲剧渊源由此。”(《寻找苏慧廉》第119 页)“有些不良分子,抱着别种目的,进入了教会,不免有包揽词讼,藉势欺人的事,神甫、牧师受其蒙蔽,出头与官厅交涉,特别在天主教中常见的事,成了闹教仇洋的原因。”(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21 页)
【23】从内地会的章程来看,基督教传教士还谴责天主教传教士过于轻易求助于公使团的做法。(见《中国基督徒史》第259 页)基督教中以传教士“干涉词讼为大戒,而努力于教友信德的培植;使教友都能洁身自好,不求个人的利益。”(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22 页)
【24】王治心在他的著作中阐述当时抨击基督教主要是陈独秀的唯物主义,胡适的经验主义,也就是科学为上,以及钱玄同的疑古思想。当时的非基运动的理由“大都是以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与信仰科学万能为出发点,后来才走到反帝国主义的路上。”(见《中国基督教史纲》204-205 页)
【25】当时的国民政府表态:“本党对于宗教问题,取信仰自由之义,对于此次反基督教风潮,亦本此态度处之。”(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09 页)
【26】“在广州原拟招募二万五千暴徒,准备在十二月廿五日,散往各处教会机关,实行暴动。”最终未成。
但在其他地方,得到政府党部的特许,“闽、浙、湘、苏、赣、鄂等处,常有捕捉传道牧师,反缚戴纸帽,游行市中,百般侮辱,且有因而丧命之基督徒。”(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08 页)
【27】《教务纪略》卷四上《直隶藩司周善后谕贴》文中要求,致信传教士不可用公文信面,不可称他们为老爷。《教务纪略》卷四下《大主教、主教樊国樑教案善后章程》第一条:不赞成用大人、老爷来称呼主教、神甫。
【28】见《教务纪略》卷三下《粤督陶整顿教务章程》。
【29】沙百里在其著作中给了我们一个很典型的事例,说是北京向南约150 公里有个东闾村,该村住有蔡、杨两族,两族住地隔着一个水塘,水塘中有一佛塔。姓杨的一族听信他们贫穷是因水塘的佛塔所造成,于是擅自拆了佛塔。姓蔡一族遂告到保定府,杨族惧,因擅拆佛塔按律问斩,于是问计于邻村亲戚。告知信教可免。正巧有刘神甫在,杨族以愿灵魂得救而入教,于是祸免。(见《中国基督徒史》第239-240 页。)。
《教务纪略》卷三下《总理衙门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有例:“贵州入教者遇有讼事,自称教民,以为护符。”
【30】关于英国这个历史状况,在今天已经有很多中文书籍了,所以也就不引出处了。
【31】《教务纪略》卷四上《保护长江一带及苏杭内地商教》:两江、湖广、四川总督、浙江、江苏巡抚会同上奏,赞同杨儒等提出的保全各国使臣及各省洋人为第一要义。
【32】例如同治五年(1866 年)下达:“教士除教务外,不得干预一切公私事件。”又如光绪十二年(1875年)“凡奉教人遇有讼事,悉听地方官审断,教士不得干预。”
【33】关于此类问题,记录较多。例如:《教务纪略》卷三下《总理衙门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提出:“遇有教民涉讼,听凭地方官从公审断,传教士不得插身帮讼。”更不能包庇隐匿涉讼的教民,使其不到案受审。
《教务纪略》卷四下《美国李佳白民教相安议》:“华人入教之先,主教者当细访其行,可收者收之,不可收者去之”。又《教士联会防讼释疑说略》中明确规定:“奉教华人仍为中国子民,非惟不可抗逆官家禁令,更宜恪守政府法度。”“教会欲召诚信之人,不愿来假冒之人。万一假冒混迹其间,……我教会同以此等作为,深可摈斥。愿白于海内,凡遇不逞之徒,不妨据实通知,教会必不容纳袒庇。”内地会章程中明确规定:基督教传教士不得庇护被控有罪的信徒。(《中国基督徒史》第259 页)又《大主教樊国樑教案善章程》规定:“教士不宜干预词讼也。”“收人入教宜慎也。”“有人投教,宜查明有无事故,是否诚心。”“入教后当遵守教规,讽习经典。或一年或半载,察其诚心求道,非为他事,乃准入教。”1909 年美以美会华西宣教大会规定:愿入教的信徒,考验6 个月并有足够的推荐;随后接受洗礼和教众认可,才可进入教会。(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86 页)
【34】沙百里指出:《北京条约》使基督教传教正式合法化,常任的公使团在北京代表了主权政府。因此,中国的基督徒也能求助公使团以对抗中国的法律。“当然,不少坏蛋也会利用这些意外的好处。”(《中国基督徒史》第226 页)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二谕旨:教案层叠不穷,“推原其故,总由人心诈伪。每有莠民藉入教为名,横行乡里,倚势作威,藉端兴讼。一不遂意,则以肤受之愬,使教士闻之不平,代为申理。”地方官员“遂成偏重之势,平民被抑,积愤滋多,匪徒藉此煽惑,激成事变。”(《教务纪略》卷首)。《教务纪略》卷三下《总理衙门各国大臣商办传教条款》:自从签署条约后,对于天主教“华人皆轻视之。加以入教者倚势欺人,不服之心固结不解。迨民教相争,酿成案件,地方官理当查办,教士又出而庇护,教民藉此藐视官长,民心更为不服。且当中国有事之秋,一切罪人、讼棍俱以教中为逋逃薮,从中生乱,百姓始而报怨,继将成恨,终且为仇。各处民人不问天主、耶稣有无区别,而皆指为天主教;不知西洋各国疆界有分,而概视为外国人。祸端一启,凡驻居中国之西人,所在皆为危境。”再如:“同治五年,贵州巡抚案报贵定县有冉石保等先曾从贼,嗣入教民袁玉相、夏正兴团中,藉教中声势,纠众杀害王江保、左寅寿二人,重伤三人,将其家财什物牛马,掳抢一空。又查同治五年,贵州巡抚案报,遵义县公禀内有宋玉山、唐神仙、谭元帅、蹇远渊等先曾从贼,受伪职,嗣入教中,扰害乡城人民不可胜记。又有杨希伯、刘开文、郑小明、霍闻九、赵文庵等皆系遵属,素不安分之人,同入教中,在堂执事,乡愚被其讹索,孤弱受其欺凌。
出入衙门,干预讼事。若教民涉讼审虚,杨希伯等率领教民多人闹入县衙,强逼县官另断。教民被官管押,即用外国教士名帖硬请释放。他如强占人之妻女、财产及人命重案不可枚举。”
【35】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出版。
【36】《教务纪略》卷四下《粤督陶复李提摩太书》有:“民教相仇之过,其不因宗教起见”之语。
【37】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反对缠足,特别是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开办了女子学校后,竟将放足作为入学的必要条件。(《中国基督徒史》第273 页)
【38】见《教务纪略》卷四下。
【39】参见《中国乡村的基督教》第104-105 页。
【40】厦门大学创建者和校长林文庆在其著作中指出:“不公和腐败已经变成这片土地的常态。在任何法律诉讼中,如果没有钱或权势,无人能免受处罚。许多基督徒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依法达至正义,这一事实为无知者憎恨传教士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178 页)
【41】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06 页。
【42】最早想和解这两类矛盾的可以追溯到康熙身上,他于“1700 年11 月30 日正式宣言,说中国的祭孔祀祖,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纪念其过去的善行,并没有宗教性质。”(《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07 页)二十年后,部分传教士“允许基督徒不迷信的拜祖宗;为守礼节而祭孔也可以。”(同前书,第111 页)在《利玛窦-凤凰阁》(作者菲利普米尼尼,中译本王苏娜,大象出版社2012 年出版。)一书中,时间提前了三年,也就是1697 年,耶稣会士们得知罗马教廷为祭孔祀祖是否与敬拜上帝相冲突时,他们向教廷提交了康熙的说法,祭孔祀祖是民俗而非宗教仪式。(第284 页)到了清末,这样的认识更被接受。又如《东抚周复赫士书》:“中国祀典昭垂,不外报谢与景仰二意。祭神如神在,并非误以木偶为神。” 《大主教主教樊国樑教案善后章程》:“孔子道德,西人亦皆钦敬,惟不行祭孔之礼,不助修庙之费。”(《教务纪略》卷四下)
【43】《利玛窦-凤凰阁》第277 页。
【44】我们从康熙的父亲顺治那篇《御制天主堂碑记》就可以看出,褒奖的是汤若望的治历,对天主教的教义不置一词。康熙是这样,雍正也是这样。
【45】《中国基督教史纲》云:“教难虽平,传教之禁仍为解除,西士不能传教,华人不准进教……”(第101 页)
【46】沙百里说:要使康熙跪在上帝面前的设想,“完全是幻想”。(《中国基督徒史》第178 页)
【47】例如,雍正元年的谕旨,直接将传教士称为“远夷”。咸丰八年(1858 年)在与英国的条约中,才明确规定在与外国的公文中不得使用“夷”字,显然并没有完全杜绝,更不要说在民间了。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总理衙门为此事上奏,要求再次禁止对外人使用“夷”字,得到批准。将外人称为夷的,我们直接可以在有明的文献中找到,而并非只有清廷才有。
【48】将天主教的教义说成是左道,在明朝已经开始。之后有清的杨光先写成的《辟邪论》,亦可称作代表。
雍正、乾隆两朝,苏州发生以“洋人散布邪说,煽惑良民”之罪绞杀传教士。乾隆十一年六月廿六日(1746年8 月12 日)颁下谕旨,直接斥天主教“挟其左道,煽惑人心”,也拉开了在全国禁止天主教的大幕。史维东认为:“绅士将传教士当成社会政治上的敌人,把基督教看成异端邪说。”(《中国乡村的基督教》第5页)史维东在他著作的第140-141 页中说道:“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只要一提到天主教,全国上下的官绅士民都会联想到邪教或非法活动。”在江西赣州的揭帖,号召杀死“天主教匪”。
【49】据《中国基督教史纲》统计,这场义和团动乱,天主教主教5 人、教士48 人、教友18000 人被杀;基督教教士188 人,教友5000 人被杀。(第175 页)北京所烧西人住宅34,教堂18,男女学堂23,传道学堂4,施药局12,医院8,印刷所3,盲人学堂1,天主堂2。(第179 页)沙百里认为:因此死亡的中国的天主教徒可能超过3 万。(《中国基督徒史》第237 页)最为惨烈的山西,“一位姓顾的女教士,因为要抢救一个女孩,落在后面,拳匪就把她连女孩一齐推在火里烧死。”巡抚毓贤命人,同时还亲自动手,“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末了杀孩子,把首级号令在城上。那天杀死的西人,天主教有2 个主教,3 个神甫,7 个女修士;耶稣教有牧师夫妻16 个,医生夫妻2 个,女教士12 个。”拳匪“用种种残忍的方法,如挖心、挖眼、肢解、活烧等等,真是惨不忍说。”(第184 页)这完全是反人类的暴行了。沈迦说:“据说,拥有洋货,如灯泡、钟表、火柴的人,在当时也可能成为袭击目标。”(《追寻苏慧廉》第154 页)
【50】如文章中所引《英教士在山东传教章程》中明确规定:“凡娶妾、赌博、吸鸦片,因教断亲,邪行法术,夜聚昼散,倚教弃族,恃教惹事,全不准行。”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的内地会章程中:明确规定向不道德的性关系、赌博、鸦片宣战。(《中国基督徒史》第258 页)1909 年美以美会华西宣教大会明文规定:禁止吸食、种植和销售鸦片;禁止赌博或酗酒。(《《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86 页,)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顾维钧在1916 年的芝加哥大学会议上说:“许多划时代的改革,比如反对鸦片与禁止缠足,都受到传教士的鼓励。”(见前书,第95 页)
【51】如杨格非(Griffith John)就为此批评他的本国政府。传教士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说:鸦片贸易是“基督教的羞耻,它严重阻碍了中国人接受基督教。”(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57 页。)“1926年,教会联邦委员会(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份声明,敦促废除治外法权。大多数传教士和传教团已准备好放弃其特权━━比他们的政府或外贸部门都提早表态━━于是他们被批评只为中国人作贡献,而不帮助自己国家的商人。”(见前书,第136 页)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联合请求脱离传教条例的保护。提出脱离条约的保护中外人士不少,可参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15-216页。
【52】苏慧廉肯定称不上一名医生,当有一名姓丁的秀才,请他为其戒毒。苏慧廉为其戒毒成功。(参见《追寻苏慧廉》第79-81 页)由于首次戒毒成功,就有人慕名而来,苏慧廉决定开办戒毒所。两年之中,有三四百人接受了治疗。(同前书,第84 页)《追寻苏慧廉》第229-230 页引《张棡日记》中有英国医生包莅茂在温州为四名吸鸦片者的戒毒事迹。1890 年,传教士们发起成立“中华国民拒毒会”。(《中国基督教简史》第143 页)贝德士在他的著述中也提到传教士开办戒烟所。(参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95 页)
【53】贝德士说:“传教士开设医院、麻风病院、盲聋学校、孤儿院和戒烟所,并为妓女和黄包车夫提供服务。”(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95 页)传教士医生于1891 年在广东创办第一所麻风病院。传教医生嘉约翰除了主持惠济医局外,另一举措就是他于1898 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参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58 页)关于麻风病医院的创立,王治心有述。(参见前书,第260-261 页)
【54】例如,利玛窦的弟子也可称得上挚友的瞿太素在洗礼前,必须将自己小妾扶为正室,并承诺不再娶妾。(参见《利玛窦-凤凰阁》第251-252 页)又如,李之藻的亲朋中有一名叫卢卡的富商,将自己的姬妾打发安置毕,才能接受洗礼。(同前书,第268-269 页)
【55】传教士们不仅将纳妾视作有违教义,还将烟、赌、酒、嫖视作不道德。王治心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可参见其著《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67-271 页。
【56】基督教传教士更重视开办医院,也正是他们把西方的医学带进了中国。1835 年基督教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开办眼科诊所,名为新豆栏医局,也是在中国第一家西医医院。该医院分文不取,施诊给药。之后该医局更名为惠济医局。(参见《中国基督教简史》第51 页)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JohnGlasgow Kerr)接手惠济医局,在华44 年,共诊治病人14 万人次,施行手术4.9 万人次。(同前书,第55页)1905 年,全国3445 名基督教传教士,就有301 名医生,其中94 名是女医生,他们效力于166 家医院和241 家门诊所。这一年,35301 名病人住院接受治疗,而接受诊治的超百万人次。(《中国基督徒史》第275 页)据《中华归主》统计:1920 年在中国的教会医院有246 所。其中著名的医院有:上海仁济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山东齐鲁医院、长沙湘雅医院等。至于教育,据《中国基督教简史》第202 页转引《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统计:至1921 年,幼儿园139 所、小学6599 所、中学291 所、师范48 所、大学16 所,还有盲童学校和聋哑学校。著名的大学有: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等。聋哑盲童,在中国社会中连个正常人的尊重也不会的得到,遑论还能接受教育。关于传教士创办盲童学校、聋哑学校可参见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72-274 页。
【57】传教士柏卫办医院。(见《丹麦人在安东》第11-13 页)对于丹麦传教士办医院亦可参见邱广军《清末民初基都教会在中国东北的医疗传教活动》一文。(见《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第128-14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出版)柏卫办学校。(见《丹麦人在安东》第17-18 页)传教士聂乐信办学校。(同前书第17、52-58 页)聂乐信办贫民救济所。(同前书第59-61 页)传教士于承恩开办的中学里有当时很出色的种植园,并颇有名气。(同前书第210-227 页)传教士郭慕深创办女子医院和育婴堂,特别是育婴堂的经历曲折,见《丹麦人在安东》的《风雪夜归人》一章。根据1922 年编撰的《中华归主》统计,丹麦路德会在东北创办了29 所初小,11 所高小,3 所中学。
【58】见《丹麦人在安东》书中的《小城的纪念碑》一章。
【59】李纪《十九世纪天主教在中国东北的传播》一文中说:“19 世纪初,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法国5 个城市设立了筹款组织,定期向登记的市民收取捐款,用以支持巴黎外方的海外传教事业。”(见《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第110 页)在作者《丹麦人在安东》也多处提及传教士回国筹款以及丹麦寄来资金。
【60】见《丹麦人在安东》第11 页、第18 页。
【61】实在太多:如丁则良所著的《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1951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再如姚民权、罗伟虹所著的《中国基督教简史》,当然后者平和了许多。又如陈才俊《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对“满洲”的认识》一文中一面说大部分传教士“远赴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福音”,一面则称他们是“其最高利益准则是国家的长远利益和教会的传教利益”。(见《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第82 页)
【62】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05 页。当年利玛窦等人到广东韶州就被安排住进当地的南华寺,他表示不愿意,地方官觉得很是诧异,问道:你们不是说自己是僧人吗?利玛窦穿了12 年的僧袍后,终于改穿儒服,留发蓄须,遵循中国文人的生活习俗。(参见《利玛窦-凤凰阁》第142-144 页、158 页、165 页、204页)
【63】这个问题当年的耆英说得直截了当,他在与法国人签订条约时强调:“在中国,民众集会只会作恶。
佛教徒和道教徒均不可聚众集会。倘若准许,必为恶民用作谋叛的借口。”(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163 页)
【64】见《利玛窦-凤凰阁》第277 页。
【65】见《中国基督徒史》第179 页。
【66】见《中国基督徒史》第181 页。
【67】见《中国基督徒史》第178 页。
【68】见《中国基督徒史》第184 页。
【69】贝德士似乎看到了这点,他说:“自发的组织被疑为潜在的政敌,有可能煽动叛乱和推翻统治的政党或王朝。”(《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57 页)遗憾的是他没有紧紧抓住这一点,并作为一个重点来阐述。
而造成这样的不足,是贝德士认为统治者更多的反对是教义。
【70】贝德士说蒋介石:“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从基督教中汲取了可以强化其革命、民族和军事决策以及美德的元素。”(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137 页)
【71】贝德士说:“随着蒋介石及其追随者在1927-1928 年取得胜利,反基督教运动中比较激进和动荡的方面渐渐消退,但事实上,在整个国民党统治时期,仍有反基督教的紧张气氛。教会也被要求向政府注册,但从注册条件来看,政府完全不理解教会的本质与功能。规章制度似乎要在政治层面限制教会成员资格,这完全不可接受。”(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105 页)于是贝德士责问道:“当统治者和国家控制某些宗教人物时,宗教是不是再次像从前一样成为国家的仆人?”(见前书,第106 页)贝德士例述国民党人物像廖仲恺、蔡元培、汪精卫、陈立夫反基督教的言论之后,举出一位代表国民党反基督教的人士,他宣称:“在党的领导下,禁止任何宗教拥有实体组织。”请注意“实体组织”四个字。接着贝德士认为对蒋介石等人作为基督徒心怀感激,但他们从未真正将自己与基督教会、教堂、信众组织和集体等联系起来。贝德士进一步指出:“在任何意义上,他们都不是基都教会和服务团体正常基本运转的重要支撑,但是,却是对抗敌人(尤其是党内和政府敌人)的保护伞。”(参见前书,第190-195 页)“党的控制对于教会而言确实是不适合或不能接受的,而且这也侵害了宗教自由。”(见前书,第201 页)
【72】参见《丹麦人在安东》第228-230 页。实际上,三育中学的遭遇并非个例,那时对满洲国皇帝照片、国旗、国歌不敬的,尤以教会学校为最,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勒令停办,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教会学校被停办,学校传教士被抓更为普遍。(参见《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第188-192 页)
【73】中国基督教徒之所以成为如此,我认为宋泉盛(曾任台南神学学校校长)在1948 年已经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目前最普遍的宗教号召局限于利己主义的说教,及旨在个人得救的利己主义的热情。”(《中国基督徒史》第306 页)他们至今还陷于“廉价恩典”中不能自拔,这不仅是官办的三自教会,连有点自主的家庭教会也是普遍的状况。
【74】满洲国规定,教会学校也必须尊孔,读儒经。1935 年3 月,满洲国教育大臣以书信形式向教廷保证,学校里规定的儒家礼仪,纯属政治问题并不具有宗教色彩。(《中国基督徒史》第301 页)
【75】参见徐炳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对基督教会的控制》一文。(《文本、地域与解释的新视角》第150-160 页)贝德士说,在日伪统治的沦陷区,“教会虽然是合法的但仍被视作可疑机构。”日本人“他们试图在日本牧师的帮助下,以一种便于指挥和控制的方式组织中国教会。此种努力在东北地区获得极大的成功,在华北地区亦是如此。”(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207 页)
【76】1877 年,在山东烟台召开的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中国传教士有473 人。(《中国基督教简史》第139页)1890 年5 月27 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当时就有中国传教士1296 人。(同前书,第141页)1926 年10 月,有6 名中国主教进铎。该年外国天主教传教人员为3059 名,中国传教士为1184 名。(《中国基督徒史》第288 页)依照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1900 年,外籍传教士886 人,中国传教士470人;1910 年,外籍传教士1391 人,中国传教士521 人;1920 年,外籍传教士1364 人,中国传教士963人;1930 年,外籍传教士2068 人,中国传教士1500。(第190 页)
【77】在戴德生组建的内地会中,其中就有成员提倡教徒们自筹资金和将传教的领导权交给中国人。(《中国基督徒史》第259 页)苏慧廉在1927 年2 月的《差会与中国》中写道:“就说温州吧,为了将它发展成为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我已经谋划了超过三十年。我的同事,包括中国和英国的,都一直为此不懈努力。我曾反复对中国教会说,我们不可能永远当他们的‘保姆’。”“就我们而言,只要有人胜任中国教会的工作,我们非常乐意双手将其奉上,绝不吝啬及勉强。……差会这些年来制定的政策都是为了使中国教会稳步向自治与自养的方向发展。我建议,现在可以更进一步明确,给当地教会提供津贴的同时,委派中国人担任委员,独立处理教会事务。”(《寻找苏慧廉》第435-436 页)贝德士写道: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模式自19 世纪中期以来就存在于传教士圈中。(参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64 页)至1920 年,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独立教会。作为差会从1900 年以来,他们在20 年中为逐渐强化中国教会而作准备,但在一些主要工作方面,包括一些政策的制定,仍然在传教士的手中。“事实上,多数传教士真诚渴望中国人管理教会。教会资金的来源一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见前书,第83-84 页)另外,中国信徒们也在积极地本土化,如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和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有六百多处,散布在河南、河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等地。(参见《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13 页)王治心援引《教会的宣言》中呼吁:“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怕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有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见前书,第214 页)
【78】贝德士援引1907 年百年纪念大会会议记录对差会的说明:“用于差会的钱有一些是来自富有的基督徒大量的捐赠,但更大一部分钱是来自那些并不富裕甚至是非常贫穷的人。”当然其中也包括中国基督徒的捐赠。而这些基督徒他们目的是使人们美好富足,“这中间没有任何政治的或与之相关的动机”。(见《中国基督教史著述选译》第236 页)
【79】沙百里说得比较婉转:“信徒们被要求参加各种的学习会。在会上,他们的信仰并不遭受直接批评,但却渐渐被人民,对科学论据,对社会主义建设,而最终则是对党的信仰所取代。”(《中国基督徒史》第312 页)
【80】见《丹麦人在安东》第38 页。
【81】见《丹麦人在安东》第65-79 页。
【82】据沙百里统计1951-1955 年间,有5000 名天主教教士和修女、1000 名基督教牧师被迫离开中国。(《中国基督徒史》第313 页)其中最有名的是罗马教廷大使黎培理因坚决反对“三自”运动,于1951 年9 月5日被驱逐出境。(同前书,第316 页)
【83】至1953 年9 月,在《三自宣言》上签名的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已达40 多万,占全国总数一半以上。(参见《中国基督教简史》第274 页)据统计,1949 年,基督徒共有835000 人。(同前书,第245页)
【84】早在1950 年5 月6 日,周恩来在与基督教人士会谈时说:“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简史》第260 页)1951 年2 月22 日,《人民日报》在发表《南充宣言》时指出:“断绝与以美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切关系。”“断绝与梵蒂冈的经济及书信往来。”(《中国基督徒史》第315 页)据姚民权统计:至1952 年9 月底,全国124 座城市举行了169 次较大规模控诉大会。(同前书,第273 页)
【85】1951 年4 月,中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召开会议,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讲:美帝国主义会利用基督教来进行文化侵略和间谍活动,爱国的教徒们要揭露基督教团体的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及国民党反革命匪帮分子。(参见《中国基督教简史》第270 页)之后在控诉会上,控诉的内容则是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怎么破坏中国基督教爱国运动,怎样以超政治论点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还揭发传教士搜集情报,从事间谍活动,以及中国信徒追随外国传教士,充当走狗、败类等等。(参见前书第273 页)
【86】对于未来,齐尊周表示:“我要留在大陆”。他看到“独立民主自由幸福的前程,就在我们的前头”。
关于齐尊周的1949 年后的遭遇,以及其妻女被威逼细情,可参见齐家贞所著《黑墙里的幸存者》上册第117-155 页(该书由台湾新锐文创于2014 年出版)
参考文章:
崔世光:安东丹国医院的终结——《丹麦人在安东》序
鸿路:育婴堂末日
鸿路:凯撒的归凯撒 上帝的也归凯撒
鸿路:牧师的绝路
(议报 2022年6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