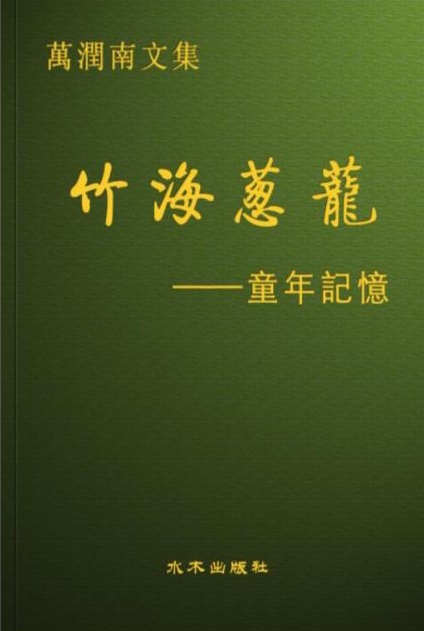1-13 转学上海
刚开始在英驻小学读书,我不是正式学生,而是跟着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上学的伴读生。农村女孩子入学率低,许多是因为是要在家带弟弟妹妹。学校便推出一项德政:只要在课堂上不闹,可以带着弟妹一起来上学。我便是这项德政的受惠者。
第一学年大考,我也要了一份试卷做着玩。结果算术考了100分,语文考了99分,是全班的最好的成绩之一。因此我理所当然地转了正。我还记得语文考试被扣了一分,是因为我填空时写错了一个字:把“野”字的右边旁“予”写成了“矛”。我至今还认为我“矛”得有理。千里茅(矛)草谓之野,何“予”之有?
很强词夺理吧?哈哈,我的自以为是,小时候是出了名的。这源于我同光浩舅舅一起做作业,完了互相对答案,凡是不一样的,我都照他的改了,因为他是舅舅嘛。结果全错!而我原来的答案,其实全对。后来我把运算过程中的每一步为什么会错也琢磨清楚了。这次教训让我刻骨铭心,从此只要别人同我不一样,我就毫不犹豫告诉对方:“肯定是你错了!”而且还清楚地告诉对方:你错在哪一步了……
我在宜兴外婆家读完小学二年级,要到上海父母身边去读三年级了。我从小也算是“颠沛流离”:从县城到上海,从上海到乡下,都是母亲抱着、外公用箩头挑着。这一次,是我头一回自己迈步离开外婆家。
从黄玕村往东北方向步行三里地,便是新建,那里有轮船码头。我和外公在那里搭上了班船。小火轮噗噗地喘着气,不紧不慢地把我们载到了常州。在那里换乘上那种站站都停的慢车。火车哐当哐当地摇晃着,把我们晃到了上海。
大清早从外婆家启程,到上海已是万家灯火、满天星斗的深夜。马路上已是空落落的,一辆摩托车呼啸而过,外公赞了一句:“这放屁车,跑得真快!”
习惯了乡下的空旷和一望无际,高楼林立的大城市让我感到不安和局促。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新的生活开始了。
那时候我们住在巨鹿路271号,门前是小菜场。我们家租的是二楼的双亭子间,房东是楼下德泰生南货店的老板。老板姓柴,宁波人,有两个公子,老大叫松年,老二叫永年。那个叫松年的很不是东西,常常欺负我这个乡下人。
我跟着姐姐上巨鹿路小学,念三年级。
母亲对我们的学业抓得很严。每天都要背课文、默生字,而且有体罚。背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要用尺子打一下手心。我很少受罚,姐姐却常常挨打。姐姐因此觉得母亲偏心,一有抵触情绪,学业更受影响。
其实我姐姐另有其聪明之处。她口才好,灵牙利齿,不像我笨嘴拙舌;她唱歌好,我却是五音不全。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总是用一把尺子去度量,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
耳不聪则嘴不灵,在家里又只讲宜兴话,所以我的上海话很蹩脚。这让其他小朋友非常瞧不起。从乡下到上海,教学方式大不同,但我很快适应了。学习成绩虽不“出类”,但也略为“拔萃”。所以被任命为小组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官”。
当了小组长,我很尽责。找了一本新日记本,写上全组同学的姓名,后面划上许多格子,统计他们每天交作业的情况。交了就打勾,不交就打叉,一目了然。班主任冯老师在课堂上表扬了我。
这引起了同组的一个外号叫“茄子”的妒嫉。这个外号源于他的长相,想象一下:一付长脸,额头小,下巴宽,而且往上翘,像不像一个茄子?有一天,“茄子”神神秘秘把我拉到一旁,说他今天没有来得及写作业,但希望不要给他打叉。然后打开他的铅笔盒,说可以挑一支铅笔或一块橡皮送我。
那一年,我也就七岁,“茄子”最多八、九岁,小小年纪,就懂得行贿!我拒绝了他,告诉他东西我绝不能要,但可以网开一面。对他说:先不给你打叉,空着。赶快把作业补上来,再划勾。
我以为是帮了“茄子”的一个忙,谁料是遭了暗算。一会儿班长就来查我的作业登记,看到那个空格,没有说话,脸色却非常难看。这时候,“茄子”躲在一边,看着我们奸笑。
第二天,班长宣布我们那个小组改由“茄子”担任组长。
上海小赤佬,真真不得了,小小年纪,不仅懂行贿,还会设局、陷害、踩着别人往上爬。
后来听到有人总结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打不过一个四川佬;三个四川佬,斗不过一个上海小赤佬。
我这个乡下佬深以为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