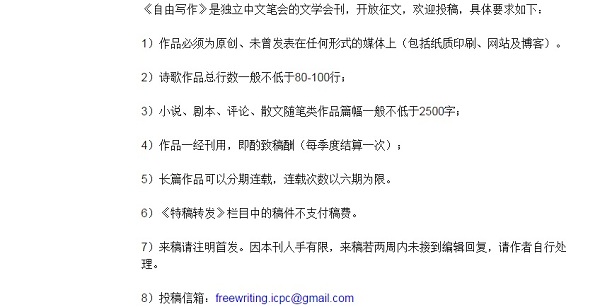三、流亡者的两重世界
造成二十世纪流亡这一现象大面积扩展的无疑是政治迫害的结果。世界上所有的极权政治都有话语强加癖嗜好,甚至想在民族性、宗教性、政治性、文化性、思想性信念上用整齐划一来归化,用意识形态全权话语来控制、吓堵国民,使之“犬儒一生”,成为“沉默不语”的羔羊。流亡现象就是这样孕育而生的,二十世纪产生的四个主要的流亡文学形态(俄国(苏联)、德国、东欧——以波兰和捷克为主、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例外地与反抗这种“单行道式”强加性全权意识形态话语相关,反抗的结果就是大批知识菁英被国家放逐和自我流亡。行使这种勇气的都是一批最出色者,中国有学者后来喟叹极权国家把知识菁英、国家良心排除出去是别有用心(淘汰菁英可以纯化犬儒份子):“1990年后,中国菁英出局,平庸才会如鱼得水。……平庸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极大的伤害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勇气。”(谢泳,《斯人流亡菁英何在》,收入《不死的流亡者》,362——365页)。
“流亡”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悲惨的命运,流亡者逃离困厄不前的现状,逃离专权独裁的国度,身体虽然是释放了,但却也被完全切断了和故国的关切联系,原乡已经在地理意义上与他毫无关系。这是所有“流亡者”面对的集体境遇,这对忧愁善感的流亡知识分子们是一个最大的精神打击,他们被割断了与母体脐带的精神联系,他们会为这个噩梦背一辈子的“游乡梦魇”枷锁。和遥遥无期的归途相比,梦醒后只有面对“流亡异国”的现状,他们要在白天与黑夜之间找到各自的栖息地,这是两种文化的纠缠,原乡和流亡地文化的黑夜与白天。这也是两种文化压迫,流亡者的文化命运是难以遗忘和难以进入。两个文化世界和两种文化压榨就横亘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炼狱后才能重生。萨义德说“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知识分子论》,45页)。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