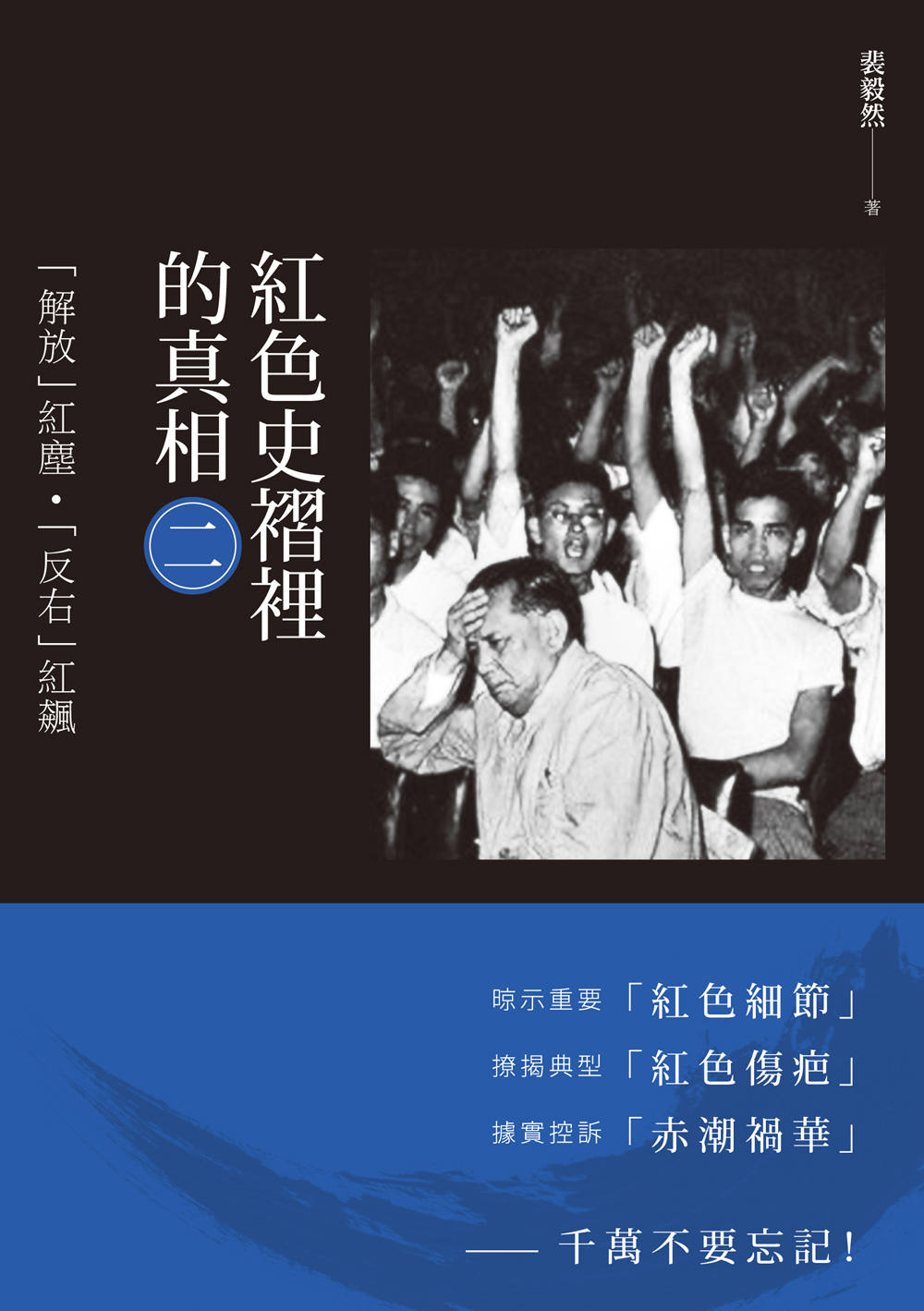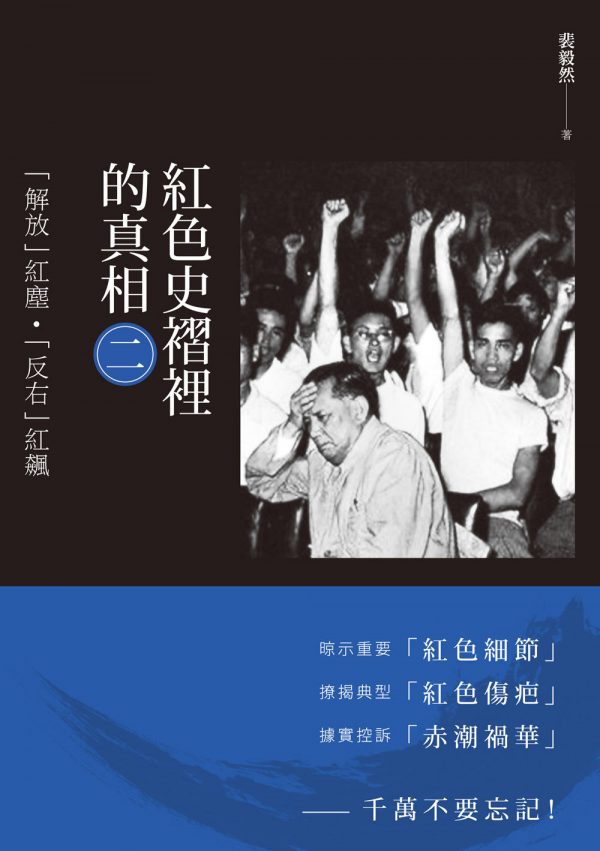 自序
自序
本集专述“激情燃烧”的1950年代,史褶滴血,疤痂未合。以事为证,以史为凭,多列证据,少发或不发议论。不过,这么一段血腥肃杀的疯狂岁月,实在做不到某些香港学者要求的“纯客观”。述史叙事不可能没有一点倾向性,只能尽量“莎士比亚化”——史论出自史实本身。
1950年代,中共暴力推进共产,用刺刀与漫画铺展“最新最美”的红色图纸,强塞大陆于马列之鞋,吾华进入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伟大毛时代”,腥风血雨、肃杀狰狞,长夜难熬。仅举一例——
1950年,西南师院外语系19岁女生郭辉霞,其父“逃亡地主”走投无路,两天未食,投江前见女儿最后一面。女儿领至寝室:“你躺一会儿,我去给你买两碗面条吃。”女儿没去买面条,而是叫来公安,一起将父押送回乡,女儿也参加斗争会。结果,先打“逃亡地主”,接着揪打地主女儿,“打她的骚勾子(屁股丑称)!”郭辉霞被扒下裤子打得皮开肉绽。西南师院吴宓教授认为太伤风化,专门找了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1]
土改、镇反、肃反,至少杀了200余万“阶级敌人”;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工商业公有化)、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61年至少饿死四千万“阶级兄弟”;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寰内士民瑟缩捱命于“无产阶级专政”。恐怖越来越浓,日子越过越穷,苦难越来越重,还须时时念叨“党的恩情”、天天得跪谢中共,必须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若无1950年代的“激情燃烧”,没有思想改造运动(六旬教授都得扭秧歌)[2],就不可能有反右、反右倾、大饥荒、文革、六四。没有马列主义的引导,就不可能有走入地狱的公社化;没有焚烧理性的1950年代“激情”,就不可能有公然失信天下的反右、不可能再演兔死狗烹的文革、不可能有坦克碾街的六四。
文革后,血腥“镇反”(镇压百万“反革命”)[3]、人祸“公社化”不便再提了,祸国深重的反右,明令“淡化”。但土改还是“大仁政”(穷人翻身),抗美援朝还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保家卫国”,大陆人民仍须继续磕头谢恩,无限怀念“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否则就是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破坏安定团结”,就是“妨碍国家安全”……
英国阿克顿勋爵(1843~1902)早有警言:
历史不仅是一个发现的航程,也是一个与敌人斗争的过程。敌人就是早已实权在握的人,这些人强烈希望隐藏真相。[4]
秽史者自秽,谤书者自谤。“伟大毛时代”真相渐露,天安门毛像摇摇将坠。但出于“合法性”,中共仍在精心装饰1950年代,似乎那是一段与民更始、百废俱兴的“美好时光”,大陆人民“意气奋发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中共之所以还在维护老毛形象,还在修补这段千疮百孔的灾难岁月,当然是“司马昭之心”。“红灯”仍闪,意识形态未拆违清障。“阶级本能”使中共敢做不敢书,动用一切手段遮抹血印,以推捱“历史审判”。只是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遮掩那只马脚——政治利益。还原1950年代真相,凸现这段被竭力“淡化”的史实,当然是正义的“填补空白”。
如今,中共已完全背叛马列原教旨、背叛“毛思想”,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以“三大改造”为标志的中国共运彻底失败,“西风”终于压倒“东风”。中共希望用“后三十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解释“前三十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法性,南辕北辙,驴唇马嘴,当然是永远无法完成的“历史任务”。
笔者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久伏“铁屋”,50岁才在香港惊悉“大饥荒”,研究方向发生“战略大转移”——从浪漫文学转向实沉史学,由于不合中共“主旋律”,在大陆完全边缘化,分赃式的各级课题一律与我无缘(无论我怎么申请)。从结果看,非常感谢见弃于“党和政府”,反而成就我研究的“价值最大化”,将我旋送至解析赤潮祸华这一大课题。出身大兴安岭的筑路小工,能参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大转型,以这样的方式“报国”,深感荣幸与焉。
官史无真,逢恶必讳,利益压倒是非。尤其当代史,钩挂诸多政治利益,阻力自必重重。不过,中共干都干的,岂有评说不得?亲感亲受,亲历亲述,势必“主观”,虽带好恶,但原始鲜活。后世学者纯粹依靠资料研史,缺乏现场感,多多隔膜,也有相当局限。
笔者从小嗜史,50岁由文入史,也算叶落归根。文学研究者不少中年转史,一些作家(如冯骥才)也从虚构转向纪实,大概也是“价值升级”。二十世纪国史如此苦难深重,文学毕竟高蹈轻浅,难羁我步。青年爱文,中年研史,晚年思哲,实在也是学人的“必由之路”。浪漫空灵的文学,难以承载历史之重。1980年代解冻初期那阵“文学热”,寒蝉仍噤,送走“两个凡是”,来了“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框定思想,不许揭露文革伤痕,不准指说毛共罪恶,只能用文学曲笔“弯着说”,文学因承担史学功能而显赫一时。随着反思深入,明晰直接的史学自然百倍给力于形象思维的文学。
1990年代,“六四”后去职的《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韩寅之女大学毕业,得自谋职业,向父亲抱怨。父亲乃1960届复旦新闻系毕业生,开导曰:“自找单位是难点,但较之我们当年的计划分配,硬‘拉郎配’,任掌权者摆布,家破人亡,撕心裂肺,口含黄连还不敢呻吟一声,今天的自由择业要强得多。”1960年该父毕业,父瘫、母瞎、妹肺穿孔,他打报告要求留沪照顾家庭。系总支书训斥:“你是革命第一,还是家庭第一?”他只能噙着眼泪咽着苦水,为53.5元工资赴赣。是年冬,其父见背,1964年老母去世。[5]笔者1982年大学毕业,系总支书教导我:“资本主义国家大学毕业哪像我们100%就业。”明明剥夺自由,却被说成“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歪歪理难道不需要拧过来么?
2013年,一位青年责问老年“右派”——
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他们?
这位老“右派”极为担忧——
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点担忧。前两年,我不再担心中国再会发生“文革”的可能,现在不了,样板戏又唱起来了,毛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者也要“讨个公道”了……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6]
我们这代赤祸亲历者(尤其人文学子)负有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将赤祸钉上史柱——“千万不要忘记”!
[1] 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页159~161。
[2] 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出版社1997年,页152~153。
[3]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透露:“镇反”杀了70万,1955年“肃反”杀了7万,1956年杀掉少一些。这些资料《人民日报》发表时删除。参见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上),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6年,页111。
[4] (英)达尔伯格·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11年,页334。
[5] 韩寅:〈漏船载酒泛中流〉,载张大芝等主编:《阴晴雨雪旦复旦》,香港华泰出版社2008年,页131~132。韩寅分配江西公安厅,改革开放后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六·四”去职。
[6]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2014年,页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