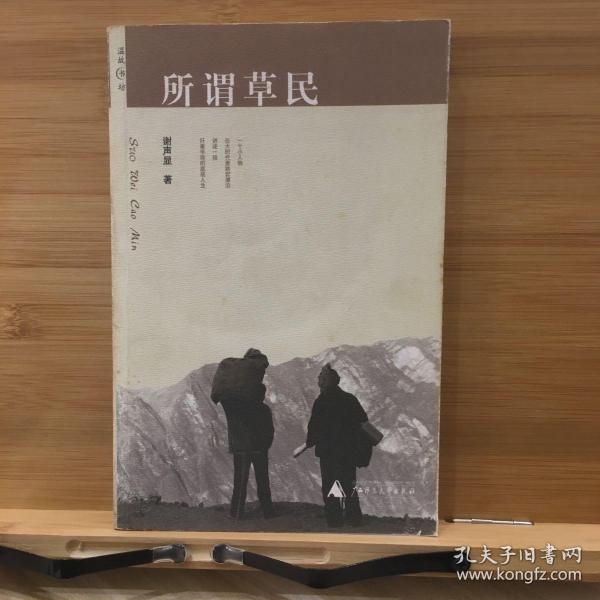第五章 十六仓(北山公园)
九 第一攻击波
星期六晚上。
每天晚饭后睡觉前,是仓内最安静的时间。
没有特殊情况,天井里不会开灯。外面黑沉沉的,仓里面的灯是彻夜长明,便成了查仓的看守在暗处而仓内的囚犯在明处的情势。如果有看守在这时放轻了脚步突然出现在风门前,就能轻易拿获那些违反监规的人,然后弄出去惩处。因此,北山公园内的人犯们在这段时间便特别老实,各自坐在自己的铺位上作出反省状。
朱必成占有临门那一边的第一个铺位,那是全仓最好的位子,在这个铺位上能通过风门望到天井,视野相对开阔,还能优先享受从风门洞透进来的珍贵的阳光和新鲜空气。此时,朱必成正靠在他用被褥叠成的土沙发上,好似老僧入定一般闭目养神。
巡廊上响起了哨兵换岗拉枪栓验枪的哗啦声。中学生循例压低了声音用普通话报时:“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20点正。”
每间牢房有一盏钉在天花板上的15瓦灯泡,灯泡外面蒙着钢筋作的网罩。看守所的电灯灯丝发红光线桔黄,人犯们顾惜眼睛,从不在晚上看有字的东西。高洁坐在自己的破棉絮上,正轻声背诵着主席诗词,偶尔还就其中某个词句的意思同我交流一番。
正在牢门边弯腰提夜壶的中学生突然头不抬身未动地从唇间发出了一声:“咝——”
全仓的人顿时都规规矩矩地僵住了,没人敢向仓门口张望,大家都变成了不能说话不能动的木偶人。
当时,北山公园内已将仓里不准喧哗的监规改成了不准说话。胡管理说过:“家伙们应该在里面静静地闭门思过。”长年累月被关在一间室子里的人绝不可能不讲话,再模范的人犯也做不到这一条。在那不审不判无所事事的牢房里,为了打发时间,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经历、亲友的故事讲过一遍又一遍。老校长就说过:“同仓关的时间久了,比夫妻之间都还要了解得清楚;即使是两口子,都不可能每天24小时都在一起互相盯着。”
但如果仓里谁正在说话时被抓住,那就得受罚了。处罚之轻重,也全凭那位看守当时的心情。因此,每个仓都有这么一条规矩,任何人只要一发现有看守接近风门洞时,都有责任发出警报。各仓报警的方式不尽一样,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绝对不能让看守发现你在向同仓的囚犯示警。因为当你发现看守时,他也一定看见了你。如果你的动作、眼神和声音被查仓的看守认为有报信的嫌疑,那么,你就惨了。
16仓的警报——最先发现看守的人必须全身不动而从唇齿间发出的一声长嘘。
“咝——”声刚落,风门口便出现了一张长满青春豆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警惕地在仓内扫视了两遍,没发现任何人有违规的嫌疑,才发出一声:“都给咱老实点!”
从风门洞里窥见武装管理的身影已蹑足移近了13仓,16仓里面凝固的空气才松弛下来。中学生别有用心地自言自语:“武装管理,河南的陈班长。”
看守所内分行政管理和武装管理,所属系统不同,职责各异。行政管理就是看守所长以下的警察,基本工作内容就是刘所长讲的“保管员”,负责照单收发及里面的日常生活还有对违反监规者的教育惩戒。那年头儿还没有武警,穿军装带枪的战士是现役军人。他们被称为武装管理。武装管理任务很明确,不让人犯们逃跑。照规章,他们不能过问人犯们的案情,也不负责人犯们的教育和惩罚。正常情况下,他们连各仓室的钥匙都不能掌握。但那年头儿不正常,有行政管理经常利用这些精力过剩的青年来修炼违规的家伙。这个头一开,年青力壮的小青年或出自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或纯粹为了寻求剌激取乐,就常常主动地来寻找一些违反监规者进行教育惩戒。与行政管理们还有一点不同的是,那些带枪的青年来自五湖四海,3年服役期满又将各自回到来的地方,因此就和当地的派别斗争没有关系,也分不清谁谁是参加的什么组织。那年头,人们受到的教育是“对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象严冬般寒冷。”他们只知道这里面关押的都是阶级敌人,被打入了另册的阶级敌人就不是人。因此修炼起来也就一视同仁亳不留情,绝不象本地的行政管理那样区别对待。
一见是陈班长当值,高洁双眼发亮。这是他期待的最隹时间和最隹人选。
周未这段时间,行政管理都回家去了。即使武装管理修炼某个与行政管理有关系的人,他也无法干涉。还有,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这位来自豫西山区的陈斑长是位阶级斗争观念最坚决的贫农子弟。由于他没啥文化,讲不出多少大道理去触及灵魂,就爱以拳脚来触及囚犯们的皮肉。
高洁立即向坐在里面墙角的独眼点头示意。
独眼咧嘴一笑,慢吞吞地从铺位上站了起来,然后若无其事地晃着双肩朝仓门边踱去。
朱必成正闭着双眼怨天尤人心潮澎湃之际,他的小腿上突然被狠狠地踩了一脚。
“哎哟,我日你妈!”朱必成双目好似要喷出火来,但他深知晚上在监内闹事的后果,只好压低了嗓子骂:“瞎了你那一支狗眼。”
独眼没还嘴,他嘿嘿地笑着,猛地又给朱必成当胸一脚。16仓的红毛犯人万万没想到,独眼会无缘无故地向他挑衅。朱必成一时间竟愣住了。独眼趁机又是一个耳光,扇出了一声脆响。朱必成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他一声怒吼,抱住独眼的双腿使劲一拱,将对方掀倒,两人在仓板上扭打起来。
高洁立即弹身而起,将头伸出风门兴奋地大叫:“报告管理员,16仓有人违犯监规,打架!”
高洁的叫声响彻了如墓地般静谧的看守所,“咚咚”的脚步声迅速从天井对面响了过来。
按照看守所内一般打架斗殴的常规,只要一发现管理员出现,双方便立即住手,装成没事人一样。朱必成听高洁一叫便放开了手,不料独眼却死缠蛮打,趁机又给了他几拳。
“住手,我操你娘!滚过来,下来!”陈班长出现在风门口。
独眼和朱必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跨下仓板立正站到门后。
“为啥打架?”
“报告武装管理,他无缘无故地动手打我。”朱必成抢先回答。
“报告,我过来屙尿,他突然伸脚绊了我一跤,我才还的手。”
陈班长已作了两年多的武装看守,他清楚地知道,在这些看守所的老犯口中绝对问不清是非曲直,也找不出客观公正的旁证人。在有被无限期拘留的老犯那种年代,这里面真是一所大学校。提审的人说过一句挺深刻的评语:一支笤帚在仓里搁上半年,也会开口撒谎。凡是有经验的管理员都不会费神在这类事情上去弄清谁对谁错,因为他确信弄不清楚。打架是他亲眼目睹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家伙都严重地违犯了监规。
但陈班长今天的心情特别好。我推测他刚收到了未婚妻的来信,所以他不想动手,才破例地试图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去触及阶级敌人的灵魂。
陈班长没立即将两个严重违犯监规的家伙弄出去,这情况大大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你俩个家伙是犯的什么罪?”陈班长心平气和问。
这次朱必成不抢答了。独眼抬起头,说是执行命令枪毙了一个人。
“你的家庭出身?捕前你在干什么?杀的什么人?”那年头,家庭出身是任何询问调查的第一个问题。
“工人,家庭出身贫民。我杀的那家伙是个现行反革命杀人犯,他龟儿用剌刀挑开了我们一个广播员的肚子,她肚子里头的娃儿都长出鸡鸡了……”
陈班长被独眼的回答弄得几乎忍俊不禁,但他知道面对如此严肃的问题不能笑,他咬紧下唇,挥手止住了独眼。他花了好大的功夫又才调整出庄重的表情,问朱必成:“你呢?”
“报告,我是个技术员,家庭出身职员,武斗时杀了一个人。”
“报告,他欺谝武装管理。”高洁一步窜到两人身后的仓板上,趁陈班长还来不及叫他滚开,便躬下腰对着风门连珠炮般抢着说,他杀的是个志愿军一等功臣,抗美援朝时在上甘领被打瞎了双眼的残废军人,叫李卫国。
“呵——原来你就是杀害李卫国的凶手!”年青战士都无限敬佩部队里的前辈英雄,此时他突然发现杀害前辈英雄的家伙竟敢在自己当班时严重违犯监规,就禁不住浑身血液沸腾。他怒吼着将朱必成和独眼弄了出去。
铁栅门外,一阵阵惨嚎和捶击声撕裂了死寂的监狱之夜。
高洁惬意地摊坐在朱必成那张平时不容任何人窃据的土沙发上,他眯着眼抖动着右腿,好象在欣赏优美的乐曲似的聆听着外面一声声惨叫。后来,他竟忍不住用左手掌掩住半边脸,吃吃地轻笑起来。
童便也珍贵
约半小时后。独眼被架回仓来。朱必成则是被4个人抓住手脚抬进来的。
同犯们立即围了上去。独眼被大家关怀的手摆弄得皱眉咬牙咝咝地吸气,但他仍然挣扎着说:“没关系没关系,老子没得啥子;他淫贼象被按在杀凳上的猪一样嚎,你们听到没有?老子咬着牙一声都没叫。”
中学生说:“你比他挨得松活些吧?”
独眼却说,他俩一出去问都没问,那些正在打扑克的武装管理都围上来过瘾了,枪托拳脚一阵乱打,直到他们都打累了才收手。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年的12月,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北京发出了一条最高指示:
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根据这一条最高指示,后来又形成了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制止各监所对犯人的虐待、殴打,并容许犯人控诉。
但直到1974年春,各地的监所才将这份文件传达给每个在押人员。我们也是那时才听到这条最高指示的。从传达这份文件之后,监狱管理员对在押人员的体罚和虐待,才受到一定的限制。
我后来看到了这份文件的来源,倍感亲切。特抄录如下:
毛泽东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示(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注:刘建章,原铁道部副部长。)
周恩来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三点批示:一、将刘建章保外送医院就医,并通知其家属前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年内再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34-335页)
这故事发生时,还没有那条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连首善之地的监狱,对被关押的高级干部都实行了被领袖称为“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何况我们这偏远的小地方老百姓。
朱必成浑身灰土满嘴血沫,除了老校长过来帮他脱掉外面的衣裤,将他安顿在铺位上,再没人搭理他。他疼得在铺位上不停地扭动呻呤,根本顾不上跟这种时候还在逞强的独眼斗嘴。
大家七手八脚地擦净了独眼的身体,当过医生的双皮老虎指着他腰背上一团团紫红色的瘀血块说,那是用枪管捅的,如不及时治疗,怕会留下内伤。
但仓内除了伤湿膏和清凉油外,没有任何可供外用的药品。
众人唏嘘间,洪扒手低声给高洁说了几句什么。高洁便扭头盯着年纪最小的中学生,一本正经地问:“你跟女同学云雨过没有?”
“什么云雨?”虽然已经年近20,但初中刚念完便碰上停课闹革命的中学生不解地问。
“我知道、我知道,‘云雨一番’,吴瞎子说过,”独眼竟忍着伤痛抬起头来兴致盎然地解释,“就是跟女人搞那话儿。”
中学生顿时红了脸:“我跟你妈云雨过!”
经过一番严肃的解释和盘诘,然后就认定中学生还是个童子,他的尿也算是童便。据洪扒手他们那一行历代传下来的经验,童便是疗伤圣药,没遗过精的童男屙出来的才是正品,疗效最好。中学生满脸欠意地说,可惜我遗过精了。大家都说,算是准童便吧,将就将就,总比没有的好。
高洁立即把洪扒手盛开水的盅子抓了过来。受惯了杀人犯欺侮的洪扒手不敢发出一声异议,还在一旁进行了认真的指导。高洁依照洪扒手之嘱,接了小半盅子中学生的尿,最初那一股和后面的尿尾子都不入药。
高洁亲手将盅子端到独眼嘴边,温情地劝他快点趁热喝下去。
独眼被众人扶起来,就着高洁的手咕嘟咕嘟灌下去一大半。他摇摇头,用手背擦了擦嘴:“够了够了,他妈的一股燥味,怪不好喝。”
众人便象哄小孩一样,说了些良药苦口之类的话,劝独眼将剩下的喝完。
独眼手一挥,竟自躺了下去,坚决不肯喝了。
“剩下的给我嘛,我原来就有内伤……”朱必成有气无力地乞求。
高洁微笑着端起盅子向朱必成走去。当朱必成费力地撑起身子满脸感激地伸出颤抖的手来时,高洁却古怪地对他笑了笑,将剩下的准童便仔细地倒进了夜壶。
虽然缺医少药,但独眼天天都有准童便服用,吃喝拉撒都受到了精心的照料。我还应独眼的要求,重讲了一遍他最爱听的老派武侠小说《鹤惊昆仑》以示慰劳。
当时的我根本没有想到,将来还会有“平反”、补发工资的结局。为了在出监后有混饭吃的技能,就天天在北山公园里面练说评书的功夫。在仓内,最受尊重的人就是会讲故事的人。因为能替因等待那不知何年何月才到的“运动后期”,而整日无所事事的同犯们打发那难捱的光阴,真是功莫大焉。独眼平时直把我当先人老辈子一样侍奉着。绝不会说奉承话的独眼经常由衷地赞叹,“谢君比说了一辈子书的吴瞎子还凶!不光会说古书,还会说洋书。”
直到星期一,胡管理才知道朱必成前天晚上被修炼的事。他知道了也无可柰何。既然谁都可以对人犯任意体罚,你作一个行政管理的就不可能去指责武装管理惩罚确实违犯了监规的家伙。
趁朱必成被胡管理弄出去治伤的机会,老校长在仓里提出不能再这样干了,再整下去怕要出人命!高洁却恶狠狠地说:“我们这是以斗争求和平!不把猪八戒弄服降,仓里就得不到安静!不要因为猪八戒没整过你就来充好好先生。”报复心正切的王茂军等人马上态度激烈地响应支持。我们几个心有不忍之人也只好噤声。
十 监狱里的老革命
1970年,由于那位永远健康的副统帅闹出个惊天动地的“九。一三”事件,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全国的看守所内都进行了非常管理,措施之一便是停止每天的放风。除了极少数参加劳动的人犯外,其他人都整日被闷在幽暗的牢房里,没机会呼吸新鲜空气也无法活动筋骨。
在万县市看守所,上面一发出停止放风的命令,当即便雷厉风行地实施了。但在非常时期过后,上面却忘了再发明令恢复。加上管理人员觉得,不放风还少了一项麻烦的日常工作。因此在万县市看守所,这停止放风的措施便一直执行了近两年之久。
当时,我们天天都能从风门洞里看到一位身材瘦小腰背微佝的老年人犯,在那非常时期却享受着每天放风的特殊待遇。
每天上午,他都会被看守按时放出4仓来。老人一出来便沿着天井的边缘似竞走运动员般迈步急走,不东张西望也不减速。他连续走上将近1个小时,直到浑身大汗后,才坐在石阶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走那么长时间,这短发雪白的老人就主动报告进仓。
望着这瘦弱的老人天天不声不响地在天井里急走的样子,我不由自主地总会想到文革前那风靡全国的《红岩》老革命华子良。只不过他没有华子良装出来的疯痴神态而显得平静坚毅。
有老犯告诉我,那是个老地下党,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他每天走的步数,便是从看守所走回家中的距离。赵唯在想象中回到家中与老妻坐一会儿,又走回看守所。单边8公里,一步不多一步不少。他被农科所多次押回去批斗时计量好了的。
赵唯当年在下川东真称得上赫赫有名。他是万县专区云阳县人,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他在上海读大学时,于1931年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了地下工作的生涯。第二年,赵唯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被组织上派回云阳,建立了云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将共产主义的火种带进了大巴山。第二年他父亲死后,赵唯继承了全部财产。地下党的力量壮大起来后,赵唯于1935年1月19日,在自家的打谷场上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将赵家祖辈积累下来的田地财物全分给了农民。然后组织了著名的云阳武装暴动,拉起队伍成立了游击队,任司令员,攻占过云阳县城。后来,这支游击队便一直活跃在大巴山和七曜山区,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期轰轰烈烈艰苦卓绝的战斗。
本地年老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政府多次悬赏上千银元买“匪首双枪赵唯”的首级。
那部轰动一时的小说《红岩》中的许多英烈,均是川东游击纵队赵司令的战友和下级。如全国闻名的英烈彭咏梧(彭松涛),就是这支游击纵队的政委。在大巴山下牺牲后,他的头颅被敌人砍下,悬挂在奉节县竹园坪寨楼上示众,他的墓如今还在奉节县城供人凭吊。江竹筠(江姐)当时是中共地下党下川东联络员,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的职员。她于1948年6月在万县被捕后,即解送重庆,演译出渣滓洞内的那些动人的故事。
赵唯一直领导着游击队转战在大巴山和七曜山区。1949年12月,云阳解放后,赵唯被任命为云阳县长。1954年出任万县专区副专员。
后来,当赵唯调到我所在的16仓后,我问过他《红岩》这部小说为什么将发生在川东的史实移到了川北,彭咏梧(彭松涛)的司令员也变成了位老太婆?赵唯告诉我,作者是川东地下党的同志,自然清楚这段史实,在创作过程中也来找他搜集过材料。但当时他已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贬在农科所作一个不管事的副所长。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为了避免“替右派分子歌功颂德”,才作了些技术处理。赵唯说:小说嘛,可以那么写,但作为党史,川东地下党的历史是不可抹煞的。
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信口雌黄,说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在这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到处都抓“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许多老革命们便失去了自由。
我们仓里有一个诈骗犯就嘲弄过赵唯:你家是云阳县的大地主,你又是那么早的大学生,假若你规规矩矩地读书留学,作个专家教授,一辈子自由自在该过得多舒坦?你却不会享福自找苦吃,先共了自已家的产,然后提着脑袋干了几十年革命,结果却把自己革到共产党的监狱里来了。
赵唯正色回答: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过好日子,是为了大多数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虽然我现在被关进来了,这只不过是错误路线的影响,我们党历来就是在不断地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前进的……
出于这种信念,他一有机会便叮嘱看守所里的“三老会”们:为了出去以后有精力继续为党工作,我们在这里更要保持信念加强锻炼。
赵唯1968年被抓进看守所。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影响,所以当局曾主动给与他优待:住单间、吃大米外加油酥豆办,还有单独放风和一份《人民日报》。但赵唯在看守所内自律很严,对当局的优待只接受了单独放风和《人民日报》,他同其他人犯们一样,挤在又脏又臭的大仓里。由于在山上打游击时长期饱一饨饿一饨,赵唯的肠胃一直不好,每天早上那2两大米他是全吃了,但中午和晚上那两罐包谷,他就只能将上面的稀羹喝掉,而将下面的大半硬包谷米给与那位照顾他日常生活的人吃。大家都劝他接受当局的优待,吃3饨大米就别吃包谷了。可赵唯却固执地不答应,他说:既然现在成了囚犯,便不能在吃的问题上搞特殊化,更不能去住单间脱离群众。
赵唯毕竟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常对我们讲一些他自己的革命经历。
赵唯是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的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叫林祖涵。林祖涵就是林伯渠。他是早年的同盟会员,1921年1月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林伯渠在长征时便是著名的五老之一,到延安后作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时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赵唯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就在林伯渠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组织上又要求赵唯辍学,将全部精力投入地下工作。赵唯二话没讲,便照组织的安排退了学,向家里要了一笔钱,在上海开了一家川菜馆,作地下党的联络站。
赵唯整天西服革履厮混于上海滩,结织了许多在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当他讲到这段经历时不由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了几句题外话:那时候,凡在社会上有点地位的人进馆子吃东西,结帐时该付80块的必给100块,多付钱才显得有面子;现在少数有地位的人进馆子,都要少付钱甚至不付钱,才显得有面子……不过短短几十年,人的价值观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64岁的赵唯在万县市看守所内被拘押了6年多后,于1976年4月6日被判刑20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赵唯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纠正。恢复了党籍,享受离休待遇,长期居住成都。
1993年,赵唯以85岁高龄因病逝世。
十一 祥和的16仓
转眼间,天就凉了。
不到半个月,体质强健的独眼又出现在倒马桶的行列中了。他在管理员的口令声中,照旧端着沉甸甸的紫金钵向厕所飞奔。朱必成虽然在两天后便得到了治疗,还带了一大包内服外贴的药回仓,却仍然躺了一个多月,才有体力报告胡管理员,将挨打时弄脏的衣服拿出去洗。
就在他刚洗过衣服的那个星期六晚上,王茂军又无缘无故地向他挑衅。两人因严重违犯监规,理所当然地又被值班的武装管理弄出去修炼了一顿。
这次,王茂军和朱必成都是被抬进仓的。回仓后的待遇还是同上次一样,朱必成既没受到多少照料,也未喝到准童便。
有一天半夜,朱必成在迷迷糊糊之中被伤痛弄得醒了过来。他睁开眼,发现高洁正光着膀子坐在被窝内捉虱子。本来仓内人人都很注重卫生,常年不动也不出汗,便不容易生出那种小虫子。但高洁缺少换洗衣服,他的被子又烂得只是破絮一团,根本不敢拆洗,自然就生了虱子。生虱子本不可怕,但可怕的是朱必成却发现他这杀人犯捉到那些吸血的小虫后竟没有立毙指下,而是将它们向其他人的铺位上空投。本派的战友和他平时最尊重的老校长还有我均未能幸免,只不过朱必成的铺位上被多空投了几次。
当时,朱必成气愤地动了一下,本想当场揭露高洁。但转眼间,他却合上了眼帘。他感觉到高洁那双发红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自己,高洁的眼光似两柄冰凉锋利的剑。朱必成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
这一晚,朱必成再也没有睡着。
彻夜不眠,朱必成想明白了许多事儿。
第二天一早,朱必成从铺位上挣扎着坐起,谦恭地对全仓抱拳行注目礼一周,然后将目光停在高洁脸上,诚恳地说:“以前,我有许多事儿对不起大家,今天给各位赔礼了。请大家相信,我不会再报复谁,我也不会再干那些损人不利已的蠢事了。”
老校长立即利用朱必成主动道谦给大家带来的感动,不待高洁插嘴,马上站起身来:“这些年,你们都曾经狂热地斗来斗去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原来你们都以为目的很明确——就为争一个理念上的正确与错误!可现在,你们不是都越来越糊涂了么?真理到底在那一边?那位能说明白?现在能看清楚的,只是许多人被斗死斗残,许多人被斗得家破人亡,自己也被斗了进来;斗、斗、斗,为了什么原则、路线?斗的人谁得到了好处,给人民又带来了什么好处?再这样斗下去,说不定就在监内也会自己斗死几个……本来,大家都是好好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为什么会落到现在这步田地,难道自己就不会动脑筋好好想想……”
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说得那些好勇斗狠之徒都认真地静下心来。监狱本来就是个使人反思的地方。人犯们不同的经历和相同的现状,也强迫大家结合自己的情况,或多或少地进行过一些反思。老校长抓住了这个适当的时机,给了他们所需要的一阵当头棒喝,使得那些平时不习惯进行思索的大脑开始了认真的思索。
只要开始认真思索,许多复杂迷乱的事都变得简单明了。
就这样,老校长在恰当的时机,结束了高洁发动的这埸车轮战。
自此以后,16仓一派祥和安宁。不再害怕有人打小报告了,长期关押得不到处理的囚犯们为了消磨时间,便大肆违犯监规。被禁锢的人们焕发出令人吃惊的创造力,用牙膏皮作笔,用清凉油的盒子做成刀片,制造出了竹针、象棋、扑克等等严重违禁的工具和娱乐用品。我们还安排了轮值的哨兵,专事监视风门外的动静。仓内就放心大胆地开展各项活动:写笔记、讲故事、打牌、下棋、搞缝纫……
在“十年浩劫”的特殊时代,那些被“拘留无限期”地关押在黑牢里的人们,在狭窄的牢房里是怎样渡过那漫长的岁月,正常的大脑无论如何也是猜想不到的。我也准备将那些匪益所思的生活方式,在下一部书中详细讲述。
那年头,人人事事都讲斗争的紧张局面在16仓内提前结束了,闭门思过的枯燥日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大家都说,这日子好过多了。
高洁又背了一句语录:“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高洁如果是生在春秋战国那一类时代,肯定是个人物!”我曾当众评议。
但他终究没成个“人物”。他被那块条石砸死时,还不到40岁。
当高洁刑满释放回到铜鼓山后,历史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洁的心智有了用武之地。没几年,他就成了铜鼓山先富起来的农民之一。农民富了便要修祖坟建新房。高洁也未能免俗,他修了祖坟再建房。
备好材料后。妻说,这等大事定要请位道士来,选择黄道吉日破土动工。高洁不信这一套。他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但他在妻固执的坚持下终究还是让了步。高洁处处都体谅跟着他受够了惊吓的妻,不愿再给她增加心理负担。
终于请道士选好动土的日子,作好了一切准备。高洁请来了工匠,吉日吉时放鞭炮破土动工。
就在动工的第4天晚上收工时,屋基都快下好了,众人才发现基脚还差一块条石。
高洁还是正点让妻子安排工匠们喝酒吃饭。
饭后人们各自散去休息,高洁独自拿起工具出了门。
铜鼓山的男劳力个个都会干石工活。高洁虽然已进入小康,但本质上还是个农民。他认为又叫人来采一块石头不好计方算帐。为了节省那几块钱,高洁带着微熏的酒意,独自去后边岩上采所需的最后一块条石。
那天晚上,秋月当空,月辉黯弱地瑟瑟摇动,似笼罩着团团的寒气。秋云在夜空中弥漫四散,被晚风吹得如丝如缕,渐渐淡远。
高洁被自己撬下来的那块条石压在了胸部。他口鼻喷血,当场身亡。
高洁的妻子后来又请高人看过,说动土那天绝非黄道吉日,却恰恰犯了“鲁班煞”,故而高洁要死于非命。高人说那“道士”是假冒伪劣,算错了闰年闰月。
高洁的新屋最终还是建成了。
高洁那忠实的老妻在新屋旁为他修了一座新坟。
若不是我在这儿将高洁写出来,这芸芸众生来去匆匆的世界上,根本没多少人知道,在那高高的山村里,曾经走出过这样一位农民。
结束语
消逝最快的莫过于岁月。
好似转眼之间,我已两鬓染霜。突然就觉得,生命之书所剩下的页数已不多了。
我曾亲历过一个特殊的时代。由于种种原因,我青少年时的经历,即使在同时代人之中,也算得上是丰富而多彩。
过了知命之年,在单位里改任调研员,空闲时间便突然多了起来。读过几本佛经,也略懂得了心平气和。那些年青时的坎坎坷坷,都变成了“亲切”的回忆。
我便经常去追寻过去的时光,久久与其深入地攀谈。作为一个经历过那一切的过来人,我以为这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好象有位外国人说过:每个人的历史都应当是一部《圣经》。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是史学家。
历史是由无数个人的经历汇合而成的,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草民。
草民们曲曲折折走过的路,能实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过去,并帮助人们认识现在,预测未来。
我向赵晓玲老师致谢。若没有她的鼓动与帮助,可能我至今还没有将这些往事变成文字的计划。
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或许是一件有益的事。
(全文完)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