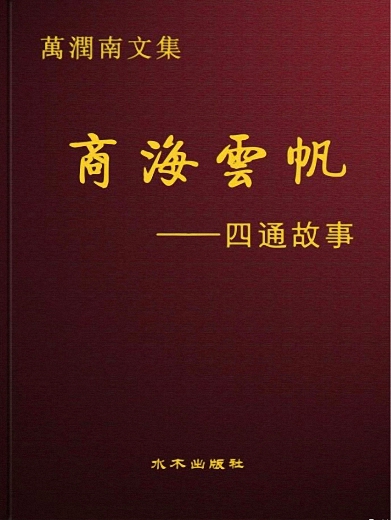第十章 四通文化
(68)对话会
《孙子兵法》上说:“上下同欲者胜”。“同欲”又可以分为同心、同德、同利、同乐等几个层次。当年我们在四通,在这几个方面都努力了。首先,是在制度、时间上作了安排:每周一次的经理办公会,是让公司的管理层“劲往一处使”;每个月一次与员工的对话会,是让全公司上下“心往一处想”。

这样的对话会,一般先由我做主题讲话,然后现场回答大家用小纸条提出的各种问题。每逢这样的时刻,四通的员工总是兴致勃勃、非常有参与感。直到现在,许多人对当年的“对话会”,依然记忆犹新,印象深刻,津津乐道。
二十多年后,集团办的孙英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当时我们都特别喜欢上班,每天一大早,早早准备好了,盼著来接我们的班车……四通人还喜欢开会,特别是大会,全体职工对话会,甚至可以说是有瘾。大家都不愿意漏会,生怕听不到万总讲话和回答问题,那时候四通就是我们的家。”
有一个四通的小女生,1989年后,离开四通自己创业,做得非常成功。后来她在深圳遇到了李玉,说起自己当年参加“对话会”的感受。说那是她学习经商办企业的启蒙学校。她常常会带自己的先生去旁听对话会,让他也感受一下四通的企业文化。
记得负责OA批发部的,是个个才二十岁的年轻人,叫唐地,干干瘦瘦的,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其曾叔祖是民国初年的国务总理唐绍仪。他回忆说:“万总的讲话能让人血液流速加快,深深打动着我们。他讲的全是新观念,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壮丽的前景。四通的抱负,最关键的不单是一个公司的愿景,而是影响到中国的改革进程的伟大事业。我觉得从那时起的四通就不是一个单纯关心自己生意赚多少钱,能有多少业务的普通公司。在那个年代,我们为此深感自豪,尤其,是我们四通的打字机掀起了中国汉字输入的革命、办公设备的革命,咱亲身体会了,参与了!”
还记得有一位小青年,在一次公司培训结束后的演讲会上,仰起头,闭上眼,把手一扬,模仿契科夫的语言:“在四通的每一天,都忙得筋疲力尽,但内心却如此充实。我想对公司说:如果你今天就需要我的生命,那就拿去吧!”口气有点夸张,但表达的心情,是真诚的。
是啊,一家公司,如果每一个员工都愿意为之卖命,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正是许许多多像唐地这样的年轻人,这些四通棋盘上的过河小卒,一个个都成了驰聘商场的干将,成就了四通的辉煌。
“对话会”多次在北大的电教馆举行,还借用过中科院发育生物所的礼堂、友谊宾馆和中国剧院的剧场。
这样的对话会,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而是生动活泼,有问有答,火花四溅,气氛热烈的互动过程。记忆中,有许多精彩的片段。
到1987年上半年,公司人员急剧增加,我们准备租用友谊宾馆北配楼三层整整一层开阔的大厅,作为总部办公室。对话会上,有员工提出了质疑:“万总,听说公司要花40万元租用豪华的友谊宾馆办公,是不是太奢侈了?”
我说:“不奢侈。如果我们一分钱也不挣,那么租一间茅草房也是奢侈。去年我们销售了1.1亿元,用营业额的千分之四来租一个办公的地方,应该说是非常节俭了。公司大了,人多了,公司需要有与现有规模相称的对外形象,人员需要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这样我们才能为顾客提供第一流的服务。”
一个企业,能花多少钱,能分多少钱,要根据企业的营业收入。四通对所有的专业公司和经营实体,都实行目标管理,具体来说,叫“五定二挂钩”,即定销售额、定利润、定资金、定人员、定库存,运行费用与销售额挂钩,分配与利润挂钩。一开始,我们规定每增长二十五万元销售额,公司才可以招募一位新人。这个标准后来不断加码,人均销售后来增加到五十万元。到1988年,人均销售提高到一百万元,当年我们的销售额突破了十个亿,总部员工的人数是960人。
公司的发展没有一天不存在问题,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我们应该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我有责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让大家了解公司正在做些什么;也要让员工关心的每一个问题,都得到公司有关领导的解答。这是公司员工对公司领导每月一次的“月考”。
按惯例,大家把自己关心的各种问题,写在小纸条上递上来要我作答。其中有公司的发展目标、产品开发、销售服务、宏观环境、公共关系……我都一一作答。这种直接面对全体员工的对话会,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敢开的。这跟口才没关系,而是要求公司的头头必须襟怀坦白,立身正派。因为员工是匿名写字条,他们什么问题都敢问,你必须当场作答,如果心里有鬼,绝对经受不住这种一月一次的开放式“面试”。
曾经有一张纸条上问:“万老师:你们一家,除了你,还有万老(指我父亲)、储老师、李老师都在我们公司,是否……”
我念完最后两个字,然后说:“下面是省略号”。会场里传来一阵窃窃私笑。
我说:“这位同仁是想问:你们姓万的是否在公司搞家天下?”全场又是一片笑声。
之后我回答:你一定是1985年以后来的新员工,因为经历过那一年“清理整顿”的老四通,没有一个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我简略地回顾了当年风云突变、泰山压顶,公司几乎面临灭顶之灾,万老眼睛充血,储忠临危上阵的经过。我说:“那时候,我可以选择留在中科院,继续在美国当访问学者;储忠可以继续当新长征突击手和第三梯队,准备在上海工商行接班。但是,我们选择扔掉铁饭碗,破釜沈舟,到四通来和大家共命运。这是我们姓万的一家为人仗义。当年GCD里有一个徐海东,全家66口参加革命,连毛说起来都为之动容,因为那时候革命尚未成功,他们都是提着自己的脑袋来加入队伍的。我们老万一家投身四通的艰难创业,没有那么了不起。现在,公司的前途依然坎坷,也正是用人之际,你们谁家有老爷子、兄弟姐妹、七大叔八大姨,能干的、有胆的、敢砸铁饭碗的,欢迎大家推荐到四通来。古人说: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惟贤是用。我们的气量,不能连古人都不如。”
在我离开四通以后,继任者按惯例开过一两次这样的对话会,员工的问题越来越尖锐,便再也不敢继续面对。从此,对话会走入四通的历史,公司“上下”再也不能“同欲”了,按孙子兵法,必败无疑。
在1987年9月的一次对话会上,有人问:“万老师,你总说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的IBM,那你能告诉我们,现在公司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吗?”
我回答:今年我们的销售目标是保2争3,大约是2-3亿元人民币。我们离目标还有多远?提供给大家一个数据:IBM去年的营业额是500亿美元,相当于200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我们大约是IBM的千分之一。如果说我们是在爬坡,目标是珠穆朗玛峰,峰高8882米,我们现在不过爬了一个8米高的小土坡。如果说我们进行的是两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刚刚走了二十五里地,你说我们离目的地有多远?如果按当年长征路线来讲,我们还刚上路,迂回曲折,艰难险阻,还都在后面呢!
前几天,IBM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成员有IBM的副总裁、业务开发部的主管以及负责中国和香港业务的地区总裁,一行七人,到四通来参观访问。
对我们“要成为中国IBM”的提法,他们非常有兴趣。我说:我们要成为中国的IBM,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四通。我还提到,有人说,企业成长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问号(?);第二个阶段是问号加惊叹号(?!);第三个阶段是惊叹号(!)。四通经历了第一个阶段,刚刚步入第二个阶段。一开始,从上到下,对我们是普遍的怀疑;现在,开始有人说我们还不错,但依然带着大大的问号。我希望四通能够尽快步入第三个阶段。
IBM的副总裁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讲,不存在第三阶段,也就是说,不会有一个企业没有问题及人们对它没有看法。他说IBM这么多年了,一直在世界五百强里名列前茅,但是人们对IBM依然有许多问号。在七十年代,还有去年(1986年),有一段时间议论纷纷,说IBM不行了,没有活力了,不能再发展了,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等等。有人告他们的状,他们打了一个世界上历时最久的官司,打了十几年。有人根据反垄断法起诉他们。这期间IBM的董事长什么事情也不做,专门处理和政府打官司。他说今天的IBM依然处在第二阶段。对一个企业来说,不可能只有一片叫好声,只剩下一个惊叹号。
我听了之后,当时小小的出了一身冷汗,脑袋清醒了许多。是啊,直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我们带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甚至当面称我们是“中关村一条街上的骗子”。许多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你就是写一千篇《四通故事》,也改变不了这些人的偏见。
惊叹号随风飘去,大问号与世长存,阿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