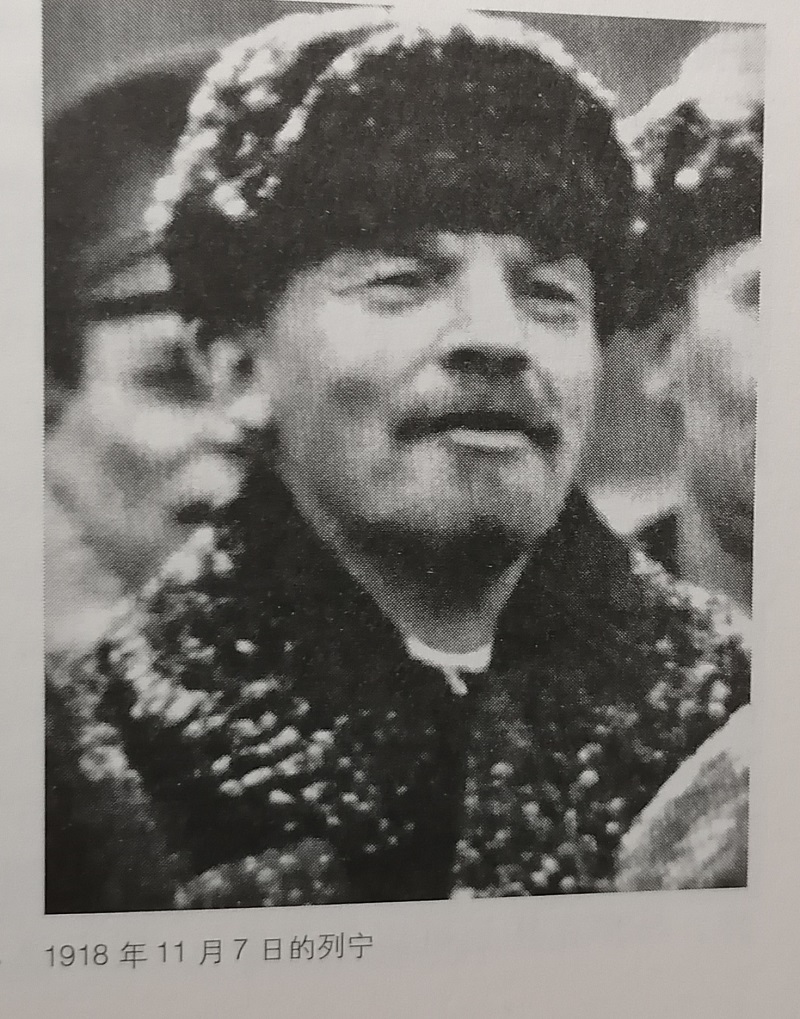考茨基与列宁之争(三)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考茨基与列宁争论的焦点。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考茨基的观点:
考茨基一开始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经典语录: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CP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考茨基接着指出: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按字义来讲,专政就是取消民主。但是,当然按字义来讲,专政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个人独裁。个人独裁和专制之间的不同在于:个人独裁不被视为经常的国家制度,而被视为是暂时的应急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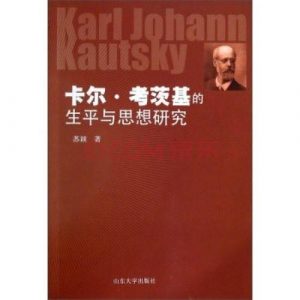 “ ‘无产阶级阶级专政’ 这个词一一也就是说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的专政一一就已经排除了这一点:即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是指这个词在字义上的意义而言的。
“ ‘无产阶级阶级专政’ 这个词一一也就是说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的专政一一就已经排除了这一点:即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是指这个词在字义上的意义而言的。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一种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现的状态。马克思还认为,英国和美国可以和平地,也即用民主的方式实现过渡,单这一点就可以表明,他在这里所指的不是政体。”
“……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这个专政并不同时就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这个政权的权力应该服从普选制。”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 :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普遍选举权……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
“马克思在这本书里一再谈到全体人民的普遍选举权,而不谈一个特殊的特权阶级的选举权。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状态。
“因此,那些赞成专政反对民主的人是不能依据马克思的话的。……
考茨基指出,马克思认为 “无产阶级专政” 不是一种作为管理形式的政体,而是 “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任何地方都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状态”。在考茨基看来,马克思认为,专政是一种暂时的需要,而不是革命的目的;是一种与夺取政权直接有关的暂时需要,而不是一种合乎愿望的管理形式。在英美这些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可以通过民主方式来实现,专政是不需要的。
列宁对考茨基上述论断极为恼火,使用比较极端的言论攻击对方: “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然这样骇人听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 “要把考茨基所有的谬论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事实真是像列宁所攻击的那样,考茨基的 “每句话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吗?让我们把考茨基接下来的论述展示给大家,请大家斟酌一下,公正地作出评判吧。
考茨基接着指出: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防止把这种作为状态的专政同那种作为政体的专政两者混淆起来。只有后者的倾向才是我们队伍中的争论的问题。作为政体的专政,同剝夺反对派权利的含义相同。反对派被剝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在于: 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
这个问题问得好!既然资本主义的国家并不剝夺反对派的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做不到呢?列宁不是大言不惭地说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 吗?具体的表现又在哪里呢?
考茨基接着又指出: “在这方面,首先必须指出,当我们把专政作为政体来谈论时,我们就不能谈论一个阶级的专政。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个阶级只能实行统治,不能实行治理。如果有人不想把专政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统治状态,而理解为一种特定的政体,那么他就只能说个人的专政或一个组织的专政,也就是说,不能说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只能说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但是一旦无产阶级本身分成不同的政党,那问题就立即复杂化起来。于是,这些政党中间的一个政党的专政就决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专政。如果社会主义诸政党由于它们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态度不同而分裂,如果比方说一个政党通过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取得政权的话,那么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于是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变成无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且还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于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具备了十分奇特的形式。
“为什么无产阶级的统治应该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相容的形式呢?……
“人们也许倒可以推断,通常只有在无产阶级构成居民大多数或者至少受到大多数居民支持的地方,无产阶级才会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在其斗争中的武器,除了它的经济必要性之外,就是它的群众性。只有在无产阶级受到群众的,也即大多数居民的支持的地方,无产阶级才能战胜统治阶级的权力手段。……
“这一点也适用于巴黎公社。新的革命政权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有普遍选举权的公民投票。这次在最充分自由之下举行的投票的结果是:几乎巴黎各区都以强大的多数支持公社。65名革命者当选,而反对派只有21名当选,……65名革命者中间有法国各个社会主义派别的代表。虽然他们互相斗争得很剧烈,但是他们没有一派对其他派实行专政。
“一个在群众中扎根很深的政权,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有人用暴力行动来压制民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能永远避免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
“由此可见,作为废除民主的专政,只有在下列的非常情况下才能加以考虑:即如果各种有利条件的特殊巧合允许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尽管大多数居民不赞成或者坚决反对这个政党。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举行普选时出现了反对社会主义政府的结果,那么这个政府究竟是应该按照我们一向所要求于任何政府那样,服从人民的裁决,同时抱着坚定的意志要在民主的基础上继续为争取政权而斗争呢,还是应该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权地位而扼杀民主呢?
“一个专政在违反大多数人民意志的情况下靠什么来继续执政呢?”
考茨基以上这些论述对布尔什维克党来说十分切中要害!十月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虽然有二十多万人,但大都活动在一些大中城市,以产业工人为活动对象,远不能说是一个在群众中有深刻广泛影响的社会力量。所谓十月革命其实是一场政变,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成功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既然 “一个在群众中扎根很深的政权,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那么,一个在群众中扎根很浅的政权,就有千百个理由去损害民主。布尔什维克党人 “用暴力行动来压制民主的时候,这个政权就不能永远避免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
列宁1905年在他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文中也指出了民主主义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之间的区别。区别就在于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社会主义专政具有暂时的性质。而且列宁所依据的是马克思于1848年在《新莱茵报》上写的一句话:“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 “马克思的这些话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 列宁解释说:“它说明暂时性的革命政府应当以独裁的方式行事。”
看起来,列宁这些话同考茨基的话并不矛盾。考茨基在引证马克思的话时说,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种 “管理形式”,而是在夺取政权后的一种“暂时状态”。但是,在这里具体情况取决于对 “暂时性” 一词的解释。这个词意味着多长时间呢。几个月?几年?几十年?上百年?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都是暂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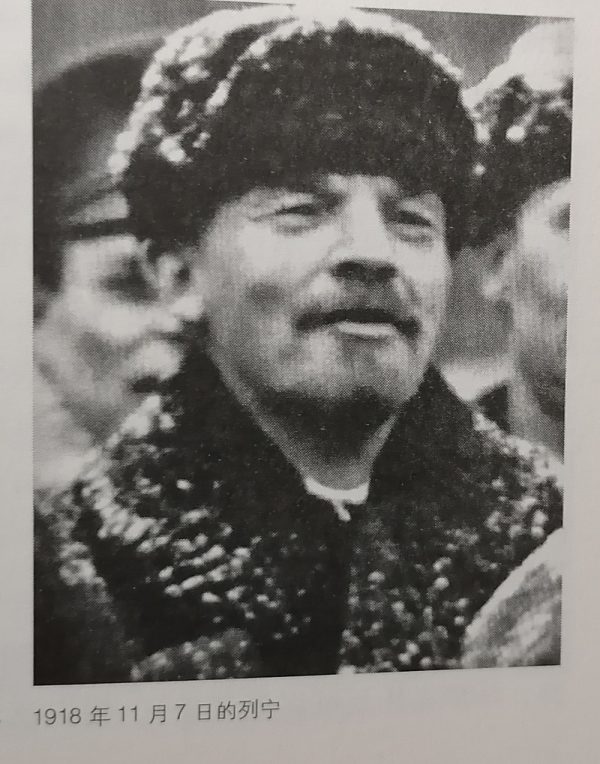 列宁在1919年11月7日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了这个 “暂时” 阶段的时间问题。他写道:“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是要一下子消灭阶级是办不到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灭的。” 列宁把阶级与专政紧紧地捆在一起,其用意是为实行长期专政找借口。
列宁在1919年11月7日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了这个 “暂时” 阶段的时间问题。他写道:“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是要一下子消灭阶级是办不到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灭的。” 列宁把阶级与专政紧紧地捆在一起,其用意是为实行长期专政找借口。
专政要求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这是要排斥自由的。列宁1905年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就写道:“人民生活中的大问题只有靠使用暴为才能解决。” 之后,他从未放弃这一原则,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写道:“考茨基本人已经堕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庸俗地说什么 ‘纯粹民主’ ……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考茨基对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概念的 ‘解释’ 把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化为乌有,他也就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叛徒伯恩斯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较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是铁板一块,一党独大,社会主义思潮、组织的多元化也属正常。而一个政党的专政必然导致独裁专制,而专政的对象当然是非我者诛,一些社会主义政党也在所难逃。兄弟阋墙,甚至自相残杀的惨状不可避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其回忆录《雾霭》中对此有所报道:
1918年初,对无政府主义者和最高纲领派实施了首次逮捕,他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的日子里和解散立宪会议期间的战友。4月11日夜间,肃反委员会和赤卫队的小分队在莫斯科实施了解除无政府主义派别武装的行动,行动过程中逮捕了四百多人。7月又开始了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迫害,这次迫害实际上是因该党对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及对当局的土地政策持激烈反对的立场所致。……
针对孟什维克的 “疯狂、嗜血而可耻” 的行动,是因为孟什维克在1919一1920年地方苏维埃选举中的一些局部成功而引发的。1920年的选举中,孟什维克夺得了莫斯科苏维埃中的46个席位、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苏维埃中的120个席位、克列缅丘格苏维埃中的78个席位,等等。下面这件事对于说明当时工人的情绪很有意义。1920年的选举中,彼得格勒一家工厂除了(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之外,还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列宁做候选人。结果在公开投票中,列宁得了8票,马尔托夫得了76票。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于是就惹得执政党领导人 “暴跳如雷”。
早在1919年2月,捷尔任斯基即指示各省肃反委员会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进行 “最严格的监视”,并从中雇佣卧底。这些措施经政治局形成文件,文件中说:“建议报刊加强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整治……监视所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查封《印刷工人之声报》和《工人国际报》。”
怎样的语言! “迫害”,“监视”,“查封”……
凡是与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活动有关的问题,定期在俄共(布)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1919年4月至12月,政治局就这些问题讨论了25次。对社会党人的典型判决是关入集中营 “直至内战结束为止”。官方的宣传千方百计地利用关于隔绝社会党人的临时性(直至 “劳动战胜资本为止”)的论点。然而全俄肃反委员会地方机关的通令中却强调说,肃清外部战线并不意味着同国内敌人斗争的结束,因为 “彻底肃清反革命活动只有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情况下才能想像”。原来如此:恐怖和集中营,一直要到世界革命胜利。
肃反工作者也为不经审判的惩罚奠定了基础。起初将这样的恣意妄为解释成 “革命的合理性”,后来便具有了正式政策的性质。1922年1月,捷尔任斯基的副手温什里希特在报告中写道:“对于反苏党派活动家,在一定的情况下必须在全共和国境内或者某些部分实施某种镇压,不必拥有针对他们的具体材料。”
在省肃反委员会的机要处中,特派员开始行动了,他们的使命是揭露社会党人,派密探打入他们的队伍。1921一1922年,已有十分之六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部门实施针对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行动。
1920年1月5日,俄共(布)中央作出如下决定:“一、根据去年的指示,建议在红军中工作的全体政治委员和CP党员向特别处告知一切可能对特别处工作有好处以及将为部门或个人所知晓的情况。” 从1921年起,所有重要机关和大学均开始成立 “促进委员会”,委员会完全由CP党员组成,并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别部八处的领导下工作。委员会任务是搜集关于官员和大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和敌对意图的情况。
1923年下半年,联共(布)中央秘密考试核查委员会将外交人民委员部、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驻外机构的原社会党成员全部清除干净。根据促进委员会的提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从此开始在驻外使团中工作,以便对于苏联职员进行 “內部监视”。这样的做法一直延续至今。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特征是唯我独尊,垄断思想,垄断组织,垄断权力,将一切异己排除于所处社会之外。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其所著《一杯苦酒》中用精辟的文字给布尔什维克作出这样的结论:
从历史的观点看,布尔什维主义是从肉体上消灭农民、贵族、商界、整个企业家阶层、僧侣、脑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癫狂系统;……是基于一切压迫形式的对人的剥削和对生态的疯狂破坏;是掩盖思维空虚的反人类的训条。
从哲学的观点看,是社会自恋范畴的思维方式和对任何论敌的剪除和排斥;它集教条主义之大成,是以狭隘需求对待真理的权宜的和最终的结果。
从经济观点看,是由于否定经济自由和面向社会的市场所造成的极大浪费的起码的最终结果;是生产力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关系的绝对官僚化;是长时期的科技落后。
考茨基对列宁的批评仅仅是在布尔什维克的罪恶刚刚冒头时进行的,倘若他能活到一百岁,看到 “列宁的战友和学生” 斯大林的 “大清洗”,他肯定会和共产主义一刀两断。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13)
1945年,苏联将军伊万率领苏军攻打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他手下的官兵向他报告: “城里布满重兵,建筑物的窗口都架着机枪,敌军戒备森严!” 伊万当即高呼: “共产党员冲啊!”
1968年,伊万将军又率领苏军重返布拉格。手下官兵向他报告: “布拉格大小百货商店柜台里都摆满了新式皮鞋、高级西装、美味食品、日用电器。” 伊万立即下令: “共产党员冲啊!”
荀路 2018年11月初稿
2020年4月23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