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第五期《读书》杂志有两篇文章很值得一读,一篇是《V——chip与美国的言论自由》,一篇是《英国最有名的黑人是谁?》。前一篇我给大家已做了评介,这次我给大家评介后一篇。
事件的缘起是这样的:
1999年2月的一天,BBC(英国广播公司)“在线新闻服务”发布了一幅网上新闻图片,那是一个名叫斯蒂芬·劳伦斯的黑人小伙的特写。下面有这样的文字:斯蒂芬·劳伦斯,英国最有名的黑人。
斯蒂芬·劳伦斯本是一件凶杀犯罪的牺牲者。1993年4月22日晚,他在伦敦东南部的威尔霍尔大街等公交车时,无缘无故被几名素不相识的白人青年围起来殴打,最后竟被残忍地杀害了。这个牙买加移民的后代,当时只有18岁。
在大英帝国的首善之区发生这样的事,固然骇人听闻,但它与新闻法治又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劳伦斯之死,已经和正在极大地改变着英国社会:从行政到司法,从警察制度到教育体系,从自命为公正平等的政治和法制价值体系到英国赖以存在的种种社会关系,都由此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质疑、批评和挑战。正因为如此,劳伦斯才在不期然中成了一个“最有名的英国黑人”。而这些变化之所以能够发生并向这样的状态演化,英国新闻媒介既是始作俑者,又是最重要的发动机和导航者。而新闻界的全部所作所为,离开英国的新闻法治都是无法想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塑造着社会,而塑造媒介的则是法治。
促使劳伦斯成为英国社会最大议题之一的主要力量,是新闻媒介。整个过程折射出了当代英国新闻法治的全部精魂,那就是,新闻媒介是社会的哨兵、预警者和监督者,必须从法律上提供保障,使其能够履行这样的职能。
劳伦斯之死最初并没有引起新闻媒介的特别关注。他被杀害的第二天,当地的一些报纸和广播电视将之作为普通的凶杀案作了一般性的报道。过了一天,几家全国性的报纸也以同样的调门就此事刊发了消息,但都没有上头版,更不用说头条了。这样的犯罪新闻,是英国媒介每天日常菜单上的必备食谱,人们早已见怪不怪了。
事情本来就这样过去了。如果一位白人尤其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在伦敦的大街上无缘无故地惨遭杀害,那也许会成为英国社会一个关注的焦点。但劳伦斯是一个黑人。黑人被杀,总有什么理由,这是白人社会对这类事一种常见的看法,英国也不例外。
 但问题就出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白人社会观念上了。当劳伦斯们不断无缘无故地被白人致伤致残,乃至无端夺去生命,而整个社会却麻木不仁,甚至还认为事出有因的时候,英国新闻媒介不安起来。于是,事情急转直下,斯蒂芬。劳伦斯之死引发了20世纪末英国社会最大的一次社会动荡。
但问题就出在这种根深蒂固的白人社会观念上了。当劳伦斯们不断无缘无故地被白人致伤致残,乃至无端夺去生命,而整个社会却麻木不仁,甚至还认为事出有因的时候,英国新闻媒介不安起来。于是,事情急转直下,斯蒂芬。劳伦斯之死引发了20世纪末英国社会最大的一次社会动荡。
先是《每日快报》登出一篇深度报道,抨击伦敦社区潜伏着严重的种族主义。这使许多人开始意识到此案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刑事凶杀。紧接着,纳尔逊·曼德拉在当选南非总统后访问英国时,专程会见了劳伦斯的父母。在对劳伦斯之死表示同情之时,曼德拉严厉谴责了英国社会的种族主义势力。曼德拉的崇高威望使他的这一抗议性举动广受关注,更多的新闻媒介开始深入思考劳伦斯之死对英国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
1996年,伦敦刑事法院对被提起公诉的三个杀害劳伦斯的嫌犯进行调查和审理后,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而当时已有许多证据表明,这几个白人青年都拥有利刃尖刀,常常叫嚷要杀“黑鬼”(这些都有警方的录像为证)。劳伦斯被杀后一个小时,有人看到嫌犯们神情慌张地在家里清理凶器。但是,陪审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结果,三个白人青年在人们的重重疑惑中,走下了审判台。
但是,石破天惊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97年2月,英国著名的全国性报纸《每日邮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登出了五个白人男青年(三个嫌疑犯及两个未受指控的青年)的特写照片,并在每人的照片下面清清楚楚地标明了他们的姓名。而在照片之上,是通栏的特大号字型作成的标题,只有一个词“MURDERS(杀人犯)”。该报在当天的第二、三、四版,刊登了大量详尽的调查性报道材料,指认五名白人青年就是杀害斯蒂芬。劳伦斯的凶手,言之凿凿,俨然铁证如山、不容抵赖,大有不将这五个人绳之以法不能还天下一个公道之势。
法院认为罪名难以成立而予以开释的人,却被一家世界知名的报纸以如此重磅炸弹式的版面语言,真名真姓并配以其近照,明明白白地指控为“杀人犯”。这种情况,在世界新闻史上前所未有。更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每日邮报》在该爆炸性标题下面的副标题是:“如果我们错了,你们就以诽谤罪起诉我们吧!”
《每日邮报》的惊人之举并没有惹来诽谤罪的官司,却打开了重新调查劳伦斯案的大门。英国新闻媒介进而掀起了全面批评英国社会积弊的浪潮。《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镜报》等英国全国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舆情激烈。
关于英国的司法制度,“并不是所有犯罪都能得到处理,也并非每个杀人犯都能绳之以法,但斯蒂芬·劳伦斯案件说明(英国的)刑事审判制度已经一败涂地,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针对警方的调查和侦办,“所有的谴责可以归结为三个词——无能、腐败、种族主义,而真正的被告应该是英国最强大的警力所在地——伦敦警察厅”。
英国的教育制度则被抨击为滋生种族主义无形的温床,“到目前,根本没有对孩子从小学就开始进行种族宽容的教育,也不去引导他们正确理解和对待其他的文化和传统”。
这些排山倒海的批评产生了连锁性效果,一系列的调查开始了。
厉害了,大英帝国的报纸!虽然司法不公在任何国家都是敏感的问题,但将此问题列为禁区不许舆论公开评判,绝对是极权专制作祟的问题。劳伦斯被害,凶手被无罪释放,任你是谁都会感到这是不公正的。倘若在中国,“劳伦斯”能得到媒介如此的关注吗?哪个媒介有胆量说这个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已经一败涂地”?又有哪个媒介敢公开谴责警方的案件侦办是“无能、腐败、种族主义”?
早在中国北宋初年的1066年,英国司法已经开始应用普通居民组成的陪审团和通行于全国的普通法。近千年的法治传统使得英国朝野的绅士风度尽显风采。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谁都不愿以蛮不讲理的面貌出现。于是,在劳伦斯一案中,人们一方面看到媒介敢于对司法不公大张挞伐,一方面也能看到政府面对批评勇于自我反省。
接着看双方的“费厄泼赖”:
“警务投诉委员会”调查的结论是,伦敦警方对劳伦斯遇害案件的侦办“明显地软弱无力、漏洞百出,并且一再丧失破案良机”,有关负责侦办的警官“有一系列严重失职行为”。警方内部也有人站出来,揭发说委派的侦办劳伦斯案的人员,有明显敷衍塞责的倾向。在强大的压力下,1998年10月1日,伦敦警察总监保罗。坎顿爵士被迫作出如下姿态:“我对至今尚未将杀害斯蒂芬。劳伦斯的凶手绳之以法深为遗憾,并为我们的失误再次向他的父母致歉。”
就改革立法和司法,以退休法官威廉。麦克弗森爵士为首的专门调查委员会作出报告,建议“中止不得以同一罪名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二次起诉的刑事审判制度”,同时指出英国大城市的警察局普遍存在着“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倾向”。这已经明显地发出了信号,对劳伦斯案,从侦办到审理,确实存在因种族主义作祟而使凶手逍遥法外的可能性。
对于教育制度和社区关系,有关方面准备通过立法改革中小学生的课题设置,增加不同文化和种族“互相理解和谅解”的内容。
但英国新闻界并不满足于这些反应,他们进一步将劳伦斯之死反映出的种族主义坚壳和积淀经年的社会问题一层层剥开去。1999年2月,英国新闻界发起了第二轮攻势。先是BBC播出了长达45分钟的纪录片《为什么会有斯蒂芬·劳伦斯之死?》,问了一系列“为什么”。其中最尖锐和深刻的问题是:“以往,这类案件已发生过数以百计,为什么都没有引起新闻媒介的注意,唯独劳伦斯案成为历史性的焦点?”通过极具冲击力的画面语言,该片对上述英国社会的积弊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抨击,使人们从中不难得出结论:英国的种族主义势力已深深地潜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不严肃对待将会带来重大的社会危机,甚至造成整个社会结构性的破坏。该片也使许多自认为身居主流社会的白人真正感到了一次羞辱和愤怒。片中有这样的镜头,控方律师向坐在被告席上的一名白人青年质证时,按照法律程序首先提问:“你的名字是大卫。诺里斯,对吗?”这个杀人嫌犯竟用面带嘲讽的表情回答:“我对这一问题保有不自证有罪的特权。”英国法律规定,刑事被告在可能会自证有罪的问题面前可以保持沉默。但诺里斯连被问到自己的姓名时都搬用这一“特权”,明显说明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于是,有媒介尖锐地质问:“这一特权是为有理性的公民而设,还是专门向那些蔑视法庭,践踏法律的狂徒提供保护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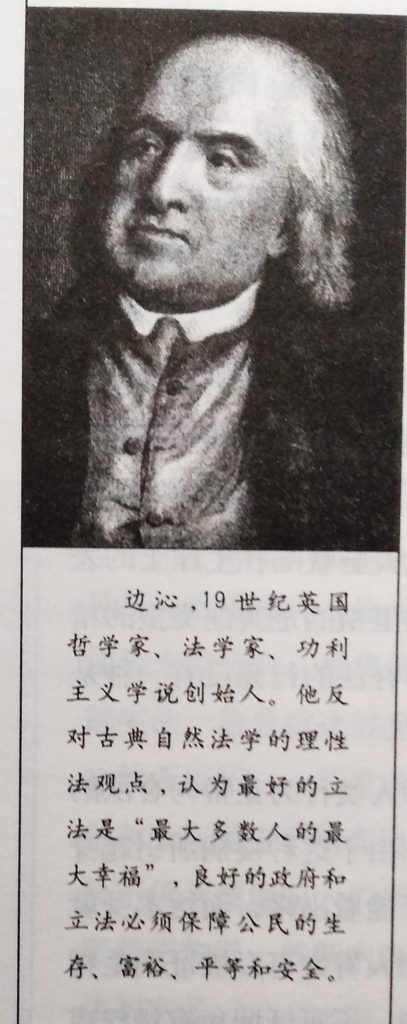 随后有媒介质问:“为什么普通的黑人平白无故受到警察盘问和搜查的比例是白人的五倍?”“诺里斯们”如此狂妄的态度完全是植根于社会深层的种族主义观念。在这一点上,警察侦办此案时的疏于职守与白人杀人犯的观念如出一辙,“不就是杀了一个黑人吗?”但掌控着四万多警务人员的伦敦警察总监保罗。坎顿爵士,断然拒绝新闻媒介和社会的批评,认为他的手下已尽职尽责,而且警察中间不存在任何“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由此,新闻媒介开始呼吁这位英国警界的“巨无霸”下台,随后,伦敦和英国各地都出现了示威游行,要求这位本身就表现出强烈种族主义倾向的总监离职谢罪。
随后有媒介质问:“为什么普通的黑人平白无故受到警察盘问和搜查的比例是白人的五倍?”“诺里斯们”如此狂妄的态度完全是植根于社会深层的种族主义观念。在这一点上,警察侦办此案时的疏于职守与白人杀人犯的观念如出一辙,“不就是杀了一个黑人吗?”但掌控着四万多警务人员的伦敦警察总监保罗。坎顿爵士,断然拒绝新闻媒介和社会的批评,认为他的手下已尽职尽责,而且警察中间不存在任何“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由此,新闻媒介开始呼吁这位英国警界的“巨无霸”下台,随后,伦敦和英国各地都出现了示威游行,要求这位本身就表现出强烈种族主义倾向的总监离职谢罪。
与此同时,《每日邮报》再次以头版、二版的大篇幅刊登社论《为什么我们坚定不移》,除了重又指名道姓地控称五个白人青年是“杀人犯”外,再次表示“欢迎(被指控为杀人犯的白人青年及其家属)起诉本报”,并认为法律程序有利于“真相大白”。
更为令人吃惊的是,《星期日电讯快报》从内务部官员手中取得官方调查报告摘要,并立即全文刊出。随后,事态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英国内务大臣杰克·斯特劳闻讯后立即以泄密的理由下达了禁发令。斯特劳向新闻界发出这个禁令是在2月22日,新闻界立即就此上诉到法院,几个小时后这个禁令就被法院推翻了。2月23日,《星期日电讯报》照登不误。很快,英国所有的主要报纸都连载了这个数万字的官方调查报告摘要。不仅如此,媒介转而以激烈的言辞猛烈抨击工党政府,“这是政府执意控制新闻媒介的最新也是最拙劣的一次尝试。新工党(首相布莱尔称自己代表的是‘新工党’)只是善于学习反面的东西,在控制新闻媒介方面,他们与撒切尔的保守党一样具有无限的癖好”。斯特劳和内务部的次长在议会里也遭到了保守党的猛烈抨击。
在劳伦斯案件中,英国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它设定了一个议题——种族主义正在瓦解英国,然后借助对斯蒂芬·劳伦斯这个勤劳工作的黑人青年的种族主义凶杀案,把整个社会这方面长期积淀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一齐暴露在人们面前。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内阁、议会、法院、警方、学校、社区等等,都受到了强烈的抨击。新闻界大有得理不饶人、一追到底之势,很多高官显贵则很难受,甚至丟官弃爵,身败名裂。
新闻媒介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掀起这样的狂涛,根本原因是有法律保障。这种法治是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的: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行政、立法、司法可以互相监督制约,但还必须有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在任何社会都不例外。英国新闻媒介一向以其监督职能而自豪,无论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不断有内阁高官因腐败行为被新闻媒介曝光而蒙羞下台。即使有了反对党的监督、议会的监督、法律的制约和新闻媒介无时无刻的追踪,依然有许多政治上的黑幕交易。所以,英国人说,新闻媒介的监督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但是没有这种监督,腐败必然更加猖獗。
权利与义务相对应,新闻媒介面对的限制也是很多的。在司法报道方面,英国本来是有“蔑视法庭罪”的,记者在没有结案前报道案情,可以说处处是雷区:或误将“嫌犯”说成了罪犯,或带有倾向性使公众同情或憎恶当事一方,或在法庭上偷拍偷录,或对案件审理中法官的执法有所评价,或在法庭要求交待报道的消息来源时予以拒绝……等等,都有可能被判“蔑视法庭”,因此会面临坐牢,罚款,或二者同时执行。像《每日邮报》那样指名道姓地指称某人是“杀人犯”,如果是在案件审理中,必定会被法庭认为是“媒介审判”而构成蔑视法庭罪。但是当法庭程序终结后,新闻媒介指称陪审团认定无罪或罪名不能成立的人有罪,却不算“蔑视法庭”。这看似荒唐,实际上是一种有意留出的“法制缺陷”或“法制真空”,从而为社会和新闻媒介对司法审判进行评论留一个渠道,以求通过新闻媒介的介入和舆情民意的表达来减少冤假错案。
人们总以为新闻媒介是“无冕之王”,在西方社会被称之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部门。因此有人说,在西方国家,新闻媒介揭露政府的丑闻不仅是一项重要的舆论监督,而且是一种“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但是,有时情况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简单乐观。
冷战时期,英国有两名记者通过秘密渠道得知英国海军部门内有一名间谍,还得知有两名高官曾主动使这个间谍避开海军部最严密的保密审查。于是,记者将此事公诸于世。消息传出,英国上下一片哗然。不久,英国国会派出拉德克利夫勋爵调查此事。
但是,记者在接受调查时,拒绝透露消息的来源。勋爵只好让检察官将两名记者告到了法院。法院审理后将两名记者判处六个月的监禁。记者不服,将案子上诉到英国上诉法院。
记者认为,他们有权揭露政府官员的不法行为,否则这些行为就会存在发展下去。如果他们不对消息来源保密,就得不到消息,因为提供消息的人知道自己将被暴露,就不会向记者开口。
但是,上诉法院的大法官却说:“如果记者不告诉法院消息来源,那么谁知道消息是不是捏造的?即使不是捏造的,谁又能保证它不是某个好事之徒为哗众取宠而散布的流言蜚语?除非说明消息来源,否则只可能是传言。传言对国家是有害而无益的。”
于是,大法官大笔一挥,维持原判。
此一判决作出后,几十年来,英国的各级法院都曾以此作为震慑新闻界的尚方宝剑。这一案例告诉新闻媒介,新闻监督有时要付出代价的。
《英国最有名的黑人是谁?》最后告诉人们:
……实际上,英国新闻媒介监督性的传播信息、反映舆论、开展批评的社会责任功能,与其追求市场利润的商业功能、娱乐功能、服务功能等,总是混杂在一起的,常常令人既爱又恨。请记住,这个在报道斯蒂芬·劳伦斯案件不遗余力、颇有“铁肩担道义”风范的英国新闻界,也正是把戴安娜王妃一直追踪到死的那个以制造煽情故事闻名于世的英国新闻界;也正是那个滋养了马克斯韦尔、默多克这些唯利是图的垄断新闻媒介的产业大王的英国新闻界。这种种面目的“英国新闻界”,都生活在同一个法治社会的屋檐下,所以,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好”或“坏”来概括英国的新闻法治,就如同很难说“英国新闻界”是“好的”还是“坏的”一样。其新闻法治秉持的原则很实用——“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使这样的新闻界在市场竞争中,诸如“挖掘隐私、追求煽情、制造轰动”等恶习“屡制不改”,法治也仍然采取一种重在保障的取向,即从根本上保障新闻媒介的监督功能,使其能够对整个社会特别是立法、司法、行政以及重要的利益集团无时无刻地进行了望、预警和监督,以保证社会对于种种瓦解、破坏性的倾向能够防患于未然,而不致于使其不受约束地积淀、演化,最后一旦总爆发时,任什么贤才伟人也无力回天。一句话,他们认为,实行这样的法治对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有好处。
说得好!说得对!这么浅显易懂、一目了然的道理,有些身居高位的要人为什么不但不领会,反而一意孤行地反其道而行之呢?
有些自以为是的大人物总以为只要大权在握就万事大吉了,但历史老人的见证却恰恰相反:独裁者有谁能“光照千秋”?
荀路2020年元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