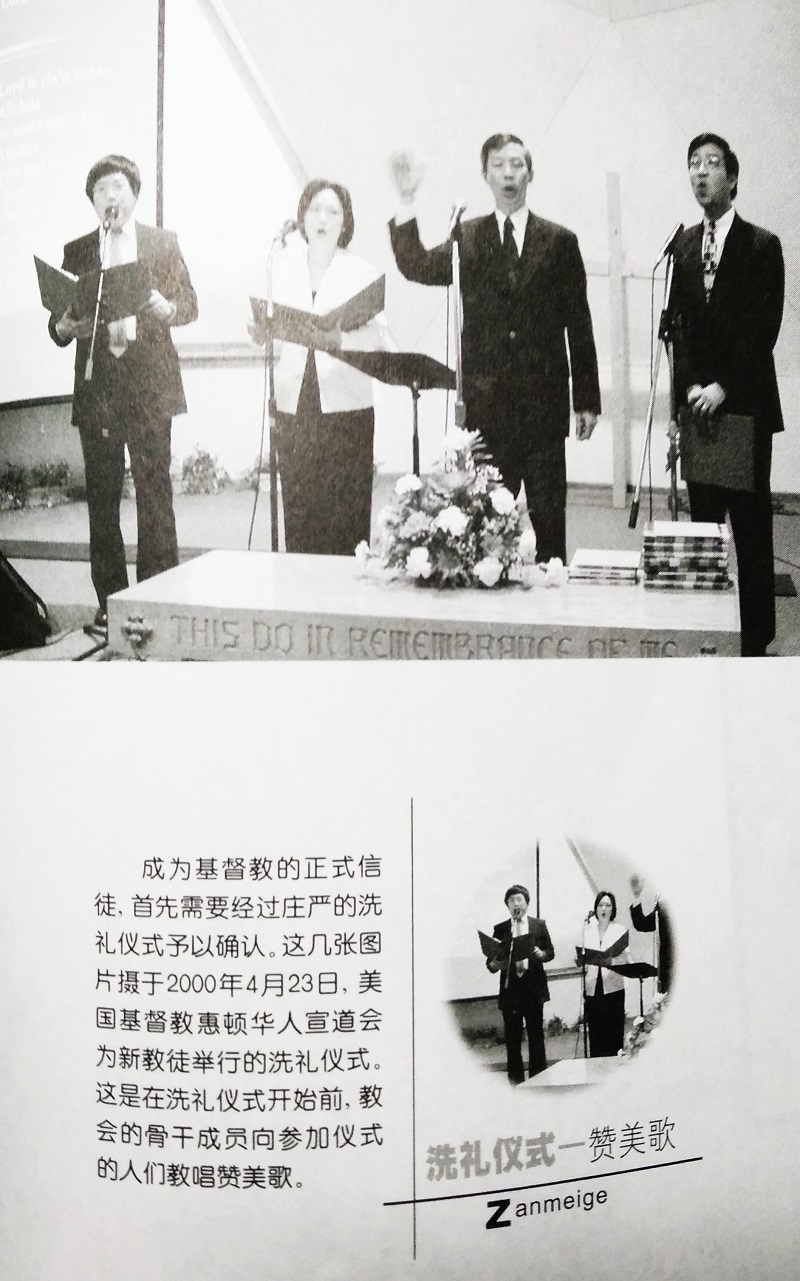(四)
但是,该裁决一出,立刻震动了美国,并在全美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波,主要都是一些反对此裁决的声浪。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布什也已亲自投入这场论战。他在加拿大与俄国总统普京召开记者会时也特意谴责法院这项判决。他说:本人认为,上帝显然是我个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仍以这项判决与美国历史及传统脱节的原因。”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反应显得更为激烈,当裁决消息传来,参议院立刻中止了国家防务法案的辩论,几分钟内便以99票对零票通过决议,谴责该上诉法院的这一裁决。星期三当晚,亦有百多名众议员(多为共和党人)齐集国会山,面对国旗集体朗诵效忠誓辞,以示抗议。
至于美国民间,事发以来,有数不清的电话、电子邮件涌向媒体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许多美国传媒工作者对此都感到十分震惊。一位媒体工作者说:每个人听到后的本能反应都是大喊“什么?”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就这一裁决也理所当然地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论战。而打赢这场官司的纽道医生则说:这宗“爱国”诉讼是代表他女儿进行的,但他自己受到了威胁,有一些威胁电话不断打来,这些电话来自那些崇拜上帝的人。
正因为如此,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作出裁决的第二天即宣布暂停执行,等待法庭复议。人们推测,即使复议不变,司法部也肯定会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而到了最高法院,该裁决十有八九会被推翻。
尽管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这一裁决几乎遭到普遍反对,它的前途——即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吉凶未卜且凶多吉少,但从法理角度而言,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不妥。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项带有“破天荒”性质的“政治正确”行为。说它“破天荒”,是因为如果顺着誓辞违宪的思路推,美国从立国之初到现在,二百多年来,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已经成为美国人的经验、习惯、历史、传统,甚至成为他们的个体无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都经不起宪法修正案第一条的衡量,因而是违宪的。这也正是这个案子足以惊爆美国的最根本的原因:纵然它不能改变美国的过去,所谓法不咎往,但却能深刻地影响美国的今天和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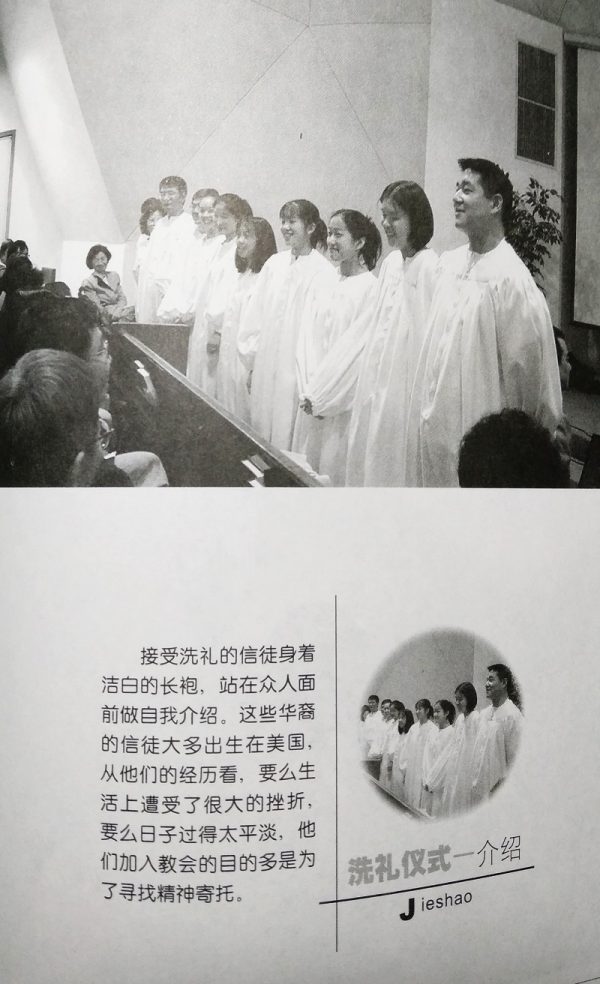 这里给大家谈谈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这里给大家谈谈美国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大家都知道,一种规则要成为法律“家族”中的一员,必须由立法机关制定认可。反过来说,只要立法机关举手通过,法律“家族”就多了一名成员。这样看来,这些“成员”的资格似乎与法院无关。起码在中国,我似乎没看到哪个法院宣布哪条法律违宪之举。但是在西方国家,有时法院(一般是最高法院)却常常要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是否具有法律“家族”的成员资格。它们手执宪法左审右查,如果一条规则在它们看来是“违宪”,它们就会取消这条规则的法律“家族”资格。
司法审查权是美国最高法院最重要的权力。但这项权力并不是宪法所赋予的,它的确立乃是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一桩诉讼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1801年,美国总统亚当斯在离任前,一下子任命了一大批人为联邦法官(原来美国也玩领导下台前的“突击提拔”)。尚未就任的新总统杰斐逊对此十分恼火,但也无可奈何,他所能做的就是上任后扣下了几份还未来得及发出去的委任状。这些委任状中有个人名叫威廉。马伯里。这老马不甘心,他发现1789年国会颁布的一项法令授权最高法院审理他这种案子。于是马伯里便向最高法院状告新任国务卿麦迪逊,要求最高法院颁布强制执行令,命令麦迪逊发出对他的委任状。
马伯里这样做马上使最高法院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最高法院受理此案,颁布了强制执行令,总统和国会肯定予以抵制,这就会损害最高法院的威信;如果不受理此案或不颁布强制执行令,又无异于承认自己无权过问行政和立法事务,同样会降低最高法院的地位。最后,刚从亚当斯政府国务卿位上转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马歇尔老谋深算,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首先,他声明马伯里有权起诉,因为委任状已有总统签字和国务卿盖章,麦迪逊应该颁发对马伯里的委任状。但是马歇尔话锋一转又说,根据美国宪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只有在驻外大使、公使、领事以及州政府为诉讼当事人时,联邦最高法院才有初审管辖权,而马伯里不属于这一范围,因此,此案不属于最高法院直接审理的案件。马伯里所提到的1789年国会颁布的那项法令,扩大了宪法赋予最高法院的权力,违反了宪法第三条的规定,因而无效。
为什么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国会的立法因为“违宪”而无效呢?马歇尔对此解释说,宪法是最高法,因此法院不能执行与之相悖的任何法令;宪法是法律,法官的职责就是执法,因此最高法院在解释宪法方面有着最后、最权威的发言权。这样,马歇尔不仅巧妙地解决了面对的难题,保住了最高法院的面子和地位,而且还开创了最高法院判决国会法令是否符合宪法的先例,从而确定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和干预行政的权力。虽然此后争论一直不断,而且没有明文规定,但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实际上已被广泛接受,成为美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西方人认为这样有两点好处: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民直接意志的体现,而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是立法代表们的意志体现,司法审查可以防止代表意志超越国民(被代表人)意志;二、这样可以保持一般法律在宪法之下的统一性。
(五)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判决效忠誓辞违宪,是因为誓辞中含有宗教字眼。那么,如果把宗教字眼从中删去不就行了。当初出台于1892年的效忠誓辞原来是没有宗教字眼的,直到1954年,由某天主教团倡议,艾森豪威尔总统敦促,国会才通过一个法案,即在国家之后加上短语“上帝之下”,以示自己是一个有神论国家(所以现在看来,这个法案是“非法之法”了)。但是,“上帝之下”添上去不难,现在要去掉,却不容易。
为什么?因为要挖掉的并不仅仅是两个字,它同时更挖掉了美国赖以成为美国的宗教传统。美国是一个清教徒移民国家,二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使这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尽管宪法中政教分离的原则使基督教不可能成为由政府提倡或国会立法的国教,但从民间自发认同和普遍接受的角度,将之视为国教,却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而传统的意义就在于它也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合法”的惯性下,誓辞中的“上帝”字眼“理”所当然地被人们忽视了。但它毕竟经不起宪法挑剔,只要有人把它拎出来说事,你就得面对。
然而,现在令美国人所棘手的问题是,这个案子已经远远不是它本身了。比如,美元不论币值,也不论纸币硬币,一律都印有“我们信赖上帝”。制币是政府行为,这样做,是否违宪?美国新总统上任时,总要手按《圣经》宣誓,这是否也有违宪之嫌?如果这案子打到最高法院,按惯例,在审理案子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宣誓中都要说:“上帝保佑美国和这个法庭”。这又该如何论处?还有,美国法庭上证人作证前的宣誓,法官就职时的宣誓,总统公开讲话时习惯性的结尾以及美国国歌的歌词,都因其含有“上帝”字样,是不是统统违宪?
如果上诉法院复议不变,如果最高法院维持原判,下面势必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根据这个判例,上面所举都有违宪之嫌。那位纽道医生难道是看准了效忠誓辞的典范性以及由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才摩拳擦掌,下一步准备指控美元违宪了吗?可是,一旦这些都被判为违宪,那么,美国还是不是今天的美国?这就是由该案所引发的美国的忧虑。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是宗教信徒最多、教徒中文化程度最高、教派最为复杂、宗教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宣称信仰上帝的人中,约60%的人不常去教堂。这个似乎矛盾的事实表明,在美国,人们多半或许只愿意私下崇拜上帝,同时也表明只有少数人才怀有很深的宗教感情。
据盖洛普民意测验,1958年是美国宗教活动的高潮时期,那一年有49%的教徒说他们一个星期中至少去了一次教堂。从1958年以后,去教堂参加礼拜活动的人数便逐步下降。1960年下降到47%;1970年降到42%;1980年则只有40%;以后多年维持在这个数字。由此可见,在美国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宗教复兴浪潮。
从年龄上看,老年人比年轻人去教堂的次数多。比如50岁以上的人常去做礼拜的人约占50%,而30岁下的人中,只有33%的人常去教堂。难怪有人戏曰:也许年龄的增长会使人越来越靠近上帝。
从性别上看,女人比男人更笃信宗教。一般情况下,46%的妇女经常去教堂,而经常去教堂的男人只有33%.
在美国三个主要宗教派别中,天主教徒去做礼拜的人数最多。49%的天主教徒说,他们每周至少去做一次礼拜,而新教教徒中这种人占41%,在犹太教徒中只占20%.
那么,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呢?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曾就一系列有关上帝的有趣问题进行过一次调查。在调查中,要求人们回答上帝在他们看来更像父亲还是母亲,主人还是配偶,审判者还是情人,朋友还是国王,创世者还是宗教信仰疗治医生,救世主还是解放者。调查结果表明:
★68%的人说上帝更像主人而不是配偶。只有8%的人说像配偶,另外18%的人说对于他们来说上帝可以两者皆是。
★65%的人说上帝更接近于父亲的形象而非母亲的形象。只有7%的人将上帝幻想为母亲的形象。也有24%的人认为上帝可以是父亲和母亲形象的综合。
★17%的人把上帝看成是情人,而58%的人把上帝想象为审判者。另外22%的人从上帝身上可以看到这双重特点。
★44%的人说上帝更像一个朋友而不像国王,也有27%的人觉得上帝像国王,26%的人认为上帝对他们来说两者兼而有之。
★49%的人把上帝规为救世主,把上帝比作解放者的人占10%,但认为上帝两者兼有的人占36%.
★37%的人说他们把上帝看作是创世者而非医生,认为上帝是医生的人占14%,然而却有45%的人认为上帝具有双重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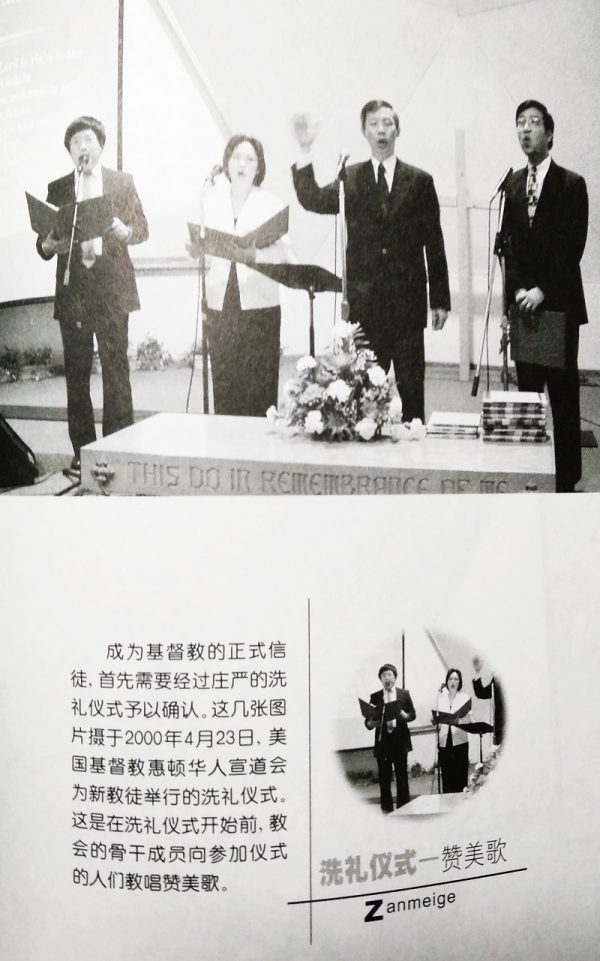 由此不难看出,在美国,人们与宗教的联系几乎就像生活中任何一件事一样普普通通而又必不可少。可以说美国信仰上帝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礼拜和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必须是一种私人的事情,要完全与政府相分离。上帝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只具有个人的意义,上帝以父亲的形象出现,是宇宙的主宰,为人们进行道德伦理以及与宗教有关的事物方面的仲裁。
由此不难看出,在美国,人们与宗教的联系几乎就像生活中任何一件事一样普普通通而又必不可少。可以说美国信仰上帝的绝大多数人认为,礼拜和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必须是一种私人的事情,要完全与政府相分离。上帝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只具有个人的意义,上帝以父亲的形象出现,是宇宙的主宰,为人们进行道德伦理以及与宗教有关的事物方面的仲裁。
美国学者的看法是,宗教信仰也许已经深入到这个国家的每个层次,但是这种信仰更可能是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而不是反映在对于教堂礼拜活动或其他固定宗教仪式的盲目忠诚上,或是对某一宗教格言的字面意义的盲从上。
诚然,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在宗教上也不例外,一方面美国大多数人相信上帝;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中种种犯罪与道德堕落的现象层出不穷。宗教信仰并没有使美国社会成为一个像宗教教义与宗教道德所要求的那样的理想社会。人们的信仰与指导他们生活的准则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鸿沟。但是,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既不同于政教合一国家的宗教专一与狂热,也不同于无神论国家中人们对宗教的冷漠。作为美国社会文化的一种核心力量,美国宗教将以它在美国社会中的特殊方式继续发挥其积极的影响。
看了以上论述,就不难理解美国民众表现出的宗教情结——内心热烈,行为节制。
美国之为美国,宗教之功难以抹灭。可以说,是美国的宗教塑造了美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当然,说宗教塑造历史不是说它对政治直接干涉,而是指它作为一种终极价值和力量之源对政治(人)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总统就任宣誓,并不是发誓为上帝替天行道,而是祈求上帝帮助他,保佑他,给他力量。这是一种信念的支撑。再者,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推其原因,也是为防止某一教派掌控政权,从而动用政权力量干涉宗教自由。说到底,这个原则还是为了在信仰自由的前提下保障宗教。因此,对当初是清一色的清教徒来说,那种超越了具体教派意义上的宗教和宗教精神如果不是支配政治而是融入政治,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事实上这种融入形成了传统,也形成了相应的秩序。而美国是一个格外珍惜传统和注重秩序的国家,现在,这个传统秩序面临违宪指控。如果它真的被宪法终结,那么,对现在仍然大多数是清教徒的美国人来说,是不是乱了套而“国将不国”呢?
但是,美国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国家。它不但是一个有着宗教传统的有神论国家,它同时也是一个高度自由和高度宪政化的国家。宪法的要义即保障信仰自由在内的公民自由。因此,美国之为美国,是在于它所奉持的自由观念。《美国读本》一书中的《美国的观念》这样表述美国:
其他国家都是在这样的人民中形成的,他们出生在他们的家族自古以来繁衍生息的地方。不论他们的政府如何更迭,英国人是英国人,法国人是法国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他们的民族国家可以分裂、再建而无损于他们的国家的地位。而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
是的,在比较的意义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形成于地缘的或种族的因素,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它的形成仅仅缘于一种观念:自由的观念。是自由这个观念使最初的移民们奔赴北美,并缔造了美国及其文明。因此,在世人眼里,美国的形象肯定不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而是曼哈顿岛上的自由女神。
如果说在制定宪法修正案的那个时代,由于移民成份的单一,宗教自由仅仅只体现在基督一系的不同教派间,它并不包括在这之外的异教徒和非教徒。那么,今天时移事易,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内涵着的不同宗的信教自由乃至非宗教的自由,越发具有现实意义。美国因其自身的移民传统和开放传统,以致有人这样声称,再过若干年,美国的白人将有可能成为少数民族。在一个不同种族杂处的国家中,当这个国家的上层建筑不再像今天这样仅仅控制在白人手中,那么,假如最高法院的法官有非白人非基督徒出身,他又为什么要在法庭宣誓中祈祷“愿上帝保佑”?更有甚者,总统万一是个无神论者,他在就职时可以手按《圣经》起誓吗?如果说这些都是传统,那么,这些传统是否侵犯了他们作为个人的宗教或不宗教的自由?
作为一个有神论国家,传统美国和宪政美国发生了誓辞上的冲突。现在,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就该冲突作出了裁决,应该说是符合政治正确原则的。所谓政治正确,即正确处理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一切事务。政者,事务也;治者,处置也。处置标准如以宪法修正案为其圭臬,则谓正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固然重要,它保证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延续;但宪政更重要,它是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根本维系。当传统与个人自由以及保障这种自由的宪政制度有所不吻合时,需要变动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尽管这种变动从传统角度看,美国可能不那么美国了,但宪政至上,无疑将使美国更美国。毕竟,如上所言,美国首先是以它的自由和宪政著称于世的。
此文发表时,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尚未作出,因此,纽道医生能否笑到最后不得而知。但我以为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效忠誓辞”的违宪裁决推翻或维持,都是宪政法治的胜利!因为此类事件如果放在某个非法治国家,就连在基层法院立案都无可能,遑论上诉到最高法院。
荀路2020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