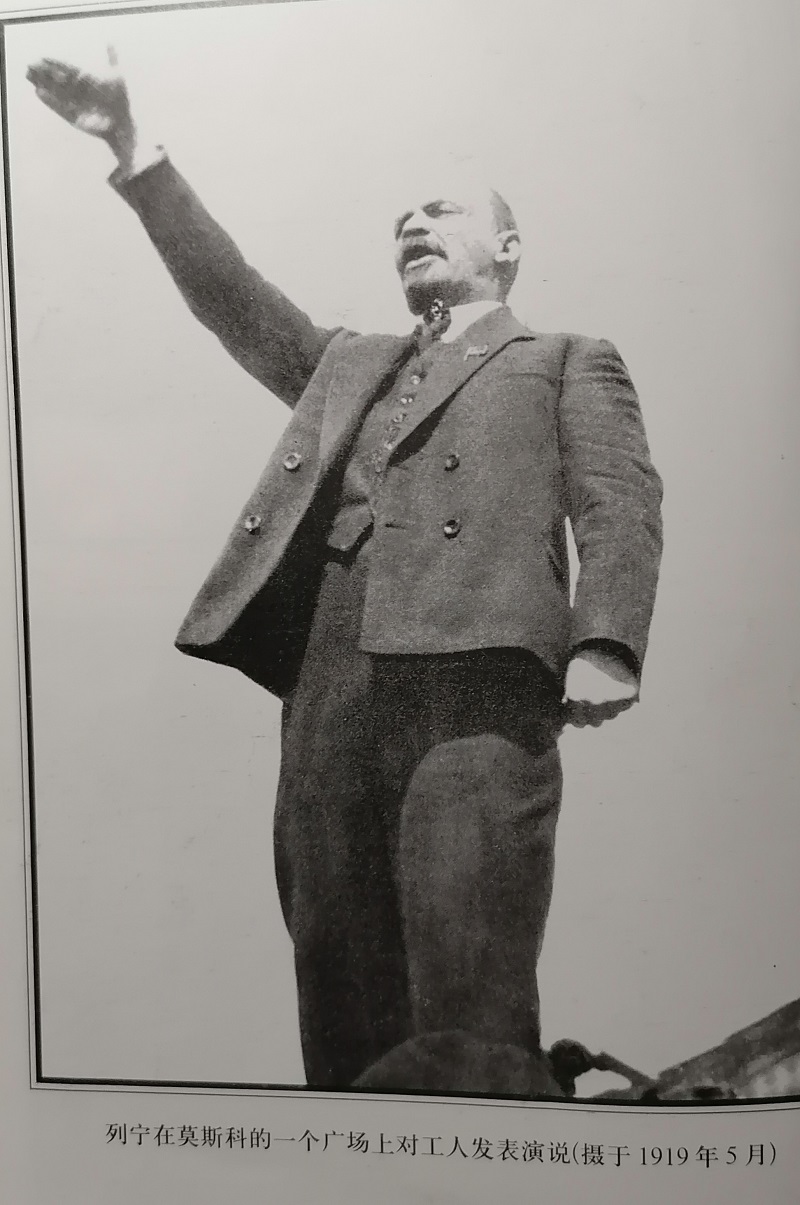胡克对俄国革命的反思(一)
(悉尼.胡克<1902一1989>是美国社会哲学家。作为实用主义思想的阐述者,他是第一批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学者之一,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坚持认为不受约束的民主对于社会和科学进展是最可行的政治结构。重要著作有《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一种革命的解释》(1933)、《马克思的意思》(1934)、《从黑格尔到马克思》(1936)、《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1940)、《历史中的英雄》(1943)、《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1955)、《政治权力与个人自由》(1959)、《革命、改良和社会公正》(1975)、《马克思主义和超越》(1983)等。
胡克在《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中,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批评。这里摘录其主要内容,供大家了解胡克是怎样以实用主义为武器去抨击马列主义的。)
胡克在第七章《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活的东西和死的东西》第五节《作为工具的党》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运动,特别是它战斗性最强的一面,尽管关切组织的问题,却表明它本身特别不知道对于用民主方法来发生作用的社会主义,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党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影响远大的危险。它的眼光所注视的,是怎样能尽快地把权力从掌权的那些人手中夺过的问题,而不注视这样的一种观点对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根据这个观点,一个少数的政党,通过它自己的一纸命令就构成一个阶级的先锋队,而这个阶级本身又“表达”了人类的利益。……有些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分子曾对布尔什维克以党的专政代替了工人阶级民主的做法中所包含的对政治领袖的迷信提出警告,列宁对他们所作的答复,作为他在实践上的冷酷无情和在理论上的天真的证据来说,是再没有比这更雄辩的了。他说,“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单是这种问题的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的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他又说,把领袖专政和群众专政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比这更糟,那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抛弃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那是执行特务挑拨者的工作”。但他的议论从来没有到达一种论证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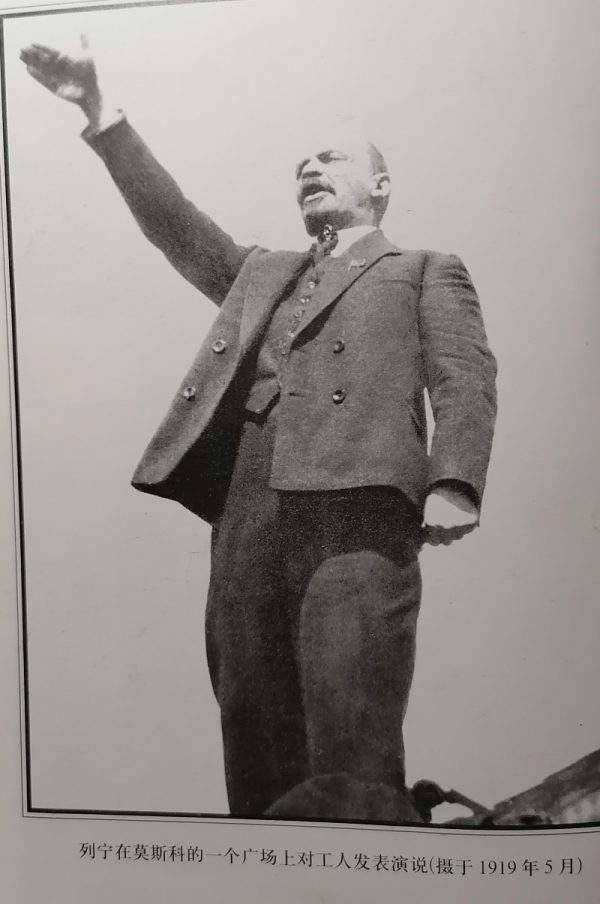 列宁的天真想法所反映的,是他无力去想像他的对于工人的最大利益的概念能在事实上同工人实际的最大利益有所不同。他的愤慨是对批评的一种反作用,由于他天真的救世主式的信念,他除了把这种批评当作对他个人的光明正大的一种攻击之外就不可能有其它的解释。斯大林就是列宁为他这种天真想法所曾付出的代价。而且如果我们想起列宁自己所喜爱的一句箴言所说,“一个政治领袖不仅要对他的领导方式负责,而且也要对他所领导的人们所作的事情负责”,那列宁对斯大林所负的责任便是绝对的。由于具有这种天真想法,列宁指责工人反对派在苏维埃内部为争取更大民主而作的斗争乃是在试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是完全合乎常情的。列宁主张任何一个背离了一贯的CP路线(如他所解释的)的人,一定会终于成为一个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而每一个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当他以前帮助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是一个“革命的英雄”,现在却不由自主地成了一个白卫军。
列宁的天真想法所反映的,是他无力去想像他的对于工人的最大利益的概念能在事实上同工人实际的最大利益有所不同。他的愤慨是对批评的一种反作用,由于他天真的救世主式的信念,他除了把这种批评当作对他个人的光明正大的一种攻击之外就不可能有其它的解释。斯大林就是列宁为他这种天真想法所曾付出的代价。而且如果我们想起列宁自己所喜爱的一句箴言所说,“一个政治领袖不仅要对他的领导方式负责,而且也要对他所领导的人们所作的事情负责”,那列宁对斯大林所负的责任便是绝对的。由于具有这种天真想法,列宁指责工人反对派在苏维埃内部为争取更大民主而作的斗争乃是在试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是完全合乎常情的。列宁主张任何一个背离了一贯的CP路线(如他所解释的)的人,一定会终于成为一个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而每一个喀琅施塔得的叛乱者,当他以前帮助布尔什维克的时候是一个“革命的英雄”,现在却不由自主地成了一个白卫军。
这种头脑简单的丑事的一个最后例证表明列宁所曾准备到达的程度。在新经济政策被引进俄国之后,西方社会民主党主要的理论家之一和坚决反对干涉俄国事务的一个人奥托.鲍威尔曾写道,“看到他们在退向资本主义;我们一向说,他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列宁对此曾愤慨地大声叫喊说:“无论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都在宣传这些玩意,他们听到我们说要枪毙进行这种宣传的人,都感到惊奇。”我们不知道,工人阶级反对派为了他们的主张而实际被杀害,是不是比列宁对他们实行杀害时的自以为是的态度更为令人厌恶。
可以代替列宁主义的政党概念的另一种选择不是传统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党概念。……可以代替列宁主义政党概念的真正另一种选择是:一个既不降低纪律,又因更善于同时把握科学方法和民主程序而在纪律上更为灵活的党。它的任务将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指导有组织的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而不是对它发号施令,以便使“夺取政权”变成把那些在社会共同体中早就存在的民主制度和倾向加以展开的活动的一个方面。它承认并尊重艺术和科学对政治所持相对的自主性,因此就除政治之外避免了对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党的路线”的那种恐怖和愚蠢。它是围绕着原则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一种对领导的迷信。它的远景既不是血腥和恐怖,也不是水乳交融。它必须在现实主义方面毫不退让,这种现实主义无非是意味着一种应用的明智。因此,它将没有那些作为党员的先决条件必须加以接受的理论教条。对它的信任将扩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即准备估计到在走向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的道路中,由它自身的组织活动所可能造成的、甚至是以最好的意图所造成的那些危险和障碍。
在这一节的开头胡克就指出:
社会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乃是当客观情况成熟的时候要来完成的东西。但是怎样去完成呢?是由人们而不是由经济力量去完成。人们可以自发地完成这件事情,而且对于他们所干的事只有一种模糊的意识,或者可以处心积虑地并且通过组织去完成。我们所知唯一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形式是一个政党的行动,这一事实并不因为谈的是政治的“集团”或“社团”而有所改变。一个政党的性质和作用是这样的:如果有真正的其它可用来代替的行动方式,而通常是有这种方式的,则既可能使理想蜕化,也可能使工具败坏了目的。尽管如此,信赖群众的自发行动,把它作为一种代替的行动方式,来希望完成政治行动的值得向往的特色而不冒陷于政治官僚主义的危险,却是不明智的。……
“因此,不论是好是坏,就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这一范围来说,这些革命都是由政党所组织的。它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图是好的,即对于用以领导社会主义运动的那种工具一一政党一一的性质的关切始终处于理论商讨的最前列。我之所以说科学意图,是因为在这里也同别处一样,每当涌现出结论,其含义似乎威胁着目的(政党就是为了这些目的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使用的)时,科学的分析便突然止步了。……党只被了解为能用以赢得政治权力的工具,而不是被了解为能用以达到社会主义的工具。
胡克在这里明确地指出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是社会革命必须由现代政党组织领导;二是政党的工具性质使得它“既可能使理想蜕化,也可能使工具败坏了目的”。但胡克就此问题抱怨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图是好的”一一对政党的工具“性质的关切始终处于理论商讨的最前列”,可是一旦商讨的结论威胁到目的时,“科学的分析便突然止步了”。
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只被了解为能用以赢得政治权力的工具,而不是被了解为能用以达到社会主义的工具”。所以胡克作出这样的论断:
“布尔什维克的成功决不证明他们的理论是科学的。因为他们所赢得的是权力,而不是社会主义。即使他们完成了社会主义——从他们的方法来看,这是一件极端不像会有的事情——这也不会证明他们的方法可以在别的地方成功的。”
让我们看胡克在该书第八章《对俄国革命的反省思考》中的论述。
胡克首先指出:“……在俄国发生些什么事情,这不仅对主观的希望和恐惧,不仅对各种事件的客观进程有影响,而且对许多怀有善意的人所作个人的决定也发生影响。”
胡克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二十多年的苏联经济这样评判:
……在一切不许有反对派,也不能容忍批评的制度中,官方的数字为人们所怀疑是理所当然的(照官方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来说,“统计不可能是中立的”,因为统计是一门“阶级的科学”)。无效率能通过行政决定而变成怠工大罪的一种气氛是不会对客观的报道有什么帮助的。有时甚至苏联的报纸也充满了对假造数字来逃避没有完成其规定定额的官吏们一一总是地位较低的一一的严厉指责。但是不管人们对俄国的统计所抱的怀疑多么深刻,某些事实似乎是清楚的。在电力、农业、航空的各方面,以及几乎在一切重工业部门,俄国已经以巨大的步伐前进了。撇开质量指标和按人口计算的产量不谈,俄国是很容易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提出挑战来作一较量的。……
然而这种工业进步的重要意义却取决于它怎样反映在生活水准上,以及这些水准同什么来比较。如果我们把一般的非熟练的产业工人或农业劳动者的生活水准来同他们在革命前时代的先辈相比较,我们得出的是一种结论;如果我们把他们同美国或英国的工人生活水准相比较,我们得出的便是另一种结论。而且如果我们作前一种的比较时,那又要看拿来作比较的是哪一年。它是饿死了四至六百万人的1933年,还是1936年或1928年或1940年,那十分尖锐地感到物产不足的一年呢?再进一步说,各个历史时期由于彼此在工业技术上十分不同,在它们之间作比较常常是有困难的。……
暂且让我们不顾实际的证据而假定俄国工人的命运是比革命前工人的命运好。那又意味着证明了什么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但是在任何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工人的命运可以有同样的根据来证明比他们在某个较早时期的地位好。如果我们把比较的基础转移到美国资本主义下的工人生活条件,这就变得更清楚。即使抱着最狂妄的党派偏见的人,也不能认真地坚持说俄国人平均的生活水准甚至接近了美国人。而且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用于国内交换的不兑现的卢布的实际购买力,那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美国工业中心的许多救济金领取者的收入还比俄国工人的平均收入为多。如果现时俄国群众的生活水准意味着表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话,我就很想看到能有证据证明这样的一种水准不能为俄国“资本主义”的正常过程所达到。就实际工资来说,沙皇制度下的工人是比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更好的。
……以俄国群众物质幸福犹成疑问的提高来自夸,乃是为社会主义使用一种十分可怜的论证。因为别的国家中工人的命运虽然同他们创造的全部社会产品相比显得相对地较差,但就所分配到的消费品的绝对数字来说,它仍比俄国工人的高得多。
……俄国已在比资本主义各国为短的时期里完成这一举(经济成就),那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除组织方面之外,它是一个遵从者而不是仿效者。在技术上它通过购买而剽窃并学得的就比它发明的为多。与别的剽窃者对比起来,区别在于它没有在这种技术上作出改进。向英国看齐,德国用了50年工夫才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为榜样,俄国就花了20年。从一种纯粹工业上的观点来看,俄国充其量作了西方资本主义同样的工作。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赞美过资本主义改造了地球的面貌并且创造了这样一些工作,世界七大奇迹与这些工作相比就显得只是日常事务罢了。
胡克对当时苏联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并不否认,问题在于:“这些利益是否值得为之付出那样大的代价,那是一个问题。这种代所是否必要,那又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必须继续付出这个代价,或者是付出更大的代价,则是第三个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其实是在任何一个明智的人看来,要解决那个问题必须先解决另一个问题:现状的代价是什么?如果那个代价是战争,则很难、但并非不可能设想随着在社会主义下的权力滥用所引起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的任何丧失,将比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更坏。进一步说,我们现在是正处在一个地位,能够更加适当地估计在社会主义下腐败和压迫的可能的根源,并建立起理论上和制度上的安全保障来防止它们。
“对集体化经济的危险没有自觉的认识,和不承认对自由、批评、个人独立、以及其它一切我们同一种发挥功能的民主政治相结合的基本实践有建立保障的必要,那在我看来就丧失了争取社会主义的理由。因为这就会导向另一种变相的斯大林主义,而斯大林主义不管有什么可疑的成就,其代价是太大了。俄国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牺牲的生命,比它在沙皇统治下的世界大战中所死的人还多得多。俄国全部历史上大众的贫困,包括饥荒在内,没有能开始与俄国群众在上一世代中所遭受的苦难和绝对的政治专制相比拟的。如昂德雷.季特(法国作家)在大清洗开始以前的著作中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更少思想自由、更加屈从、更加恐惧(陷于恐怖化)、更加沦为奴隶的’。”
(成就固然是巨大的,但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代价更是巨大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竭力宣扬它们取得的成就,而对这些成就付出的代价语焉不详或闭口不提。胡克尖锐地指出:“斯大林主义不管有什么可疑的成就,其代价是太大了。俄国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牺牲的生命,比它在沙皇统治下的世界大战中所死的人还多得多”!这种残酷的事实证明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非正义、非道德、非人道、非民主、非法治的本质。胡克的这本著作写于1940年,其时斯大林已执政16年。这期间苏联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造成七百万人死亡,随后的政治大清洗又造成上百万人死亡。而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队和平民死亡人数约为三百万人。)
 布尔什维克上台伊始,俄国人的非正常死亡不仅没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减少,反而急剧上升,一年比一年多,持续了五年之久。主要的原因就是饥荒。
布尔什维克上台伊始,俄国人的非正常死亡不仅没有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减少,反而急剧上升,一年比一年多,持续了五年之久。主要的原因就是饥荒。
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刻出现了粮食危机,来年春演变成饥荒。1918年5月列宁向全国发出电报:“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为保住政权,从1918年夏到1921年春,苏维埃政府实行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为落实法令,苏维埃政府派出了许多武装征粮队,用暴力搜刮农民的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的种粮和口粮也抢夺走了,并将为数甚多的中农和贫农当作富农惩处了。这引发了广大农民强烈的不满。农民用不愿种粮或者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办法进行消极反抗。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粮食总产量比战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天开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扩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全国17个省的大饥荒。
饥荒引发了遍及全国多个省的农民暴动。1920年冬天至1921年春天,乌克兰、俄罗斯东南及中部、′伏尔加河沿岸、西伯利亚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西伯利亚的伊施姆县参加暴动的农民达六万多人。
莫斯科东南方的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所产粮食一度销售到全国与欧洲,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20年夏天,坦波夫省的农民武装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仿效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1921年初,暴动者的人数达五万多人,暴动区域蔓延到相邻的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为了镇压农民暴动,苏俄政府派出了以图哈切夫斯基(后来的红军五大元帅之一)为司令员的部队进行围剿。苏维埃政府“反匪徒委员会”甚至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1921年8月22日,红军一个驻坦波夫省的炮兵旅就使用了82枚毒气弹。1921年9月,暴动被镇压平息。
1921年12月,全俄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找来萨马拉省的领导人安东诺夫询问:“你们省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说他们那里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安东诺夫回答说:“情况不仅仅是这样,人吃尸体的情况不仅仅只发生在那里。”“人吃尸体?!”列宁惊诧地说,立刻愤怒地指出:“(外国)武装干涉者要为此受到惩处!”当然,列宁同志不会提到武装粮食征集队。
这次大饥荒究竟造成多少人死亡,迄今尚无定论。1986年官方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造成一百万人死亡。苏联学者B.达尼洛夫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称,此次饥荒的死难者“有520万人”。
当时的苏俄政府借由作家高尔基发出呼吁,请求国际社会给予援助。
美国是最早作出回应的国家之一。1921年7月26日,美国救济署署长胡佛给高尔基回电说,美国可以向苏俄提供援助,条件是苏俄政府必须释放被关押在苏俄监狱的美国人。8月,两国达成协议,美国救济署可以派人到苏俄实施援助,但不得在苏俄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
美国救济署在苏俄的16个地区开展救济,截至1922年7月,共计将72万吨粮食和食品运抵苏俄。美国救济署还向饥民提供医疗服务,并为苏俄政府在国际市场代购粮食,发动国际援助机构向苏俄居民直接邮寄食品和物品;此外,还在苏俄境内开设免费食堂和物资发放站。1922年7月,胡佛给美国总统哈定的报告中说:美国救济署在苏俄开设了15700个食堂和物资发放站,向大约325万名儿童和530万名成人提供了食物。
高尔基在一封给胡佛署长的信中感激地指出:“……你们从死神那里夺回了350万名儿童和550万名成年人……在我所了解的人类灾难史中,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与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1922年秋天,苏俄的饥荒开始缓解。1923年2月,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及其招募的苏方工作人员人数从1.6万名减少到二千人。当年6月14日,美国救济署结束了将近两年的对苏俄饥民的赈济活动。
多年来一直看到苏联官方大肆鼓噪:西方帝国主义从苏联红色政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企图把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原来就是这么“扼杀”的吗?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36)
莫斯科一位市民丟了一只会说话还会骂人的鹦鹉,他很紧张:天知道它会在外面乱说些什么呢!要是引起克格勃的注意那就糟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去一家报社登了这么一则大字体广告:
“本人遗失一只会说话的鹦鹉。特此郑重声明: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
荀路2018年11月初稿
2020年5月29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