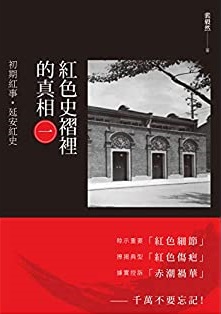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2)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12)
可敬又可怕的曾志
第一次知道陶铸之妻曾志(1911~1998),已是文革后期了。抄录陶铸那首〈赠曾志〉,感觉悲酸沉痛,摇撼心魄: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首尾二联写出陶铸被打倒后的心境与胸怀,直白明晓,深深嵌入我年轻的心。「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传递出陶铸自卑惊怯的心理,引我无限同情。此后三十年,我对曾志的了解也就停留于这一首诗。
2005年,从港刊看到曾志青年时代为厦门地下党筹措经费而卖子,有点不相信,认定反共势力造谣诬蔑。两年后,借来曾志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打开,便是曾志临终前一月的「前言」,一股红色女战士的劲头,无论价值观念还是为人准则,一泄无遗地凸露第一代共产主义战士的特质与局限,包括特别遗言「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1]。既可敬又可怕,而之所以可怕又来自可敬。
这一代共产红士确实「心底无私」、「彻底奉献」,境界确实崇高伟岸,奈何大方向错了,又因文化程度较低,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知自我奉献,无法自检自警,不知捍卫个人权利才是社会进步真正的内涵。因此,她的每一分「可敬」恰恰成为「可怕」的推力。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因「可敬」而「可怕」,更不知道由于着力方向与历史理性背反,她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只得到与初始意愿完全相悖的结果。阅读曾志,使我从细节处进一步了解中共革命的过程,同时也更清晰看到这场革命的种种局限,扼腕不已。
曾志在前言中写道:
我之所以幸存下来,不是什么「福大」、「命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靠刚强的斗争意志和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信三座大山一定能推翻,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同一定能成功……我始终将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最为重要,而把家庭、子女、感情看得较轻、较淡。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共产主义事业、三座大山、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同…… 历经夫死己辱的文革苦难,这位第一代中共党员仍带着一套完整的赤色意识形态去见了马克思,而且是毫无反思地带着70年前的认识最后走人。无论对杀伤55万知识精英的「反右」、摧毁国本的大跃进、打趴365万人的「反右倾」[2]、饿死4000万人的大饥荒,还是昏天暗地触及肌肤的十年内乱,这位文革后出任中组部副部长的老红军,晚年回忆录中没有一点反思。这本耗时二十余年撰写的回忆录,一如其青年时代认定「献身于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一股掩饰不住的光荣自豪。弥留之际,还惦记着「不要把我抬得太高!不要把我抬得太高!」[3]她最后担心的是有可能被「抬得太高」,而不是相反。事实上,进入二十一世纪,寰内士林之所以提及这位红女,并不是将她「抬得很高」,而是将她「贬得较低」。那股虽九死犹未悔的「红色典型性」——彻底将一生完全献给共产乌托邦,实在是不可能复制的红色石女。没有后来者的共产革命,谁还会去捧抬这么一朵「铿锵玫瑰」?
追溯这位井冈山女斗士缺乏反思的原因,只能归结于文化水平。毕竟,进行宏观思考需要一定理论能力。曾志15岁入党(1926年10月),正规学历只有初二——衡阳省立女三师肄业生,旋入衡阳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半年后毕业。衡阳女三师因校长教师「一片红」,出了许多革命女性。如后嫁朱德的萧贵莲(即伍若兰,1906~1929)、彭家四姐妹(号「彭家将」)、刘深、郭振怀、吴统莲、杨佩兰、李青、廖彩兰等。[4]曾志一生,长于行动短于学习。1940年初,曾志怀着攻读马列理论的强烈愿望进入延安马列学院,但是——
我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了,主要是脑子静不下来,也动不起来。一捧起书本,没看两页不是想睡觉就是心猿意马、思想开小差。……感到很枯燥、很累……这样学比行军打仗还艰难,常会冒出有劲使不上的喟叹,认为自己脑子不行了。有时也会冒出自己反正不搞理论研究,当一个实际工作者未尝不可的思想……三个月后,这一情况才有改变。这时,读书也读出些兴趣了,静得下心坐得住,自然也不打瞌睡了。[5]
十年文革,她被放逐,投闲置散,回忆录中也看不出阅读了什么书,估计她不会阅读有一定深度的理论著作。
首嫁夏明震
曾志一生三嫁,16岁首嫁夏明震(1906~1928,夏明翰同父异母弟),湖南省立三师生。夏明震死于湘南暴动。国军出动七个师「会剿」湘南暴动赤军。中共湘南特委执行省委指示——「阻止敌人打通湘粤大道」,提出坚壁清野、焚烧整座城市及湘粤大道两侧五公里以内的民房,片瓦不留。农民当然不干,一时民心惶惶。为安定民心,解释烧房原因,1928年3月21日上午,中共郴县县委于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一股乡民冲上主席台,当场杀了夏明震等九名中共头目,是为「郴州事变」。事变中,三百多名赤干被杀,千余百姓死伤。二十二岁的夏明震时任中共湘南特委书记。[6]
动员烧房大会上,夏明震被农民拖下台用梭标扎死,捅了几十刀,暴尸河滩。曾志出于「革命义愤」,亲手用大刀梭标杀死一名叛乱农民。[7]夏明震家共有四兄妹死于「土地革命时期」,其兄夏明翰死于1928年3月20日。[8]陶斯亮说夏家五兄妹捐躯革命。[9]湘南暴动欲烧城市及大道两旁五公里村庄,动员大会遭群众当场反抗,杀死县委全体,这一史实得到《谢觉哉日记》佐证。[10]
次嫁蔡协民
1928年4月,夏明震死后月余,17岁的曾志再嫁蔡协民(1901~1934),顶头上司,红七师党代表。两人性格不合,经常吵架。蔡酒后骂曾志三心二意,不真心爱他,将曾志照片撕得粉碎。1932年10月,曾志提出分手。蔡协民后因叛徒告密,被捕杀。
「卖子筹款」——曾志最经典的段子。1931年11月,她在福州生下与蔡协民的第二胎。鉴于井冈山生的第一胎送了老乡,曾母寄来四十大洋,嘱女儿这次千万送回家,她帮女儿抚婴。不久,蔡曾夫妇调职厦门。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来看他们。曾志说想送孩子回老家,王海萍百般劝阻。先说孩子太小,经不起旅途折腾;再说路程遥远,车船转换麻烦;又说来回两个多月,耽误工作;总之,不让曾志送子回乡。最后,王书记终吐实情。原来,蔡曾夫妇尚未到达厦门,厦门中心市委因急需经费,听说她刚生孩子,便替他们将孩子「送」给一位医生,收了人家一百大洋,此时已用得差不多了。
曾志回忆录中:
这哪是送?这是卖!这种事在今天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既然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送」走的孩子因两个多月就断了母奶,染上麻疹天花,很快死去。[11]
为党卖孩的事还不止曾志一例。1935年秋,中共河北省委因与上级失去联系,经费无着,只得一边紧缩机关开支,一边下乡斗地主搞粮食,一边再搞募捐,日子仍过不下去。省委书记高文华与负责经费的其妻贾琏,只得卖孩子以维持。
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头,男孩比女孩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四个月的儿子卖了50元大洋。这钱,分给王洋十元,李大章十元,解决吃饭问题。这50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三个月的生活。
孩子卖给河北省委秘书王林哥哥一位同事的姐姐,其夫为国军旅长。旅长讨小老婆不要发妻,发妻买来一男一女两婴防老。1949年后,高文华夫妇找过孩子,据说13岁时病死。[12]
再嫁陶铸
1933年初,22岁的曾志三嫁陶铸(1908~1969)。婚后,曾志长期不满这位第三任丈夫,多次打架。1941年,在延安生下女儿陶斯亮,陶铸不肯抚婴,曾志抱怨:
最让我生气的是星期天,他整天在李富春、陈云那里不回来,有时要到半夜才到家,其实也没什么正经八百的事,就是玩,去摆龙门阵。我难过极了,感情降到冰点以下。……打了一大架,两个人都打得鼻青脸肿,弄得左邻右舍都来劝解。后来有的同志说笑:「曾志,你真厉害,那一架打得那么凶,你一滴眼泪没有,象是满不在乎!」
革命者性格多热情冲动,敏感急躁。红色夫妻虽因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夫妻之间却少有「小资」的温柔细腻。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多次打吵。毛泽东向曾志诉苦:
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13]
贺子珍因此执意离开毛泽东,多次提出分手,客观上为江青腾出空位。
曾志嫁陶铸后仍有「花絮」。1933年5月18日,陶铸在上海亭子间被捕,关入南京大牢。此时,曾志在闽东「闹红」,特委组织部长,同时与宣传部长叶飞、游击队长任铁峰要好,遭组织处分。她晚年还抱怨:
当时我思想不通,为什么要我负主要责任?!只因为我是女人吗?我并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我认为恋爱是我的权利……我对叶飞是有好感的……当时,我与他们两人关系较好,工作之余较常来往……陶铸来信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做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14]
(抗战结束前)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到东北我们大家散多聚少,感情上一直未能真正修复。
这对革命夫妻差点分手。就是大好局面的1950年代,也一直吵架,直至1966年底陶铸临打倒前,曾志见陶铸处境极其艰难——
我和你的个性都太强,两人生活在一起,总要为一些事情争论不休,有时甚至吵得很凶,但是从今天起,我再也不同您争论了。[15]
红女难为妻
革命女性因高昂的革命斗志与钢铁决绝的性格,婚恋多不稳定,也不知道退让容忍。1949年初,北平「南下工作团」一位三十余岁的女指导员——
有两片说不破的嘴唇和满腹的「马列经纶」。她是四川籍的「长征」干部……有人说她嫁过四次,结果都离异了。[16]
1938年入党的「相府千金」孙铮,养成向党组织汇报思想的习惯。尤其在延安与华北的战争岁月,「哪怕芝麻绿豆也得找组织谈一谈,有什么想法从不闷在心里。」[17]另一位革命女性石澜,与大干部舒同(后为山东省委书记)生活四十年,始终以政治为婚姻地基。「我常常把在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和原则性带到家庭中,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感到家里跟社会上一样紧张,还不如不要这个家。但石澜越发现家中有矛盾,便越向组织上交矛盾。「对这些矛盾,我采取了错误的处理办法,向有关的组织写信控告他。这些信又被转到了舒同手中,舒同震怒了,向法院提出离婚。」石澜晚年才清醒过来,事情已无可挽回。[18]
曾志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可怕的「革命坚定性」。1926年底,湖南农运搞得城乡鸡飞狗跳,一片红色恐怖。15岁的曾志刚入衡阳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曾父拥地300余亩,当然「土豪劣绅」,逃往长沙途中路过衡阳,想看看女儿,但曾志——
我不想见他,给他写了封信,信中说「我现在是革命者,你逃避农民运动就是反对革命,我不能见你,以后也不承认你是我父亲。」
就是对女人最看重的爱情,她也无所谓:
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旧的思想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19]
坚持「毛崇拜」
文革中,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断然出手一并打倒阻碍「文革」的陶铸,陶铸惨遭折磨,死于1969年。曾志1998年才辞世,却一生都未走出「毛崇拜」,晚年仍问出十分幼稚的问题:
我内心深处总有种深深的惋惜:毛泽东英明一世,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搞这么一场天怒人怨的「文化大革命!?」
曾志甚至这样表明自己对毛的最后态度:
我的女儿总问我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么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这是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主席半个世纪,并不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我叹口气,对我女儿说:「不怨,主席晚年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20]
如此个人情绪化的逻辑起点,如此「肤浅」的思考态度,轻飘飘将毛归为「老人」、「病人」,叹一口气就放走了他必须承担的历史罪责,您那份为国为民的革命价值哪去了?坚定不移的革命原则哪去了?这是「一切为了人民」应有的态度么?反右~文革这样重大的国家灾难,就因为「所选择的信仰」与「指路人」便可原谅么?其智之弱、其志之低、其判之偏、其理之歪,实在匪夷所思。不过,曾志的「无悔无怨」确实十分典型地代表了第一代中共党人无法挣脱的历史局限。
当然,他们也一定明白十分「肤浅」的逻辑:原谅毛泽东等于原谅自己,反对毛泽东便会延及对「革命」的怀疑、就会使后代质问「方向」,很快就会质疑自己这一代「革命人生」的价值。毕竟,自己一生与毛泽东唇齿相依,无法剥离了。能够像李慎之、李锐这样具备反思能力且叛出朝歌,真正「大智大勇」的红色士子,极其稀少。
赤潮延绵
赤潮笼罩中华既久,总有几位「革命接班人」。女诗人柯岩(1929~ )为曾志回忆录作序:
看着他们,想着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先行者,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地安享由于他们的奉献而得来的一切吗?还能高高在上地挑剔指责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吗?……不妨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也处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我们肯像他们一样,只是为了后来人,而心甘情愿地、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吗?
这已不仅仅在剥夺对革命者历史局限性的认识权,而是剥夺了所有后人的评议权。因为革命者崇高的无私奉献,由于「我们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后人首先从道德上就丧失挑剔资格,而应自动认可革命,继承遗志,成为「红色后来人」。但是,革命者因崇高奉献就不受批评不受翻检,后人又如何从「历史局限」汲取经验教训?对革命者不能展开剖析批评,已缴纳的「革命学费」又如何转化为历史理性?对红色革命只能崇敬、只能「继承遗志」,又如何拨正赤潮架设的左倾歪理?如何从根子上认识历史偏误?更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仅仅因为「无私牺牲」就能得到绝对膜拜,那么「九·一一」恐怖分子的献身精神一点也不比红色烈士掉份。恐怖分子看来,他们的牺牲不仅仅宣倡「主义」,也在拯救整个伊斯兰。
小柯阿姨这段十分煽情的文字,包涵了十分典型的左倾偏误:「阶级感情」代替历史理性,被赤潮领歪道道,中了左倾套套——以「崇高牺牲」换取对赤色革命的认同,以手段壮烈证明目的崇高。事实证明:方向错误的「崇高牺牲」不仅不能无原则膜拜,还应特别警惕——因为它裹带特殊幻力。
很清楚了:牺牲的意义必须系于目标之正确,崇高牺牲绝不自动证明目的之伟大;手段越激烈越极端,目的大半越偏离理性。以号召彻底奉献生命的革命,能有多少理性成分?一切都奉献完了,个人什么都不得保留不能捍卫,人权、自由、民主还有什么价值?还需要这些东西么——既然生命本身都没多少意义!曾志以自觉交出各项生命权利而自傲,一旦脱党,失去组织,便感觉生命没了意义。政治第一,生命第二,曾志不可动摇的价值顺序,晚年仍说:
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等于失去了政治生命,没有了政治生命,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21]
陶斯亮评母:
一生追求崇高却又甘于平凡……您会为我们买了一元钱的时令菜而大为生气,却将自己一生的积蓄捐给了社会。[22]
曾志确实做到无私奉献、绝对忠党、终生努力,真正的红色战士,但她与数代真诚中共党人一样,一生悲剧无法挽回。因为,他们的努力乃是南辕北辙,彻底走错了路。史实证明:她给错方向的热情,浇出「毛时代」的恶花恶草;给错方向的努力,只能走向愿望的反面。晚年曾志不愿承认这一点,既有情感因素,更多的还是认识能力所囿。
笔者接触的资料中,第一代中共党人几无稍有份量的反思者,哪怕一段略有深度的反思文字都没有。徐向前晚年认为一生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十分骄傲。只是,红色革命的意义并不取决革命者的自我判认,必须接受历史检验,需要后人认同。没有继承的革命,当然不可能「万万岁」。至于共产主义事业是否伟大,是否对人类历史具有正面作用,有着苏联东欧人民的选择、有着中越蒙柬等国不得不进行的转型改革,有着朝鲜、古巴因坚持马列原教旨而仍在持续贫穷,一切还需要辩论吗?还需要大段论证吗?
1990年代逐渐响起来的「告别革命」,当然是对二十世纪赤色革命的总结性认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走向光辉彼岸,而是完全走向反面——经济长期贫穷、政治专制暴烈。「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因为所有无产阶级都想成为资产阶级,而非希望终身保持无产阶级「光荣称号」。赤色革命只是裹着新名词的又一场叛乱夺权——挑动族群斗争、破坏社会稳定。
一位女教授读拙文后,认为对曾志应在「可敬」、「可怕」之后,再加上「可悲」、「可怜」、「可恨」——可悲她一生的遭遇、可怜她的至死不悟、可恨她卖掉自己的孩子。
初稿:2007-10-27;略增补。
[1] 陶斯亮:〈致母亲——白云山上的祭文〉,载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584。
[2]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29~232。
[3] 陶斯亮:〈致母亲——白云山上的祭文〉,载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583。
[4]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8年,上卷,页127、139。
[5]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321~322。
[6]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8年,页174。陶斯亮说夏明震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党代表。陶斯亮:〈曾志与夏明震〉,原《南方周末》(广州)2008年6月26日,《文摘报》(北京)2008年7月10日。
[7]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册,页57~58。
[8] 汤益民:〈夏明翰就义八十周年祭〉,《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5期,页44。
[9] 陶斯亮:〈曾志与夏明震〉,《南方周末》(广州)2008年6月26日。
[10]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页560。
[11]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册,页125~126。
[12] 高文华:〈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一辑,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74~175。
[13]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327~329。
[14]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册,页207~208。
[15]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398、443。
[16] 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中央文物供应社(台北)1956年12月第5年,页13。
[17] 黄仁柯:《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266。
[18] 石澜:《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52。
[19]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册,页42、65。
[20]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534~535。
[21]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上册,页4、228。
[22]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584。
原载:《开放》(香港)2008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