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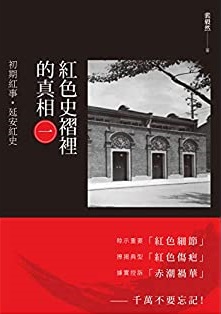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延安一怪冼星海
一曲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使冼星海名垂乐史,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跻身「延安四怪」。其他三怪:长发披肩与众不同的演员塞克(1906~1988,河北霸县人)、狂放不羁独往独来的作家萧军(1907~1988,辽宁义县人)、暴躁激烈易于犯上的译家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冼星海的「怪」是要求保证他吃鸡吃糖,否则无法作曲。
艰难求学
冼星海(1905~1945),生于澳门贫苦渔家,父亲在他出生前半年就去世了,但为遗腹子取了一个十分诗意的名字:星海。冼母投靠澳门娘家,1911年母子漂泊至新加坡。按说,如此家境不可能培育出音乐天才。
冼母洗衣帮佣,咬牙供儿上学。先入英人开办之校学英语,再入华侨小学、中学,修习汉语,打下中英文基础。此后,冼星海入岭南大学新加坡分校——养正中学附小,得到最初的音乐训练。1918年回粤,入读广州岭南大学附属义学。1919年以优秀侨生被岭大附中录取,后升岭大预科,师生誉为「南国箫手」。这一阶段,冼星海的音乐天才得到长足发展。他参加学校乐队,演奏小提琴和单簧管,并任指挥。1926年秋,冼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专攻小提琴,同时兼职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以维持生活。1928年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结识田汉,参加「南国社」戏剧活动。1929年夏,冼星海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10月,他克服经济上种种困难,靠朋友帮助上船做苦工,免费渡海赴法,他要圆自己的梦想——入学全球音乐最高殿堂。
最初几年,他在巴黎一家「北京饭馆」跑堂打杂、拉琴助餐,以维持生活,还忍辱在咖啡馆、大餐厅拉琴讨钱。他住在贫民窟最高层狭小房间,无法直身,练琴只得钻出小门上阳台。冬天取暖,得上街跑步。他先找到P·奥别多菲尔(Paul Oberdoeifer)学小提琴,再从路爱日·加隆(Noel Geallon)学作曲理论。怜悯其贫,两位老师均免掉每月学费200法郎(合十块国币)。这一时期,他失业十余次,经常饿瘫街头。一对白俄苦工夫妇伸出援手,经常请他吃饭。
这一段艰苦求学,冼星海描述:
我常常在失业与饥饿中,而且求救无门……在繁重琐屑的工作里,只能在忙里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提琴、看看谱、练习写曲。但是时间都不能固定,除了上课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想法去上课外,有时在晚上能够在厨房里学习提琴就好了,最糟的有时一早五点钟起来,直做到晚上12点钟。有一次,因为白天上课弄得很累,回来又一直做到晚上九点钟,最后一次端菜上楼时,因为晕眩连人带菜都摔倒,挨了一顿骂之后,第二天就被开除了……我失过十几次业,饿饭,找不到住处,一切困难问题都遇到过。有几次又冷又饿,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软瘫下来了……有过好几天,饿得快死,没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馆、大餐馆中去拉奏讨钱。忍着羞辱拉了整天得不到多少钱,回到寓所不觉痛哭起来,把钱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来。门外房东在敲门要房金,只好把讨到的钱给他,否则就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险(其实,如不是为了学习,倒是个活路)。有一次讨钱的时候,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颊,说我丢中国人的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忿抑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里不禁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怎样去挽救祖国危亡的思念。[1]
就在这样的痛苦煎熬中,1931年春,冼星海成功创作了〈风〉。这首曲子得到老师们的赞誉。凭借实力,经人介绍,冼星海结识了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并终于圆梦,考入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当时,在那里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只有冼星海一人考入该班,并获得荣誉奖。学校问他需要什么奖项,他答曰:「饭票」。于是,学校送给他一叠饭票。1935年5月,杜卡教授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结束高级作曲班的学习,加上他急于回国探母,在友人帮助下,再次搭乘免费货船回国。留法五年半,冼星海掌握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丰富了音乐修养,开阔了艺术视野,成为他走向艺术巅峰的重要台阶。
抗日作曲家
回国后,冼星海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新华电影公司担任配乐,为《夜半歌声》等影片配曲,同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冼星海和洪深、金山、王莹等组织上海救亡演剧二队,1937年12月抵达武汉,一路相继创作了〈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曲。
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这首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救国军歌〉,堪称抗日救亡第一歌,传唱最广影响最久的抗战歌曲。1936年夏初,塞克晚饭后独自走在昏暗马路上,走着走着,不由自主迈出军人步伐。他意识到:应该写一首抗日军歌。想到内战未息,于是,「枪口对外」成了第一句歌词,接着抗战必胜、中华民族必然解放,「永作自由人」迅速跃出,成为全歌词眼。回到住处,趁热打铁,塞克完成〈救国军歌〉歌词。第二天,塞克拿着歌词,去冼星海处,将歌词向冼星海面前一扔,点上最后一支香烟,将空烟盒也扔在冼星海桌上。冼星海端着饭碗看了一遍歌词,连声叫好,顾不上寻找铅笔橡皮和五线谱纸,立即掏出随身钢笔,顺手拆开塞克弃扔的烟盒,一边吃饭,一边用鼻子哼旋律,不时用筷子敲击碗边打节奏,又不时停下来在烟盒纸上记些什么。就这样,塞克抽完一支烟,冼星海就谱完曲子——仅用五六分钟!一支风靡全国的抗战名歌就这么产生了。
1937年9月,冼星海首次听到延安这一地名。1938年3月4日,他日记中:
今天闷得很,把《抗战中的延安》读过一次就感到很兴奋。看他们一班革命青年在节衣缩食去干革命工作,不断寻求真理和民族的解放!我们虽然在后方,可是比起他们就觉得惭愧得多!我怕自己会渐渐落后而大不前进。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祥地。[2]
延安岁月
1938年9月底,经周恩来过问,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转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沙可夫院长的聘书,以及全系师生集体签名的附信,聘请冼星海赴延任教(鲁艺音乐系主任)。正在犹豫不决,此时已有传言:
听说什么都好,就是没有自由。
一切听组织分配,不准有个人志愿。
进去了就不能出来,还必须参加共产党。[3]
两封延安催电又至,他问明提供自由创作环境及自由出入,10月初携新婚妻子钱韵玲(经济学家钱亦石之女)赴延,11月3日抵达。1939年5月15日递交入党申请书,6月14日加入中共。
1938年11月~1940年5月,冼星海生活在延安,一生创作的巅峰期,写出〈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声乐套曲在内的百余首作品。不过,音乐家冼星海内心激情似火,外表却近于木讷,拙于言辞。到延安后,入住窑洞倒还没什么,吃小米却「没有味道,粗糙,还杂着壳,我吃一碗就吃不下了。以后吃了很久才吃惯。」毕竟留法六年的洋学生,如此简单粗糙的生活,一时难以适应。他的思维定势与生活习惯亦与周边环境不时发生冲突,尤其对频繁开会不甚习惯,白耽误时间。而且,全延安没一架钢琴,只有「轻武器」——提琴、手风琴及一些中式乐器。有时,因无处发泄,竟将隔壁飞来的小鸡打得满屋乱飞,他负气地对人说:「保证我吃鸡,否则一行旋律也写不出。」
但他很快被「改造」过来,不仅吃出小米的香,还慢慢习惯了开会、听报告,甚至有点爱上政治学习。他写信给田汉:「已彻底摈弃了『为艺术而艺术』」。1940年3月21日,他给一位友人写了长信,这就是冼星海十分珍贵的一份自传。据此信可知,冼星海在延安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三元),其他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
1938年延安津贴标准:士兵(班长)一元、排长二元、连长三元、营长四元、团长以上一律五元,毛泽东、朱德也是五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四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十元。[4]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发的是延安「边币」,一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支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5]也有人记述:
每人每月发一元边币,只能够买一把牙刷一包牙粉,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6]
冼星海的优待级别已是最高规格。不过,艺术创造需要燃烧热情,而热情燃烧确实离不开充沛体力,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难以支持创造所需激情。因此,「冼星海吃鸡」并非「小资」情调发作,而是工作需要。「吃鸡」较之〈黄河大合唱〉有可比性么?奈何延安物质条件太差,「吃鸡」方成一怪。
黄河大合唱
1939年2月18日除夕夜,冼星海受邀来到延安西北旅社一间宽敞窑洞,与第二战区抗敌演剧三队聚集一堂,聆听三队诗人光未然的新作〈黄河大合唱〉。这首大型组诗来自诗人两渡黄河及在黄河两岸行军打仗的亲身感受。400多行的诗句,26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全窑洞听众的心脉随着抑扬顿挫的诗句跳动,最后一句「向着全世界劳动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一片寂静。顷刻,掌声爆响。冼星海一直坐在靠门边,霍然大步上前,一把抓过诗稿:「我有把握把它谱好!我一定及时为你们赶出来!」一窑洞的人报以热烈掌声。
为了创作好〈黄河大合唱〉,冼星海没急着动笔,用了近一月时间向光未然与三队演职员详尽了解抢渡黄河的情形以及船工号子,默默酝酿。1939年3月26~31日,六天六夜,冼星海不间断地完成〈黄河大合唱〉谱曲,一共八首,包括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创作前,延安吃鸡不易,冼星海退而求其次,要求吃糖。冼喜爱甜食,要求光未然为「作曲」买两斤白糖。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上,开始创作。他一边撮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拔去笔尖的毛竹笔竿)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黄豆粉拌红糖)。就这样,在延安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激昂狂野又婉转抒情的乐章。音乐界认为二十世纪中国音乐能够传世的只有「两首曲子一首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二胡独奏曲〈二泉映月〉,一首歌便是〈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的音乐特点为中西结合,铺入晋陕民歌及古曲〈满江红〉音型,气势雄伟布局庞大,音乐与歌词浑然一体,山呼海啸的黄河怒涛奔涌出中华民族磅礴的抗战力量。一位诗人说:「从歌声中可以听出一个民族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它所依托的抗战背景,表现出中华民族的雄厚伟力与必胜信心。
1939年4月13日,抗战演剧三队和「鲁艺」音乐系乐队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首演,观众千余。冼星海亲自指导,光未然亲任朗诵,男声独唱田冲,女声独唱蒋旨暇,二重唱史鉴、刘晨暄。演出非常成功,轰动延安。1939年5月11日,毛泽东也听了〈黄河大合唱〉,连声称好,单独邀见冼星海。当毛泽东从鲁艺副院长赵毅敏处获知冼星海在创作中用坏不少蘸水笔,特赠冼星海一支派克钢笔与一瓶派克墨水(老外送毛的延安稀罕货)。李富春设法解决了冼星海的吃糖问题,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专门拨一孔窑洞给冼星海,配备一名通讯员照顾冼星海生活,并送来一筐蜡烛,供他夜间创作。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在延安迅速传唱。冼星海被各单位请去教唱和指挥〈黄河大合唱〉,经常忙得回不了家,不久任命鲁艺音乐系主任。〈黄河大合唱〉一直作为延安各种演出和晚会的保留节目,专门招待国共将领、民间团体及外国宾客,如国民党元老张继、侨领陈嘉庚、作家老舍茅盾、美国军事考察团、马歇尔将军等。
另一支抗战名曲〈生产运动大合唱〉,也是冼星海与塞克合作。1939年春,延安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塞克在延河边散步,人来人往的大生产繁忙景象,深深触动了他。恰巧,就在这段时间冼星海多次向他索要歌词,并专门嘱咐写一些「厉害的」。塞克眼前忽然一亮:大生产运动,支援抗战,不是很有意义很「厉害」么?于是,塞克决定写一部反映大生产运动的大合唱,当即在延河边构思。没几天,塞克完成腹稿。一天早饭后,塞克关起门,进入写作状态。掌灯时分,一部多场〈生产运动大合唱〉脚本一气呵成。冼星海早在盼望塞克的歌词,拿到脚本后,3月1日投入封闭式创作。白天,他闭门谢客;晚饭后,和塞克一起到东山或窑洞前散步,切磋作品。〈生产运动大合唱〉冼星海也仅用六天谱写完毕。1939年3月21日,冼星海亲自指挥,陕北公学大礼堂,鲁艺师生举行首演,获得成功。
最后岁月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为激励军民英勇抗战,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延安首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导演袁牧之点名要冼星海配乐。当时延安电影器材十分落后,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秘赴苏,完成影片后期制作,同时接洽购买先进的苏联电影设备。毛泽东请客送行,11月到达莫斯科。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无法为战争效力,便想回国。但新疆军阀盛世才这时与赤俄、中共翻脸,共方人员无法经由新疆返国。
1941年9月,冼星海一行离开战乱中的莫斯科,到达蒙古,准备回国。然受阻于国境线,只得在乌兰巴托流浪。1942年12月9日,他辗转至阿拉木图,化名「黄训」(赴苏后用名,母姓),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哈萨克音乐界朋友,摆脱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重燃创作热情,经常出席各种音乐会,并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当地民歌。他以敏捷乐思将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还创作了一系列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交响乐,如〈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并撰写〈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
1944年1月30日,冼星海来到哈萨克斯坦的库斯坦奈州,入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
生活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经常还要断顿。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等到月底才能领到一些,即使领得也只够三四天吃。
这时,他不仅肺部有结核,还有肝肿、腹膜炎和心脏病,每天上医院抽出好几立升腹水。二战快结束时,冼星海被送至莫斯科。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找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李立三。李立三将重病的冼星海接到家中。
战争尚未结束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奇缺,李立三的住房也相当困难。更要命的是:李立三在苏联大肃反时期下狱,1939年11月4日「死里逃生」获释,但停止党籍,成为莫斯科无国籍游民。原来居住的共产国际宿舍,早被他人占用,只得挤在俄籍妻子娘家。「当时哪一家也不宽敞,有幸住单元房的人寥寥无几。」岳母家也只有一间约30平米的屋子,当中拉一幅白帘,一边是李莎(李妻)的嫂侄,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添女儿英娜。本已拥挤不堪,再把冼星海夫妇接进来,难上加难。李立三与家人商量后:把床铺让给冼星海夫妇,自己睡地铺。李立三夫妇不仅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配给,日夜奔走,难得安宁。
一个多月后,在李立三的奔波下,总算得到斯大林批示,在苏联国际救济总会帮助下,冼星海入住克里姆林宫医院,李立三夫妇经常前往看望照料。由于所患严重血癌,沉疴积疾,医生回天无力,但未告知病况实情。此时,冼星海虽形同枯槁,颧骨凸出,仍满怀信心,憧憬未来:
中国的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在祖国首都建立音乐学院,培养高级音乐人才。我想象中,音乐学院将是一座宽敞漂亮的大楼,大理石的阶梯,墙上有明亮的大镜子,像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殿堂。
四个多月后,1945年10月30日,冼星海病逝,年仅40岁。李立三夫妇帮着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为冼星海举行隆重葬礼。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苏联著名音乐家穆拉杰利。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公墓,骨灰盛放于灰色大理石小匣,匣子正中镶着一张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缎制花束,下刻金色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1980年代,经反复交流,冼星海遗孀专程赴俄,迎回骨灰盒。[7]
资料来源:
马可:《冼星海传》(附录冼星海「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秦启明:《冼星海》,长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与2006级硕士生孙晓丹合作)
[1] 马可:《冼星海传》,人民文学出版(北京)1980年,页252。
[2] 紫卉:〈《黄河大合唱》的两部手稿档案〉,《档案春秋》(上海)2006年第9期,页2。
[3] 马可:《冼星海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243。
[4]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21。
[5]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43。
[6] 苏一平:〈延安西北文工团的闪光足迹〉(节选),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44。
[7] 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英男、姜涛编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102、133~134。
初稿:2007-7上旬,补充:2009-6-9
原载:《世纪》(上海)2010年第4期
转载:《新民晚报》(上海)2010-8-14
《报刊文摘》(上海)2010-7-16;《文摘报》(北京)2010-8-21
《湖南工人报》(长沙)2012-8-15;
《文史博览》(长沙)2012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