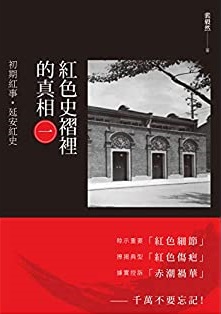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9)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二辑:延安红史(9)
延安文化人的生活
一、军事共产主义
延安生活沿袭南方苏区军事共产主义,以资历为据,稍作区别,级差甚微,男女无别,追求人人平等的价值理念。每一场「革命」的发动阶段都会提出高于既有政权的道德标准。海伦·斯诺描绘:
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最原始的共产主义,平分了又平分,一直分到原子。……「各尽所能——各取最低需要」。 [1]
延安官兵级差微弱。据艾青(1910~1996)、卞之琳(1910~2000)提供资料,1938年津贴标准:士兵(包括班长)一元、排长二元、连长三元、营长四元、团长以上一律五元,毛泽东、朱德也是五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十元。1940年代初期,延安经济困难,高知待遇降下来。中央研究院的范文澜、艾思奇、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虽略低于朱、毛的5元,但高于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4元。徐懋庸(1911~1977)兼一点「鲁艺」课程,每月另有5元津贴,加上稿费,「所以,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2]
特权当然存在,只是较隐性。如按延安物价,哈德门牌香烟三~四角/盒,毛泽东每月抽烟就得百多块钱,自己付不起的,得靠公家发。[3]1938年1月,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长谈六夜(晚饭后自黎明),毛泽东给梁漱溟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4]
访延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1885~1970):
像贺龙这样的师长,每月的工资为中国币五元,朱德为六元,折合成美金连两个美元都不到,只抵得上其他中国指挥官通常工资的一个少得可怜的零头。[5]
胡乔木:
当时国民党的县长月工资为180元,边区的县长津贴仅二元,边区政府主席的月津贴也不过五元。[6]
阎锡山的晋军,士兵月饷11元法币、少尉24元、中尉33元、少校96元,升官确实带着发财。[7] 1939年,国军士兵月饷八元。[8] 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短评:国民党上将月薪1.6万元法币,中将1.1万,少将八千,一等兵55元,二等兵50元(只能买最劣香烟三四包、火柴五六盒),最高与最低相差320∶1。[9] 中共的「官兵平等」,确具可比性。
延安生活虽苦,但对中共党员来说,安全感第一位。地下工作者曾志(1911~1998),抵达延安后的感觉:
不但有安全感,而且精神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都是很富足的。作为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对延安的体验可能是与众不同的。[10]
曾志不仅得到安全感且感觉舒适,并不认为延安生活有什么艰苦。不过,这只是地下工作者的感受。对绝大多数来自城镇的赴延知青来说,延安生活还是十分艰苦。
1936年8月,斯诺记述:
在这里陕甘边区,人们就像五千年前他们祖先那样生活在这黄土群山里。男人蓄发梳辫,妇女全都裹足。他们难得洗澡。据说陕西老乡一生只干净过两次:结婚喜日他自己洗一次澡,再就是出殡那天别人帮他洗。[11]
1938年3月,《扫荡报》记者原景信从西安赴延:
(一路上)既少村庄,又乏人烟,荒凉得不堪入目!……种的是山坡,住的是破窑,吃的是小米。窑洞就是原始人住的「穴」,又黑又臭。……人民生活表面上虽比原始人好一些,但个个有菜色,实际上却还不如原始人![12]
抗战初期,延安赤区辖地26个县(后缩至23县,1944年扩至30县一巿)[13],面积12.9万余平方公里,地广人稀,人口150万(一说135万)[14],另有资料仅50万[15]。1936年7月9日,周恩来对斯诺抱怨:
在江西和福建,大家都带着铺盖卷来参加红军,这里他们连双筷子都不带,他们真是一贫如洗。[16]
环境卫生更是原始简陋,远离文明。「窝窝头上叮满苍蝇,坑上满是跳蚤,被子缝里挤着虱子,在这种环境,你就需要吃得下、躺得下的勇气和毅力。」大生产运动掀起后,种菜必须与粪便打交道,「半天下来,任凭你怎么洗,端饭碗的手都是臭烘烘的。」[17] 延安饭铺「醉仙楼」(全城共两家),「停留在菜刀上的苍蝇,多到好像铺上层黑布。」[18]
赴延路上,「一路投宿,几乎没有一家客栈没有臭虫跳蚤蚊子。」[19]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20] 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
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21]
丁玲(1904~1986)纪实小说〈在医院中〉,记述了老鼠溜迈被头的细节。[22]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咱们还是『共产』吧!」,一摔分四,扩增利用率。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23]
入学陕北,各校学生第一课——挖窑洞,解决栖身之所,木窗木门,连根钉子都没有,整个窑洞没有一片金属,玻璃更是奢侈品,只有后来美军联络组的窑洞才有。[24]上课、吃饭、开会都在室外,所幸陕北少雨。李维汉:
同学们说陕公的室内活动就是睡觉,确是如此。冬天,空中飘着雪花,教员头顶雪花上课;雨天,泥泞满地,教员赤脚上课。数九寒天吃饭,饭凉菜冻,若遇上狂风,饭菜里还要掺杂点沙尘、草芥。课桌课椅是没有的。学员的被子一物两用,白天捆起来当坐凳,晚上打开睡觉。以后在露天广场用石头、泥块砌一些坐墩,算是小小的改善了。[25]
鲁艺情况也差不多,教员沙汀(1904~1992):
没有固定的教室,一般都头上戴顶草帽,在露天里上课。遇到落雨,就挤在一眼较为宽敞的窑洞里进行学习。同学们一般只有用三块木板做成的简易矮凳,双腿上则放块较大的木板,权当书桌。[26]
文学系学员穆青(1921~2003):
我们每周只上几次课,一般学习都在露天,冬天找块太阳地,夏天躲到阴凉地。大家一人一个小板凳,走到哪儿搬到哪儿,膝盖就是「自备」书桌。[27]
抗战初期,延安知青吃小米蔬菜、穿土布蹬草鞋,一周才能吃一次面条或饺子。1939年6月,中国女大「400多名学生只有一只篮球,书籍和药品也非常缺乏。」[28]陕公早晨四人共享一盆洗脸水,三餐小米,四人合吃一铁盒土豆或南瓜。[29] 燕京生、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黄华(1913~2007,后为外长):
伙食很简单:小米饭和七八个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萝卜,偶然有一两片土豆。[30]
落实到人的定额具体为「每人每天一斤粮(高粱粗小米,只能喝稀饭),二钱盐,三钱油。」[31]南方「资产阶级小姐」长吃小米可就受罪了,她们抱怨:
过去在家时,这都是喂小鸟儿的。
嚼啊嚼啊,唾沫都咽干了,怎么也归不拢。
有的半年多肠胃都无法适应:
到延安后半年多还是不适应,吃了小米饭大便不通,憋死了。[32]
一位粤籍女生:
我们这些由祖国南端而来到北国的女青年,由于气候、环境、饮食的巨大变化,一月三次月经来潮,举步维艰。当时月经使用的粗草纸,把皮肤都擦破了。[33]
睡也是大问题。陕公、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大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收复失地」。[34] 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直腿挺睡。延安保育小学,「我们一个窑洞要挤十几个人,睡在一个大通铺上,夜里翻身都喊『一二』,一齐动作,否则是翻不动的。」[35]相比京津沪穗城市生活,相隔天壤。一些赴延青年悄然离延,转去川渝。[36]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
每一种教育进行两个小时,往往第一小时上课,第二小时讨论、学习或休息。睡觉的时间相当长,这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口粮的不足。饭是小米饭或馒头加一些蔬菜,但是一天只有两顿。[37]
平均主义的供给制,体现了人人都是「革命螺丝钉」,苏联的共产国际称为「蓝布蚂蚁群」、「红色工蜂群」,对改造有棱有角的个人主义大有裨益,非常有利于加强组织纪律性。这一延安经验成为日后「大跃进」的历史根据。1958年8月21日,「大跃进」进入高潮,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延安经验说:
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作风来贬低我们,结果是发展了个人主义;建议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1958年8月31日,毛泽东又针对供给制与薪给制发表看法,不同意平均主义会出懒汉的说法:
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有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十分清楚供给制的政治效用,故以政治挂帅为旗号要求恢复供给制。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巡视山东历城县北园乡,对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说:人民公社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毛巡视山东,特意点明这句话,置引题醒目处。[38]
军事共产主义是延安文化人生活的社会天幕,对1949年后国史走向影响甚巨。对延安文化人来说,则从价值方向、经济可能等各个方面,从形而上至形而下全方位规定了延安文艺的质量,也是研究延安文化人有趣且有核的一处「观景亭」。
二、延安物价
抗战前期,物价尚低。何满子(1919~2009),1938年入武汉《大汉晚报》,月薪40元,「至少可以解决生活问题了。」1940年,何满子在成都编《黄埔日报》「血花」副刊,以少校速记员开薪80元∕月,可负担一位失业朋友的生活费;所编副刊稿费千字两元,每月掌握约300元稿费,都甚至想用这笔钱自办一份32开小型张刊物。[39]1939年10月的河南洛阳地面,物价之低廉让走南闯北的曾志终身难忘:
我对河南小摊小铺价格之低印象很深。一大碗面条,一碟咸菜,加住宿一夜,只要两毛钱。糊辣汤在这一带很有名,无论到哪里都有卖的,一汤碗糊辣汤加四个油炸馓子只要五分钱。一毛钱买一碟熟驴肉(约三两重),两毛钱买三四斤煮熟的花生。这些价格比起湖北襄樊来要便宜许多,但也说明这里的消费水平低,群众生活较苦。[40]
1936年8月,陕甘宁赤区甘肃地界一只鸡二角钱,一头猪一元,一头羊三元。老乡用这些牲畜换钱买食盐、棉布、大烟。除此之外,钞票就毫无价值了。[41]
1938年,山西汾阳东南一带,八路军团长杨得志(1911~1994)请带路老乡买一块钱鸡蛋,竟买来二十斤。一位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高小毕业的俊姑娘,两头都愿意,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一百块钱彩礼,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人家不干。杨得志后升旅长,过汾河前,还想带走这位姑娘,「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42] 此时币值还相当坚挺。
1937年4月,雇请瞿秋白赴俄采访的俞颂华(1893~1947),以《申报》记者身分采访肤施(延安),记载所见:
愈是往北,人民的生活愈是苦。当地的人以灰色的面条或馍馍和以红的辣椒酱及灰色的盐果腹。吃不起面的人,即以山芋或小米当饭。我们在路上常常以鸡蛋充饥。那边鸡蛋尚不贵,且到处可买,一角大洋可买六枚煮熟的。[43]
延安物价也很低廉,猪肉每斤二角,一角可买十来个鸡蛋。[44]陈明远(1941~ )折算延安一元相当1990年代末30~35元人民币。[45]若按相对标准,至少合2008年人民币百元以上。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沿袭江西苏区标准:贪污500元以上枪毙。[46]
曾志记述的延安物价还要便宜:
延安的群众很少种菜,也不太会种菜。可是大路菜,例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都还容易买到,就是猪肉、鸡蛋之类也并不缺,还便宜。一斤猪肉就两角钱。延安人还有个习惯,不吃「猪下水」,因此猪的肝、心、肺、肠、肚就尤其价贱。[47]
于光远回忆延安文化沟口「胜利食堂」,只摆得开两三桌,烹饪水平亦仅相当北京街头小饭馆,已是延安最高档次饭店。几十年后,于光远还津津有味记得那里一道甜食「三不粘」——不粘碗、不粘筷、不粘嘴。「三不粘」乃传袭至今的延安名点——油炸鸡蛋羹,鸡蛋、面粉、白糖、食油炸制而成。[48]
像如今涉外宾馆一样,延安也内外有别,涉外物价甚高。1938年3月下旬访延的武汉记者原景信,入住中华旅社,小小一屋,一半泥炕,挤睡五六人,每晚收费四角;用餐,一盘菜三角,一碗汤三角。
如果每顿吃一个菜,一个汤,一盘面条,几个馒头,差不多就需一块大洋。来延安的大多是文人,文人的钱多半是绞脑汁换来,被这样的剥削,实在有点不甘心。所以每顿饭吃完的时候,大家总爱说一句:「县太爷的一月薪金,又被我们一顿吃光了!」但旅馆老板回报的,却是一阵得意的微笑!
脚夫,八路军每天只须给中华旅社伙食费三角∕人,穿绿军装的国军就得给三元∕人。[49]
三、延安稿酬
江西苏区也有稿酬。创刊1931年底的《红色中华》乃赤区政府机关报,发行量最大。1931年12月18日《红色中华》第二期刊登征稿启事,欢迎论文、时评、社会调查、各项新闻等稿件,要求「通俗简明」,一经发表「从优酬谢」,每篇稿费「二毛至一元不等」。[50] 延安时期,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的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危拱之(1905~1973,叶剑英妻),1936年6月3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布「征求剧本启事」:
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齣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共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红一方面军各部发出征稿电报与信函,希望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实况。征稿信曰:「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1936年10月28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
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十周年,并组建了11人的强大编委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通知明确:「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此书后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1942年11月出版。
1940年4月15日,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大众文艺》创刊,毛泽东题写刊名,萧三主编,第一期刊登稿约:「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的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毛泽东题写刊名,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创刊号「约稿」:
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博古社长,毛泽东题写报名与发刊词,「创刊号」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
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
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
这则启事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
1941年前,钱物稿酬并存,之后多为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要严格登记。人们写稿一张纸两面写字。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了,周边羡慕不已。写稿得「物酬」,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还有的物酬为赠送书刊,以刊为酬。1940年9月创刊的《歌曲月刊》「稿约」:「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该刊约为2~5角∕册。 [51]
延安早期油印刊物基本无稿费,赠送一份当期刊物为酬。后来的铅印报刊才支付稿酬。1941年物价飞涨前,稿酬标准大体为1元/千字。也有铅印刊物不给稿酬的,如《文艺突击》。[52] 1939年初,毛泽东委托边区教育厅长周扬参与《陕甘宁边区实录》编纂:「备有稿酬(每千字一元五角)」。[53]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54]明显表示出政治价值对稿酬的调节。
还有特殊稿酬。1943年,鲁艺秧歌剧〈兄妹开荒〉演遍延安,中央党校几位炊事员托人给演员送来两双袜子、两条毛巾、两块洗衣皂——
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这是由于炊事员工作的特殊需要专门发给他们的,他们舍不得用,送给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感动得都哭了。[55]
1941年延安出版物60余种,整风后1943年只剩三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面向文化程度很低者的《边区群众报》(西北局机关报,常用字仅四百,发行量万余)[56]、仅供一定级别干部的《参考消息》,其他出版物均须经中宣部审查。《解放日报》不仅成为唯一信息来源,还提供「最标准」的思想观点。每天下午16~17时,从中央到基层都派通讯员去领报,清凉山下的《解放日报》社十分繁闹,领报回来的通讯员成为最受欢迎的人。[57] 级别化《参考消息》的出现,标志性地说明延安开始控制信息,延安知识分子只能读到《解放日报》,信息统一化的同时必然伴随思想封闭化,这一重大拐点的出现,当然十分典型地说明「延安雏型」的许多内涵。
延安作家的驰骋之地十分狭促,文艺稿只有一家去处——《解放日报》第四版副刊,稿费二升小米/千字。这点「稿费」相对延安作家当时的供给制收入,不无小补。《解放日报》发行七千余份,延安影响最大的媒体。1944年6月访延的重庆记者赵超构,如此评价《解放日报》四版编辑艾思奇:「他既然掌握着延安文坛的天秤,我们就无从否认他的权威。」[58]
四、稿费用途
延安文化人得了稿费,多与人分享,或被朋友「共产」,独自享用者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如「小气」,会受讥嘲非议。延安诗人卞之琳回忆:
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
《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
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
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周立波、陈学昭、曾克,张季纯、锺敬文、马可等都谈到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经历。[59]
1941年,鲁艺文学系学员穆青(1921~2003),在重庆、延安发表了几篇通讯——
这在同学中引起了反响,一来那时很少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二来能收到十元、二十元的稿费,这对每月仅发二元津贴费,只能吃到南瓜、土豆的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个福音。因此,不管每次是谁收到稿费,大家便欢呼雀跃,到桥儿沟街上买些热烧饼和一碗碗羊杂碎,饱餐一顿。
穆青有了一点文名,鲁艺各级领导找他谈心,动员他上《解放日报》当记者,「当时我们都不愿当记者,一心想努力成为一名作家。」最后,由副院长周扬亲自约穆青于延河边,从组织纪律性说到爱伦堡——当记者并不妨碍当作家,「沿着河岸走了几十个来回,终于被他说服了。」1942年8月30日,穆青与同学张铁夫一起来到《解放日报》——
从此,我便结束了令人留恋的鲁艺文学系的学习,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直到今天,整整45年。[60]
1945年8月,田家英收到一点稿费,邀请老友陆石上延安北门外小饭馆,要了一盆回锅肉、一个「三不粘」、两碟小菜、两碗陕北黄米酒。三十九年后陆石(1920~1998,中国文联秘书长),感慨不已:「这在当时,已是很丰盛的午餐了。」[61]
毛泽东和其他中共要角的文章著作得到稿费,大都把「外快」用于赞助公益或个人应酬。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毛泽东捐赠300元为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
毛泽东用《论持久战》的稿费请许多人「嘬」了一顿,并组织延安哲学研究会。[62]1939年初,柯仲平的延安民众剧团经济拮据,开办费仅40元。李富春送来100元,毛泽东也送了100元,贺龙送来20元。柯仲平一宣布消息,全团欢腾,买了一头驮驴、一盏汽灯、一些化妆颜料,服装则是从当地群众中临时借用,老百姓大多把演出当真人真事。延安要角的钱主要来自稿费。1940年,毛泽东再送给剧团300元(据说是《论持久战》稿费),周恩来、董必武、博古也各给剧团送了50元,陈云捐助一台照相机,剧团大大「阔」了一把,除了买骡子、毛驴、衣箱,还剩100多元。[63]
博古也经常拿稿费补贴新华社、《解放日报》俱乐部文娱活动。周六舞会、娱乐晚会,都要用钱。[64] 延安知青何方(1922~ ):延安仅罗瑞卿有一辆自行车,罗的〈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重庆出版,他用稿费买的车。[65]
1939年6月下旬,周恩来、博古自重庆归来,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有一把「大提琴」,一把胡琴固定在一只空「美孚」汽油筒上。[66]
五、经济的放射效应
虽说泛政治化是延安文艺的基本特色,但经济对延安文艺仍有不可小觑的制约力。知青赴延就离不开孔方兄。陕西临潼知青何方,距离延安不过800里,似仅一箭之遥,仍需筹集路费才能前往——
那个时候参加革命是要花钱的,一路上吃的、用的、住的,一切都是自己拿钱。路费和行李要自理。……所以那个时候去延安参加革命的穷人不多。一是大多不知道延安是怎么回事;二是即使听说过,一时也不容易筹到路费和准备好行李。从国民党地区去延安,太穷的人还真参加不起这个革命呢!
成都的田家英、曾彦修因路远,赴延各需六十块钱,两人都是好不容易才凑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只管开赴延介绍信,不管路费,搭乘办事处的卡车去延安,每位车资十四块大洋。[67]因此,赴延知青绝大多数出身不佳,均为地富、资本家、官员、教师等「剥削阶级」或中产家庭。无产阶级原来就很少出读书郎,远赴延安,开销不小,更去不了的。
经济理所当然地还制约着延安文艺的方方面面。1941年春,绥德的几位诗歌爱好者张蓓、高敏夫、郭小川等人自费创办《新诗歌》,1941年8月15日出了第三期,绥德西北抗敌书店经售,价目「每张二角」。这一期诗歌作者:
高敏夫、张蓓、郭小川、公木、萧三、李雷、贺敬之、胡代炜、冯牧、余修、侯唯动、袁烙、隐夫、俞波、李立方、李子奇。[68]
赴延知青多为中小知识分子,搞思想搞研究不行,搞热情浅表的文学倒是正好,一时间延安出了200多个大小诗人。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便是诗人一个。1940年,延安大诗人萧三(1896~1983):
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例如《大众文艺》上,75~83%是诗歌)。[69]
「馋」是延安人的主旋律。1938年初访延的美军上校:
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70]
中国女大生王紫菲晚年回忆: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真想偷几个吃。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二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所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来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71]
华君武(1915~2010)刚到延安,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白天糊窑洞窗纸剩下半碗面粉调的浆糊,他当了消夜。「时隔43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消夜的。」[72]
直到抗战胜利,延安交际处长金城(1906~1991,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边区的生活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比抗战最困难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艰苦的。比如一般大灶虽然油、肉和菜蔬比过去有了很大增加,各种粗粮也可任你吃饱,但大米白面还是不充裕的,往往一个星期只能吃上一两次。[73]
抗大生何方:二两一个的大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食量颇大的「抗大」生卢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个才问:「什么馅?」下饭的菜,春夏还有自己种的青菜,秋冬就只能吃晒干的菜叶,放点盐撒一点生棉籽油。开展大生产后,生活改善较大,十天半月会餐一次,每人分到一碗红烧肉,不少人吃撑得无法爬山回宿舍,东一个西一个仰倒路边,还有的人不停跑步消食,有的则拉了肚子。即使如此,还是惦着盼着会餐。香烟更是稀罕货,开大会听报告,总有人抢坐第一排,为的是捡拾「中央首长」扔弃的烟屁股。[74]
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院,14岁的罗西北(1926~2005,罗亦农独子),领回节日会餐——每人一斤面、一斤馅,本应包好饺子到食堂去煮,但他等不了,包一个在炭火盆里烤一个、吃一个,包完了也吃完了。[75]
延安经济最困难的1941~43年,机关比部队的伙食标准要低。最高规格宴请「四菜一汤」。[76]1938年3月的甘泉县,县长与勤杂工一律每天1.4斤小米,三分菜钱,一年两套军装,一月一块津贴。而且,县政府每月经费只有24元。[77] 中共其时道德自律还较强。
1940~41年,棉衣发不下来,凡有破棉衣的,发一块布补一下洞,凑合着穿。1941年夏吃了几个月的煮黑豆和包谷豆。学习用品,每人每月发半根铅笔,得用铁皮夹上写字,写尽为止;纸张也紧张得很,只发几张土麻纸,最好时每月发两张油光纸;三个月发一枚蘸水笔尖,墨水自制调配;三人合用一盏小油马灯,每晚只有二钱蓖麻油,这还是「党中央」很重视的学制正规的自然科学院。
对科技人员是很优待的。教师们吃小灶一天有半斤白面,每年发套新棉衣。我们学生发的铅笔、纸等,在陕北公学是没有的;我们住的木板床几个人铺一条毡子,没有被子的人可发给一床小被子,在陕北公学也是没有的;一周还能吃两次肉,一次馒头,我在陕北公学时,几个月都吃不上一次馒头。[78]
1940年前后,140万人口的边区要供给八万党政军人员;中共部队、机关只能自给1/5生活所需,4/5需边区百姓负担,生活条件自然好不起来。[79]1944年,毛泽东承认「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据说鲁艺上课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头维他命不够,所以要打瞌睡。」[80]晋察冀根据地生活也艰苦,姚依林:
到1942年,就看清楚了敌我在体力上的差异:我们穿草鞋、布鞋、轻装爬山比不上日本人穿大军靴、背重物爬山爬得快。山地游击战争的大问题是生活问题,它影响了战斗力。……那时,吃上一次猪肉一定是过节!全体欢腾,手舞足蹈,《红缨枪》唱词「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改编为「拿起洋磁缸,去舀猪肉汤!」[81]
延安文化人中流传一句笑语——「客请」,谓延安人太穷,得由外来客人作东。1938年8月31日,卡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两元津贴,只能上街头小吃摊买五分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粤籍留欧舞蹈家戴爱莲(1916~2006)访延,就是由她「客请」主人。[82]
1938年5月上旬,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Evaws Fordyce Carlson,1896~1947),在延安郊村遇上美国援华医生马海德,请马海德去一家八宝饭出名的馆子吃晚饭。一路上,许多人向马海德打招呼,学生、店员、男人、妇女,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
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每个人点了自己要的菜,有人吃完了站起身就走人,有的围坐在一起大讲过去的经历,谁也不感到拘束,谁也没想到要回报点什么。[83]
经济上的紧张当然会影响情绪。艾青、田间、凌子风、欧阳山、孔厥、袁静、张仃等延安文化人,多为中灶(营团级)待遇、伙食一般、津贴很少,一上市场明显缺钱,无法邀友聚餐,更不可能购买书籍字画,不免经常发发牢骚说点怪话。艾青、孔厥因此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错误,不时遭到组织「修理」。[84]
若脱离延安供给体制,追求自由,怕是不行的。整风后期审干阶段,延安四怪之一萧军(1907~1988),不愿屈服中组部招待所蔡主任的刁难(萧妻怀孕八月,蔡坚持必须本人下山就餐,不同意萧递送,而蔡本人却由小鬼送至山上窑洞)。1943年12月上旬,携家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刘庄,不要中共的供给,萧率妻儿垦荒,过着几近穴居的原始生活。三月后,胡乔木由县委书记陪着找来,劝他回城,萧军思虑再三,全家返城,回入体制。[85]
1939年9月创办的《文艺突击》,延安第一份文艺杂志,抗大政治部秘书科奚定怀、郑西野发起,约请“文协”柯仲平、刘白羽等参加,请毛泽东写了刊名,得到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秘书科长谭冠三的支持。最初两期油印,后改铅印。先为旬刊,后改半月刊、月刊,每期定价五分、一角。出版经费原为捐款,在毛泽东带动下,其他中共要角也捐了款,捐款达二三百元。但至第六期,经费告罄。奚定怀(1917~ ):“为了解决经费不济,曾到晋西北一带募捐,但终因经费困难而被迫停刊。”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创刊,售价一角,后涨至二角、五角,1943年2月再涨至一元,当然只有公家订阅,私人无力独订。[86]
延安文化园地虽然局促单一,稿费总量低薄,刺激力量不强,但效应因聚焦而劲爆。一文既出,万目争睹,关注度极高。1944年,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延安翻版四万册,一周销光。[87]
政治类书籍是最抢手的畅销书,国统区也一样。1945年7月,前清举人黄炎培(1878~1965)访问延安五日,回渝后出版《延安归来》,他违背书报检查制度径直印刷。黄说:我不是替谁宣传,不过是受“良心的使命”。《延安归来》初版两万册,几天之内抢购一空,此后印刷十几万册,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影响巨大。[88] 黄炎培的拒绝送审点燃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国民党中常委通过决议,宣布撤销新闻图书检查制度。[89]
国府那时就实现“言论自由”了。
1946年初,老编辑赵景深(1902~1985)总结抗战时期文艺:
要指出哪一本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或抗战期间有什么大著作,几乎使我回答不出来。[90]
赵景深的这一评价当然包括延安文艺。
从总体上,延安生活的窘迫(夜间点灯都受限制),延安文化人时间利用甚受制约,半饥饿状态又使他们失去潜心创作的心态。泛政治化更使他们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失去关注自身感受的“合法性”,文艺创作必须的“小我”已系着不甚光彩的“小资”,阶级学说使他们只能沿着一条轨道行走,失去价值多元化与思维丰富化的理论支撑。
拂去历史风尘,延安文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均有一股掩饰不住的扁平化特质。深究其源,经济因素也是必须追溯的源头之一。
[1]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Inside Red China》),陶宜、徐复译,三联书店(北京)1991年,页75。
[2]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21。
[3]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汉口)1938年5月初年,页15。
[4] 梁漱溟:〈访问延安〉,《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27。
[5]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1938),载李寿葆、姚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页134。
[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页133。
[7] 萧军:《从临汾到延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15。
[8] (美)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阵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54。
[9]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下),页672。
[10]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322~323。
[11] (美)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27。
[12]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5月初年,页5。
[13] 文伯:〈陕北之行〉,《中央日报》1944年7月29日~8月7日。转引自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上),页335。
[14]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增订本),中文图书供应社(香港)1974~1975年,第三编·延安时期(上),页255。
[15]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5月初年,页31。
[16] (美)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71。
[17] 王惠德:〈忆昔日〉,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71~72。
[18]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页135。
[19] 陈亚男:《我的母亲陈学昭》,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页99。
[20] 于光远:《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郑州)2005年,页77~78。
[21] 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234。
[22] 丁玲:〈在医院中〉,原《谷雨》(延安)1941年11月。参见杨桂欣编:《观察丁玲》,大众文艺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73。
[23]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84、135。
[24] 安娜·路易士·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中国〉,李寿葆、施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页176。
[2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6年,上册,页411。
[26] 沙汀:〈漫忆担任主任后二三事〉,《文艺报》1988年4月16日。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79。
[27] 穆青:〈鲁艺情深〉,《人民日报》(北京)1988年5月26日。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39。
[28] 江文汉:〈参拜延安圣地〉(1939年11月17日),《档案与史学》(上海)1998年第4期,页7。
[29] 绯石:〈我与王实味〉(1996),未刊稿。黄昌勇:《王实味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97。
[30] 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43。
[31] 黄俊耀:〈踏遍陕北山山水水的民众剧团〉,《戏曲研究》第21期;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31。
[32]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35。
[33] 李云冰:〈迂回曲折赴延安〉,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延水情: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六十周年》,中国妇女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149~150。
[34]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31。
[35] 任湘:〈我选择了地质勘探〉,贾芝主编:《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368。
[36] 乔松都:《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北京)2008年,页21。
[37]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1938),李寿葆、姚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北京)1985年,页138。
[38] 罗平汉:《「大锅饭」——「乌托邦」记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65~67、30。
[39] 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13、21~23。
[40]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313。
[41] (美)爱德格·斯诺:《红色中华散记》(1936~1945),奚博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27~128。
[42]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香港)2007年7月第2版,页198~199。
[43] 俞颂华:〈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申报周刊》(上海)1937年第2卷第20期,页439。
[44]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21。
[45] 王光荣:〈日军战俘在延安「洗礼」〉,《百年潮》(北京)2004年第9期,页36。参见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页41、43。
[46] 李琴:〈杨立三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炎黄春秋》(北京)2008年第5期,页53。
[47]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下册,页323。
[48] 于光远:《于光远自述》,大象出版社(郑州)2005年,页83。参见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221。
[49]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汉口)1938年5月初年,页18~19、33。
[50]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815。
[51] 孙国林:〈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中华读书报》(北京)2007年10月17日,第19年。
[52]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桂林)2007年,页22~23。
[53] 毛泽东致周扬信(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138。
[54]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年9月1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页374。
[55] 李波:〈黄土高坡闹秧歌〉,《新文学史料》(北京)1985年第2期。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09。
[56] 胡绩伟:《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75。
[57] 朱鸿召:〈唯读《解放日报》〉,《上海文学》2004年第2期,页78、83。
[58]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页166、165、145。
[59] 孙国林:〈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中华读书报》(北京)2007年10月17日,第19年。
[60] 穆青:〈鲁艺情深〉,原《人民日报》(北京)1988年5月26日。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139~140。
[61] 陆石:〈我心匪石〉,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221。
[62]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页108。
[63] 黄俊耀:〈踏遍陕北山山水水的民众剧团〉,原《戏曲研究》(北京)第21期;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233、235。
[64] 温济泽:《温济泽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410。
[65]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84。
[66] 江文汉:〈1939年江文汉延安访问记〉(1939年11月17日),黄天霞译,原《档案与史学》(上海)1998年第4期,页11。
[67]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41、45。
[68] 朱子奇:〈延安和绥德的《新诗歌》及其他〉(代序),载朱子奇、张沛编《延安晨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4。
[69] 萧三:〈诗到难成便是才〉,原《新诗歌》(延安)第四期(1940)。参见朱子奇、张沛编《延安晨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10。
[70]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年,页149。
[71] 蒋巍、雪扬:《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北京)2007年,页135~136。
[72] 华君武:〈鲁艺美术部生活剪影〉,原《延安岁月》;参见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页364。
[73]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页270。
[74] 何方:《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明报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册,页73~74、93~95、120。
[75] 赵士杰:〈越过急流和险滩——记罗西北〉,贾芝主编《延河儿女——延安青年的成才之路》,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页334。
[76] 陈俊岐:《延安轶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98、13。
[77] 原景信:《陕北剪影》,新中国出版社(武汉)1938年5月初年,页13。
[78] 林伟:〈忆自然科学院发展中的一些情况〉,《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参见朱鸿召编选:《众说纷纭话延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169。
[79]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5年1月第2版,页319。
[80] 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107。
[81] 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89~90。
[82] 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页41。
[83] (美)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祁国明、汪杉译,新华出版社(北京)1987年,页154。
[84] 陈明远:《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文汇出版社(上海)2006年,页45。
[85] 王德芬(萧军妻):〈萧军在延安〉,《新文学史料》(北京)1987年第4期,页110~113。
[86] 朱鸿召:〈唯读《解放日报》〉,《上海文学》2004年第2期,页82、86。
[87] 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页166。
[88]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6年,页232。
[89] 梅剑主编:《延安秘事》,红旗出版社(北京)1996年,下册,页702~703。
[90] 赵景深:〈文艺的离去和归来〉(民国三十五年新年),载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年4月初年),上海书店1983年,页151。
初稿:2008-5中旬初稿;補充至2008-9-3
原载:《新文学史料》(北京)2010年第1期
转载:《中国文学年鉴》(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