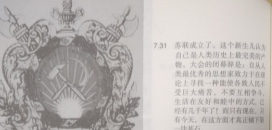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92)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45)
在1989年立陶宛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扒了俄罗斯人的皮,你会发现他们的骨头是鞑靼人的。”不管这句话真实与否,但从侧面反映出俄罗斯人在其他感觉不平等的少数民族心目中的印象。
无可否认,在苏联时期,由于联盟中央在经济上实施某些倾斜政策,使一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但是,苏联当局人为地加速民族融合,以实质上的大俄罗斯主义压制少数民族,其结果是一方面各民族经济发展了,另一方面民族间的离心力也加大了。苏联当局想以用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来换取他们对民族个性的“忽视”,再用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求,迫使他们放弃本民族政治经济上的要求,并逐渐纳入到“苏联民族”的国家发展要求中,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向“苏联民族”发展,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
其一,根据当时苏联少数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其社会发展首先应该是“民族化”的。因为,这些民族本身要求发展和独立的历史进程才开始,刚刚从沙皇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民族自豪和自觉的激情被唤醒,重压后追求自由的意愿喷薄而发。而当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优先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政策,一时吸引和鼓励了广大少数民族谋求彻底解放和迅速发展。这就使苏联当局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的目的与少数民族自我要求发展的目的产生矛盾。随着民族经济文化的成熟,苏联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一旦支撑这个大家庭存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存在了,民族分离也就不可避免了。
其二,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也同样在苏联社会的发展中表现出来,要求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可能平等之间必然产生矛盾。这种矛盾演化的结果是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增长,它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各民族充分发展的目的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通过国家协调还可以部分解决;当在中央集权膨胀、计划经济僵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各民族的利益就会产生对立,民族分离和要求民族独立就成了民族自身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民族独立运动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就往往成为这个时期政治舞台上的热点。
其三,苏联当局在民族政策中奉行实质上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人为地制造“苏联民族”,有意压制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语言的使用,导致重新唤起少数民族对沙皇时代民族压迫的回忆,造成对现行民族政策的抵触和反抗,所以才会出现“俄罗斯人的骨头是鞑靼人的”说法。
法国巴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阿兰.贝桑松在《民族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一文中以《大俄罗斯主义》为题,论述了苏联当局推行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动态:
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列宁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确立布尔什维克党在新型国家中的核心地位。因此,在打碎了旧国家,喊了一阵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之后,没有中间过渡,便进入重整军队、改造传统统治机构阶段。不少旧军队的军官以及政府机关人员怀着各自的动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一、他们有的希望恢复秩序,结束无政府状态,减少犯罪;二、有的抱着爱国思想,害怕在这新的“多事之秋”失去几个世纪以来建设取得的成就;三、有的抱着民族主义的态度,以期拯救统一、不可分割的俄国,即俄罗斯帝国。布尔什维克政权为最后一种动机提供了理由。布尔什维克政权能够恢复单一政权对旧帝国内部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的统治,这足以满足民族主义倡导者的最低要求。布尔什维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盟就这样形成了,而且这一联盟一直是苏维埃政权中的主要道德力量,迄今仍然如此。
布尔什维克一一大俄罗斯联盟很快吸引了一些极右的非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但是我不认为这个联盟是平等的,也不认为斯大林主义中在民族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有一种进步的融合。事实上,党仍然是联盟的领导者并懂得如何保持列宁所建立的党—阶级—国家的从属关系。革命的目标并没有因为民族主义的目标(帝国的保持和扩大)而被抛弃。对党来说,问题是按照恰当的等级保持“党—阶级—国家”的等级。多年来,主动与俄罗斯“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本身进行斗争,显然是必要的。反对沙文主义甚至反对俄罗斯的斗争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这一切只适合那些可能危及党的利益的同盟。自三十年代起,俄罗斯民族主义逐渐地渗透到意识形态中。俄罗斯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党选取可以促进苏维埃国家的发展具有民族意义价值的养料的源泉。例如,彼得大帝成为苏维埃国家推行军事及现代化计划的历史典范;伊凡雷帝成为肃反的先例;描写俄罗斯光辉战绩,蔑视西方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的作品)备受青睐,具有普遍价值和跨民族意义的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却受到严格的审查,甚至被禁止发行。
民族主义得到光大,因为它仇视共产主义以外的任何东西。因此,它被褒扬为“苏维埃爱国主义”,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主要力量,把民族沙文主义也拉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使国家变成与民族主义结成的联盟,并应用它把苏维埃国家政权推行到帝俄的每一个角落;接着又用同一工具,将其形式与统治扩展到边境以外的地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外在体观。基于这一原因,共产主义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这在捷克和波兰表现为学校强制学习俄语,在文化方面表现为奖励俄罗斯文学艺术而轻视西方艺术。
当初建立苏联时,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在契约上是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为基础的。为了使那些曾经是沙俄殖民地的民族国家对联盟的国家体制放心,列宁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写进联盟宪法。但即使这样,像格鲁吉亚就始终坚持相对独立的国家权利,苏维埃政权只好用布尔什维克党的一致性才压服了格鲁吉亚。但是根深蒂固的大俄罗斯主义对苏联民族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二战后,大俄罗斯主义在斯大林集权主义的刺激下变本加厉,导致俄罗斯与其他民族的矛盾加剧了。
马克思在《18世纪外交史内幕》一书中指出: “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征服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大胆综合中。”与马克思一贯以经济基础为重的立场不同的是,他在这本著作中,把俄国扩张的原因归结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因素。这本书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揭示了俄国扩张主义的根源: 建立一个梦寐以求的泛斯拉夫帝国。这是历代沙皇一贯奉行的政策,与俄罗斯民族独特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有关。
在欧洲,俄罗斯民族是一个迟到的巨人,他们的祖先是生活在第聂伯河流域的东斯拉夫人。可以说,他们是生活在亚洲古代文明和欧洲古代文明之间。因为,此地的东南部与广袤的亚洲内大陆连接,即乌拉尔山以东的干旱半干旱草原和南面的黑海草原、高加索地区。很久以来,这里就生活着游牧文化发达的民风强悍的民族。而此地的西北部与欧洲文明的中心隔着广大的东欧平原和山区,这里居住着欧洲比较落后的游牧和山地民族。这就使生活在其间的东斯拉夫人难以接触到欧亚大陆其他民族的古代文明,其民族发展过程又过早地频频受到异族特别是蒙古人的影响。公元10至11世纪,在基辅罗斯的地域上虽然形成了罗斯人,但罗斯人进一步发展成一个统一民族的过程中断了,基辅罗斯也没有发展成一个统一的单纯的欧洲国家。从13世纪至15世纪,基辅罗斯、高加索和中亚地区都处在成吉思汗之孙拔都建立的金帐汗国的统治之下。直到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才推翻蒙古人的统治,罗斯人逐步融合成俄罗斯人,在16世纪初形成统一的俄罗斯国家。
由于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使形成较晚的俄罗斯帝国具有很强的扩张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们的确继承了蒙古帝国强烈的征服意识和勇猛精神。据统计,16世纪30年代,俄国的领土为280万平方公里,人口650多万;到19世纪末,俄罗斯帝国的疆域已达224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亿。这是俄罗斯帝国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通过残酷的征服达到的。由此可以想见,伴随着对不同民族征服过程中的杀戮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反抗斗争和离异心理是多么强烈。特别是一些民族比俄罗斯人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消融其民族性的,加上传统欧洲国家对沙俄扩张进行遏制,鼓动其他民族独立,使非俄罗斯民族的归属意识始终处于不稳定之中。
知道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就会明白现实俄罗斯民族的激情何以会时不时地喷涌——大俄罗斯主义是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块垒。
唐科斯在《分崩离析的帝国》中对苏联当局与少数民族在卫国战争中的纠葛这样评论:
苏联的历史学家们看到,对于很多被俄罗斯控制的民族来说,它们并不是在殖民化和自由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在两种殖民化之间作出选择。例如格鲁吉亚人就是这样,他们过去受到灭绝他们文化的土耳其的威胁,后来是受到保存他们文化并让他们搞社会主义的俄罗斯的威胁。从那时起,殖民主义就成了“最小的坏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反抗殖民主义的各种民族运动似乎更多的是受过时的感情的支配,而不大是反映各有关民族的民族利益。历史书中充满了新的英雄人物。除了俄罗斯的那些贤明国王——虽然他们都是专制君主,但他们的历史作用不容否定——之上,又加上了各民族历史上那些懂得必须与俄罗斯联合,懂得必须接受这种“最小的坏事”的民族英雄。实际上这种民族英雄是很少的,二战前,在这方面唯一够格的历史人物就是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他于16世纪在佩列亚斯拉夫签订了乌克兰与俄罗斯结盟的条约。
直到1941年,这种变化还是模糊而混乱的。苏联社会刚从集体化和大清洗的噩梦中摆脱出来,人们可能还没有完全看出上述对苏联各民族历史的新看法所带来的一切麻烦。正是战争才最终暴露了“各民族的友谊”这种斯大林式提法的真相。战争首先暴露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不牢固性。德军在苏联领土上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是由于下面的事实而促成的,即德军踏过的土地上居住的不是俄罗斯人,而是那些勉强同意、有的甚至是在不久前才同意加入苏联的民族(如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乌克兰人对待德军的推进的态度反映出民族仇恨已十分深刻。这种民族仇恨部分地得到了德国人在苏联领土上执行的政策的鼓励。
在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以前,《20世纪的神话》一书的作者阿•罗森贝格就在柏林设想出了一个分割苏联的异想天开的计划。罗森贝格意识到这个欧洲唯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局势一触即发,建议德国用民族主义这张牌来扼杀苏联,使俄罗斯变成一个转向东方、恢复其亚洲使命的国家,并以德国扶植的依附于德国的民族国家网来包围之。在某些地区,罗森贝格计划的实施煽动了民族情绪,从而加重了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困难。高加索地区就是进行这种试验的好地方。德国军队支持各地趁苏军撤退之机而建立起来的代替被解散的苏维埃权力机构的民族政府。
如果德军把高加索的经验推广运用到全部占领的领土上的话,苏维埃联盟也可能化为乌有了。但是,罗森贝格的主张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 一方面是以约德尔为首的部分军事将领的反对。他们认为,支持分散的各民族会引起最大的民族即俄罗斯民族的反对,而明智的做法应该是信赖俄罗斯民族并使之脱离其领导人,从内部来摧毁苏维埃政权。从另一个极端来加以反对的是希特勒。希特勒认为,所有苏联公民,不管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都是野蛮人,那么为什么要对他们区别对待呢?
这些反对意见使罗森贝格提出的支持苏联各民族的政策没能实行,并最终把那些对德国在东方的暴行感到失望和恐惧的民族推向了苏维埃联盟。
不过,这些情况向斯大林表明,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盟政权是非常脆弱的,必须给它注入新的内容。从短期来说,在德军的压力下,这种内容只能是向民族感情作出让步,这是因为必须在德国人正在玩民族主义这张牌的那些地方尽快地战胜德国人。还因为,从1941年的溃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光依靠共产主义的准则是不够的,过去曾保卫过祖国的那些英雄的名字远比马克思或列宁的名字更能起到动员人民的作用。
战争还向中央政府表明,边远地区是脆弱的,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这种脆弱性会给整个制度带来致命的威胁。最后,斯大林还看到,人们对国际团结的呼吁反应冷淡。他不得不求助于另一种力量,即求助于历史上的、民族的和宗教的团结。这样,也就给苏维埃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内容,而这些新的内容又将反过来使苏维埃思想体系发生深刻的变化。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苏联各民族发展过程的巨大差异,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低级阶段,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多端,导致多民族的集权国家内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要客观全面地反思这个问题,就必须研究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产生与当时的客观现实的关系,以此了解斯大林民族理论形成的深层原因,这样才能知晓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特点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
从斯大林民族意识形成的阶级基础来看,他的父亲祖祖辈辈都是农奴,他的母亲也出生在一个农奴家庭。斯大林11岁失去了父亲,是母亲辛辛苦苦做工使她唯一的儿子上学的。因此,斯大林发奋学习,是班里的优秀学生,但大多数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弟却瞧不起这个穷小子。可以说,斯大林上的人生第一课就是深深体会到阶级的差别和阶级的对立。由于沙皇对外穷兵黩武和对内压迫剥削各族人民,使得当时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各族人民的反抗日益强烈并逐步统一到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上来。所以,1894年当15岁的斯大林来到第比利斯教会中学后,他就开始了他一生再未间断过的革命活动。
1904年9月,斯大林在《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一文中阐述了他的民族观。他说: “所谓贵族的‘民族问题’,当时(在格鲁吉亚归并俄国之后)格鲁吉亚贵族感到丧失他原先在格鲁吉亚国王统治时代所享有的特权和势力,对于自己是多么不利,他们认为充当‘庶民’有伤自己的尊严,所以想要‘解放格鲁吉亚’。他们想借此使格鲁吉亚国王和贵族担当‘格鲁吉亚’的领导者,从而把格鲁吉亚人民的命运交给他们!这是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 “现代社会生活又在我们这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问题。当年轻的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很难和‘外国’的资本家进行自由竞争时,它就通过格鲁吉亚民族民主主义者开始嘟哝起什么独立的格鲁吉亚来了。” “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走上了斗争舞台,于是新的‘民族问题’即无产阶级的‘民族问题’也跟着产生了。” 在无产阶级的民族问题上斯大林主张: “为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必须不分民族地把一切工人联合起来。很明显,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把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波兰、犹太和其他民族的无产者紧密团结起来,乃是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必要条件。”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雏形,文中的思想观点在他以后的民族理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并在实践中得到了始终如一的坚持。由此可见,阶级立场、国家利益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核心。从这一基点出发,斯大始终把民族矛盾和纷争归结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中期,苏联当局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引起各民族地区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加剧了民族矛盾。同时,这种政策在联共(布)党内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面对这种形势,1928年7月,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中提出: “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此后,斯大林于1929年4月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33年1月在《关于农村工作的总结》中,再次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观点,认为党内的分歧和斗争和国内外的阶级斗争有关,因为“我们党内的分歧意见是在最近发生的阶级变动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某些共产党人认不清阶级敌人的真面目,致使“伪装得很巧妙的反苏维埃分子就在某些集体农庄里把持一切,在那里组织暗害和怠工活动”。1934年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明确提出,苏联国内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机会主义一样是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因为民族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与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进而强调乌克兰等地方民族主义已成为苏联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危险”,号召全党要坚持打击地方民族主义。
斯大林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弦自从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以后就一直紧紧地崩着,直到他本人“驾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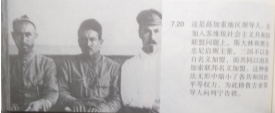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