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英研究文革对蒙族的他称之为“文化性的种族屠杀”。内蒙有34万人被捕,27,900人遭到杀害。这种大屠杀兼有种族屠杀和阶级屠杀的特质。
忘记遇难者意味着他们再次被杀害。我们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杀害,但我们要对第二次杀害负责。
——威塞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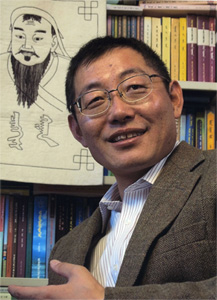 日本静冈大学蒙古族教授杨海英。他说内蒙古人民和香港占中一样要求中共承诺的真正的高度自治。但是1949年以来承诺没有兑现。
日本静冈大学蒙古族教授杨海英。他说内蒙古人民和香港占中一样要求中共承诺的真正的高度自治。但是1949年以来承诺没有兑现。
我的中国身份证上登记的种族是汉族,但我是有蒙古血统的汉族。与我算是“本家”的四川老诗人流沙河(他本姓余),从诸多家谱中考证说,成都附近这支姓余的,是元末为躲避战乱逃到四川的蒙古族后裔,为避开明朝的迫害,他们才改“金”为“余”,此后五百年逐渐融入汉族。不过,从相貌上还能看出几分端倪来:我跟流沙河老师的长相,都有些像中学历史课本上的忽必烈:宽宽的额头,细长的眼睛。我这个不纯正的蒙古人,只在十多年前去过一次内蒙古大草原,却为眼前的景象深受刺激:古时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如今的草只能没住鞋面而已。
在中国的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新疆和西藏的分离主义倾向最严重,内蒙古似乎长期风平浪静。直至2011年5月11日和15日连续发生数千名学生和牧民示威抗议事件,内蒙问题才引起国际关注。当局严厉镇压民众的示威抗议,这也成为时任内蒙封疆大吏的胡春华晋升的“投名状”——如同一九八九年胡锦涛镇压西藏人民的反抗,受到邓小平的青睐成为接班人一样。中共重用的人,必须心狠手辣,不能有赵紫阳的“妇人之仁”。而内蒙的反抗力量微弱,不是蒙古人没有藏人和新疆的维族那么勇敢——蒙古人自古就是弯弓射鵰的民族,而是因为此前中共在内蒙古实施的镇压、清洗无比残酷,蒙古人的菁英早被摧毁殆尽。旅日蒙古族学者杨海英所著的《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一书,就发掘出了这段被埋没的历史,拉响了长鸣的警钟。
双重屠杀:种族屠杀和阶级屠杀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文革时期发生在内蒙古的大屠杀,作者称之为“文化性的种族屠杀”。本书不是一本完整的历史叙述,而是以第一手的访谈为主体的数据汇编——这不是贬低本书的价值,反倒因此彰显出本书作者打捞历史真相的努力之可贵。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文革期间,内蒙有34万人被捕,27,900人遭到杀害,12万人致残。当时的蒙古人口约140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50个人中有一人被杀害。与之同时发生的还有:对于女性的强奸等性暴行各地横行,强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语⋯⋯对此,杨海英指出:“这完全是中国政府和汉民族主导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
在我看来,中共政权在内蒙古实施的大屠杀,兼有种族屠杀和阶级屠杀的特质。种族屠杀以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最为典型,阶级屠杀以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对本民族中“资产阶级分子”的屠杀最为典型。《没有墓碑的草原》的第一部即描述蒙古人中“挎洋刀的”是如何遭到中共整肃的。所谓“挎洋刀的”是满蒙时代受日本教育的菁英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组成了蒙古骑兵师团,一度成为蒙古独立的主要力量。作者的父亲曾在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服役,他的上级就是“挎洋刀的”。”挎洋刀的”蒙古军官举止端庄,谈吐优雅,气质不凡。与之对比,共产党军队中掌握实权的将领,大都是不学无术的粗鄙之人,匪气与痞气十足。文革开始之后,粗鄙的汉族军人对优雅的“挎洋刀的”发动了大规模的整肃。这种整肃除了种族屠杀的特质之外,当然同时带有阶级屠杀的色彩,与之最为接近的是苏俄对波兰军官和知识分子发动的卡廷屠杀。
本书中还用相当的篇幅记载了最具典型性的图克人民公社大屠杀的真相。文革期间的大屠杀,已经广为人知的有湖南道县屠杀、北京大兴屠杀、云南沙甸屠杀等。图克位于鄂尔多斯地区,1969年有人口不足3000人,被打成“新内人党”的就有近千人,占成人的70%以上。其中,被活活打死和因后遗症而死的49人(也有资料说79人),受尽折磨重度伤残者270人。若干幸存者向作者讲述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如灼烧女性的阴部,用铁丝制作脑箍套到人的头皮里,让祼体妇女骑在毛绳上、两人前后拉锯、受害者的外阴和肛门被拉通⋯⋯难道这就是君临于蒙古大地的伟大的中华文明和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文化?
标榜反殖民的“社会主义殖民体制”
中共一向标榜“反殖民”,并以忠诚的民族主义者自居。然而,中共对待国境之内的“少数民族”,却大力实施“隐蔽的殖民主义”和“升级版的殖民主义”,也就是杨海英所说的“社会主义殖民体制”,比起昔日之满清王朝和中华民国政府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土耳其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华帝国的江河日下乃至土崩瓦解,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几乎同步,所以一个是“东亚病夫”,一个是“西亚病夫”。印度裔学者潘卡吉•米拉什在《从帝国的废墟中崛起》一书中,探讨了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亚洲古老帝国的重生之路,总结出居然是同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泛亚洲主义与军事去殖民化。
吊诡的是,这些“亚洲病夫”一旦缓过气来,立即对更弱小者露出锐利的牙齿。1915~1923年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深陷一战泥潭,战败后帝国崩解,建立了新的、缩小的土耳其共和国。与此同时,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导致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亡,是二十世纪第一起种族灭绝大屠杀。时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亨利•摩根索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确信,在种族遏制的整个历史上,再没有如此可怕的情节。以往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屠杀和残害,与1915年亚美尼亚族人的遭遇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这场大屠杀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并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种族屠杀”。
但是,在土耳其国内,这一历史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禁区,不属于被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畴。土耳其作家奥汗•帕幕克因为在2005年声称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而一度面临四年的牢狱之灾。好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声引起欧盟干预,土耳其政府这才作罢。另一个记者赫兰特•丁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因为坚持认为“亚美尼亚大屠杀”真实存在而被极端分子枪杀。
在中国,因为共产极权体制的建立,极权体制衍生的殖民主义更为精密和严酷,对外围少数民族的屠杀也更是高度组织化。虽然中共屠杀单一民族的人数比不上亚美尼亚屠杀,但中共屠杀的境内各民族加起来的数量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藏族学者估计,中共政权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屠杀了超过70万藏人;而维族、回族、壮族、苗族等人口众多的少数民众也曾有过人口剧烈减少的时代。
在冷战时期,被中国统治的内蒙古,处于中国与苏联及其附庸国蒙古国接壤并对峙的地理位置,特别遭致北京的猜忌。“坚壁清野”的计划一旦出炉,就连那些早在延安时代就“入伙”的蒙古族共产党干部都难逃被清洗的命运。以蒙古族的最高级官员乌兰夫为首的“内人党”案,在文革前夕就已经形成了一片腥风血雨。在杨海英的采访对象中,就有多位“根正苗红”的蒙古族共产党官员及御用文人,最后仍未逃避灭顶之灾。
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中原教旨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弱,于是民族主义日渐高张。这种汉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必然要渲染近代以来中国遭到西方列强侵略的悲情史,然后以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甚至实现”伟大复兴”的”恩人”自居。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当局对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的欺凌和压迫却达到了亘古未有之地步。在政治和文化殖民的基础上,近二十年来经济殖民愈演愈烈。由于内蒙古境内储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等资源,掠夺式和毁灭性的能源开发,让草原变成荒漠,蒙古族失去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透过情绪化的零碎叙述挖掘真相
对我个人而言,《没有墓碑的草原》确实是第一本认识蒙古族问题的”启蒙读物”。对于中共建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我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不由自主地从所谓的”宏观层面”来思考,却很少从”族裔史”的角度来思考。所以,读了这本书之后,虽然不是加害者的我,也愿意因为长期以来对此议题的忽略和漠视而表示迟到的歉意。
不过,我在本书中也读到作者激越的民族情绪,与那些受难者及其家属促膝长谈,将历史深处最黑暗的部分呈现出来,不能不让人感到愤怒、痛苦和酝酿出激烈的批判意识。正如长期接触古拉格群岛的资料、本人也是古拉格群岛幸存者的索尔仁尼琴,自然而然地表示说:“我一直以来都用最激烈的方式批判苏联共产党政权。”
但是,激情之后,还需要理性、客观的思考、分析与判断。本书的中文译者刘燕子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个裂痕。在与作者的对话中,刘燕子询问说:“如何超越族裔民族主义而客观地看待这些主观的、零碎的、断片的、情绪化的语言?或者说,您自己如何做一位感情上的蒙古主义者,理性上的研究者呢?”杨海英的回答是:“没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地‘零度叙述’,‘情绪化的零碎的叙述’如利爪,能在被风化的废墟中挖掘出真实。而梳理这些支离破碎的陶片,正是研究者的责任。”我期待着在作者的下一部著作中,更多地看到第二步的梳理工作,包括对那些与中共合作的“蒙奸”群体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的深刻剖析和反思。我个人认为,作者对作为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乌兰夫的评价,过于正面了。其实,对于乌兰夫而言,党性始终高于民族身份,他虽然饱受迫害,仍然未能像赵紫阳、鲍彤那样迈出与共产党体制决裂的那一步。对于这样一位复杂多面的人物,还需要有更为深入的研究。
基于自由人权信念的民族自决
未来的内蒙古何去何从,是脱离中国,与蒙古国联合成一体;还是留在一个松散的中华联邦之中?在中国漫长而艰巨的民主化进程中,蒙古族民众的选择以及某个“天时、地利、人和”聚合的情势是否出现,仍是未定之数。如今,蒙古人在内蒙古已经成为绝对的“少数民族”,内蒙古的四百万蒙古人如何与已经在内蒙古定居的一千多万汉人和平共处?将这些汉人全部赶走是不现实的,前南斯拉夫发生的种族对抗、种族清洗已是前车之鉴。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创造性的思路。而且,必须超越激越的民族主义立场。
这也是我在与台湾知识分子交流的过程中获得的启发。杨海英在本书中感叹说,与汉人交流困难重重,因为汉族中心主义根深蒂固,“汉人一开始就蔑视蒙古人‘野蛮’”。反倒是到了台湾,他跟台湾人更能顺畅地交流,不仅是台湾民众经历了二十多年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耳闻目染,而且台湾受到北京威逼利诱的处境与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人有些许的相似之处。台湾的独立之路,最可依托的意识形态是古典自由主义,是人权至上和住民自决的原则,而不是近代以来排他性的、唯我独尊的、有仇必报的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愿杨海英的愿望早日成为现实:
“我希望出现‘对少数民族新思考’的智慧者。这本书汉文版的出版目的,就是试图探索真相调查与对话的途径,切断以暴易暴的锁链,清除暴力土壤。”
来源:《开放》2015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