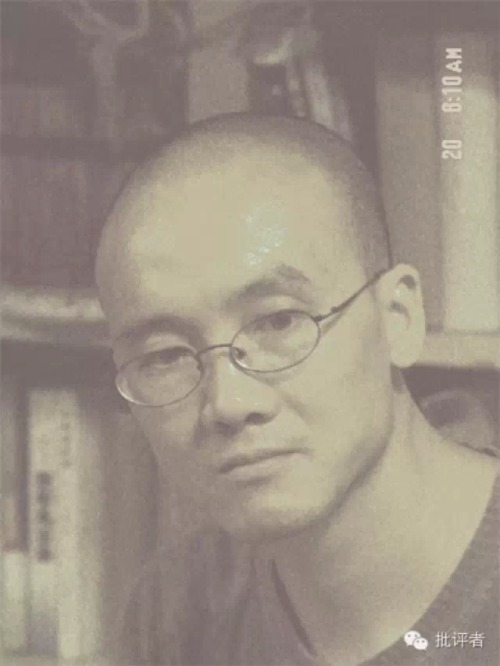“我从来都在秘密地生活。”辩护也是声张?
“要达到具体的崇高。”共勉还是对攻?
“我们都生活在教育的反面。”犬儒只是乡愿?
一一王东东:《西山》
身处外省时,王东东似乎要将活跃在诗歌创作中心的写作者逐一评述,以展示他在写作上的诸多见解。其读者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新锐的诗歌批评者。和所有怀着诗歌理想的年轻人一样,谁不向往去北京文化中心生活,哪怕是短暂地居住一阵,然后再返回旧地。然而,去北京生活,有的人是舍弃了一切,漂泊流浪;有的人是寄托于某类工作,挣扎生存;有的人是通过考学升迁。王东东属于后者,是我们现实生活方式中较为幸运的一种。他内心的感受是:“书桌虽小,也可以放下一个地球仪”。读书生活之美妙,用他的诗句形容,则是“书页里的宁静,死去的光阴,如此接近天堂”。他是一个明白人,知道“谁也不能用目光让书架倾斜”。似乎,当初那些因距离而形成的写作者已经不存在了,他失去了值得观察的对象,但这并不是对象消失了,而是对象和观察者被他整合在了一起。至少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说,自我观察更为重要。这充分表明,原本他并不属于写作潮流,而是写作潮流中的清醒者。连“在门口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也会让他产生警觉,是不是“有人在说我的坏话”?这种警觉对应的不是人间的是与非,而是更为深沉的对大环境的体会:“对一个国家了解得越多,就越无法去恨。爱一个国家也是如此。”这时,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使他明亮起来的,不是什么不同凡响的批评观点,而是一颗诗心。他是在用诗人的心灵去感受一切,表述一切。他说:“家乡疏远了我,远方疏远了我,风景疏远了我,政治主导了空气”。他“立志不做文士,只是为了不打嘴巴仗”。在他看来,无论如何,“汤圆和水饺也拼不成十字架,但是茄子和豆角可以”。但那“仅仅是在盘子里”,他不满足。因为,他感到“祖国,一片土地,在泪水中升起”。他看到“远郊的村民是刁民,只适合做仆役或管家”。对于整个不良的社会状况,“某些知识分子,心里知道,但嘴上就是不说”。“那些海市蜃楼,看,比真正住进去更幸福”。面对诸如此类的现状,怎么把自己融入到这一时代生活中去,王东东是在接近这样的一种诗人情怀。
无须证明,王东东这一代诗人正处于开拓自身写作格局的年龄。现在决定未来。他们首先要避开上一代诗人在写作上所形成的两个较为明显的惯性:一是叙事,二是口语(王东东认为口语是叙事的自然声调)。要突破这惯性,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认识上要明白,叙事和口语是方法,不是结果。它们可以帮助一首诗的形成,但本身不是诗。我们可以运用任何方法,但任何方法都不能成为一种写作上的追求。在写作上,诗人唯一的追求是诗。其次,是要寻找到自己在写作和生活上不同的站位,以此形成自己的写作空间,然后苦心经营。所以,可以说,文章开头的评述,是对王东东在写作和生活上的站位的一个简单的评述。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首诗来考察他已经形成的写作空间。这首诗的题目,叫《西山》。
古代诗人陈志岁在《夏栖西山》一诗中写到:“暂绝去来心,西山一片林。枯根滴泉响,嫩蝶抱花沉。日午蝉声懒,庭荫榻迹深。白云如有意,穿竹伴清吟。”北京西山,是太行山的一条支阜,古称“太行山之首”,又称小清凉山,历今房山、门头沟、石景山、昌平等几个区县。那么,王东东的《西山》是何情形?但见诗的起句:“西山在变低”。暗示诗人在登高。但“岁月已被西山固定,不再长高”。诗人所看到的这一幅“国画”,既不挂在客厅墙壁上,也不镶嵌在“屏风”里。西山与客厅,是诗人提供给读者的两个站位,一个是现实的经历,一个是古典的人文经验。当立足于西山,客厅是幻想重回古时那种客厅会友的书香生活;当立足于客厅,西山则是一幅挂在墙壁上引人神思的“国画”。但不管怎样,西山是人类生活的见证,“看着恐龙和北京人跑过”。而“情欲”是唯一的生命力,让人“想到了一个词但没有说出”。我们可以把这个“没有说出的词”,视为这首诗隐藏的立意。
在具体写作这首诗的时候,王东东想到的词是死亡。在这儿,死亡对应崇高,是合适的。因为诗人“要达到具体的崇高”。这崇高对他来说,是在体验之中,一种体会和实践。诗中,诗人把自己寄托于“一个失地的青年农民”,“来到了广场”,“他软弱的影子投身于大理石方砖的缝隙,哪一块是他从山上分解出的花岗岩?”这儿有对崇高的体验。还有诗人行走在圆明园的福海边,“一个脸部烧伤的行人迎面向我走来,脸上还带着炭黑”,这时,诗人心里怀着人类文明的崇高感,所以,他才能看到整个圆明园就是这一张被烧伤的脸。“但,如何向你们说明这不是幻觉?”
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崇高。从一开始,崇高就与悲剧和悲剧人物有关,悲剧让悲剧人物不胜其重,从而分裂甚至毁灭,这种存在的危机带给观众的净化感也包含着崇高感:因为观众总会重生。这可以说是悲剧崇高。当悲剧的艺术逐渐消亡,我们只能在崇高感中回忆悲剧。也可能,崇高本身是一种回忆:不仅是对悲剧的回忆,更是对崇高本身的回忆。这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朗基努斯会说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
当我们把王东东的《西山》视为含有崇高这一主题的审美对象时,我们只能从该诗的形态和格调中去体察。第6节,诗的首句:“我如何得到这个印象?”幸运的是,此时诗人并不是在登高,而是“我坐着,看着窗外”。《西山》一如济慈的《夜莺颂》,“《夜莺颂》包含着许多与夜莺没有什么特别关系的感觉,但是这些感觉,也许一半是因为它那动人的名字,一半是因为它的名声,就被夜莺凑合起来了”。《西山》也是这样,因为它跟北京这个地理有关,但不是古代诗人陈志岁的“穿竹伴清吟”,而是给出了一个雄伟的景象:“一个红轮,在地平线追赶南行的火车,一大串红轮……”。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社会无疑是一列由邓小平南巡所启动的火车,这列火车被一个巨大的“红轮”推动着前行,我们感受到的一个最大的现实,是崇高在坠落。当然,毛时代的泛崇高早已经不存在。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王东东于自然山水中寻求与现实的对应物。有人是在古书典籍中寻求与现实对应的思想,有人只是在寻求但从不与现实产生对应,仿佛一只无头的羔羊,任人宰割而不自知。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共同目标的时代。我们不是彼此的竞争者,我们应该是同盟者。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是天生的,需要同盟者去创造。可在平庸的现实,人们普遍渴求正常的生活,即使在所谓的文学艺术界,也很少有人对真理有真正意义上的感知,这让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难以产生。我们都有一种“自我保全的冲动”。英国的E.博克(1729-1797)在《我们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的起源的哲学探讨》一文中提出,崇高感情的根源是“自我保全的冲动”。这当然同样是因为存在的危机,一种危险的机会,于是崇高感同时包含着危机和欢欣,一种欢欣,加在危机之上。所谓危机,用王东东的诗句来形容,就是“一个漂浮的天空,握住心痛的锥子”。在这儿,王东东深刻地洞察到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那充满痛苦与危险的移动,“正是不断确定自己的位置的冲动让人们热衷于移动”。
一个念头浮现:西山变得越来越低,
它正在下沉,在我心里坠落。
康德认为:“崇高感是一种只能间接产生的愉快,它先经历一种生命力在一瞬间受到阻滞的感觉,然后立刻又继之以生命力的更强烈的迸发,它在想象力的运用上是很严肃的,包含着惊讶和崇敬”。他没有将崇高赋予外在的世界,而是将之归结为心灵的理性。在《判断力批判》中他又说:“崇高不存于自然界的任何物内,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里”。而王东东的诗作《西山》,是在一个“念头”之中,由于这个“念头”是以痛苦(用坠落来比喻)为基础,我们从中领略到了崇高(用登高来比喻)。在这儿,同样的“自我保全的冲动”,让王东东获得了“反抗力量”。“崇高只须在我们内部和思想的样式里去寻找根据,这种思想样式把崇高性带进自然的表象里去”。《西山》这首诗体现出了心灵的理性,和这种“思想样式把崇高性带进自然的表象里去”。诗句:“步行去对面书店,在天桥上就会瞥见西山”,“市民的骄傲,不光在家里,也在安稳的城市”,“深信人类可以改变地貌,愚公移山”,“汽车从天桥下通过,人群昏昏欲睡”,这些诗句表达出特殊的,或颇多变化的情感,让我们可以自由组成新的结合。整首诗,类似这样的诗句,体现的不是个性,也不是指哪一个更饶有兴趣,或更富有涵义;而是一种冷抒情,以接近更为完美的工具。因为是工具在帮助自由结合。显然,这种结合也不是为了形成一大套,非要让人信服的说教;而是对整个关于西山浮泛的感觉,有一种化合力,给我们一种新的,事实上是关于崇高的艺术感情。
我看到大地上冒出的工厂机械(但我反对说
大地是装置),它们的样子像笛子——
管风琴、钢琴、大提琴、小号、定音鼓……
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西山》这首诗的形态和格调,除了前面提到过的西山与客厅之外,还有诗人目前就读的北京大学、西山的游客、思想上的漫游者等等。第13节,共计12行诗,一并出现了资本人、权力人、知识人、新人、肉体人、科幻人、保护神,简直就是一幅极权时代的思想图像,各种意志和观念被强行混搭在一起。“大学饭店打烊早,女服务员不断催人”,这时,灵魂和酒鬼相伴。要知道,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中心,社会变革的发源地。王东东作为后来者,仿佛置身于一片废墟的清冷中:“黑影粘附池塘里的淤泥”,“雷电沉落的一瞬间照亮了荷花”。随着朝拜西山的人流步行,“思想、风景和人物都难以着陆”。王尔德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王东东意识到,在当代,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战争,他的诗句掷地有声:“思考,犹如治疗”。据观察者发现,北京大学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已结束于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至本世纪初,犬儒主义盛行。在诗歌写作上,似乎有一个学院派,如孤军;更多写作者堪比民间,普遍失去中心。用王东东的诗句,可称之为,“而遍布四野也是一种对抗”。这样一来,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山》这首诗的结尾,就一句:在此之前我欢乐。
从正面的意义上讲,在诗友当中,有人会认为王东东比较学院化,有历史积累所形成的小传统;能觉察到他对思想世界的着迷,和对建立一个世界的着迷,观察敏锐、系统,能沉得进去;而王东东自已,则大胆地号称执著,偏执。事实上,王东东可谓相貌堂堂,富有正气。好辩,好胜;辩论时爱把自己置于无辜的境地,然后奋起直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断其后路,抱之以爽朗的笑声。对平庸,了无新意的东西,他容易不耐烦,时有礼貌性的歉意。与人相处,偶露羞色。常深居简出,而博闻强记。
1983年阴历三月,王东东出生于河南杞县,属于中国中原地区的农家子弟。据他说,祖父辈中有懂日语的知识分子。他的祖父成分被划为富农,可见应该也受到过历史的挤压。知道了这些,也就更可以理解他写给堂伯父的诗《八月》:
我旅行。在浙江,在向东海进发的游船上,
我突然听到一阵内陆集市上小贩的叫卖声,
从无边的天空落下:你完成过多少类似小贩的愿望?!
时易世变,所以他想到堂伯父时说:“我的愤懑,并不多于死者的隐忍”。作为被改革的一代人,他似乎忘记了家族受到的压迫。但“从死亡呛人的气息中传来的”,还是“你的脸惨淡地微笑着,似仍难以接受血脉的和解”。这是他从三代人的命运中,从诗里经历到的“死去的人来和我相见”。他在写作上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风格和世界观,可以说,他是一个早慧者。他对思想潮流的敏感,问题的专注,知识体系的掌握与运用,说明在一个人有限的生命中,不管被置于何种境况,完全可以创造出自己命定的精神父亲。
我们说一个人具有历史意识,那他一定是意识到了某种群体的命运。王东东的历史感知,从而令他在写作上获得一个整体感,也就是说,他会在整体上去努力。他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诗歌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应该包括叶燮的‘理、事、情’,也即思辨、事件、情感。最终才能获得本体的充足或深化。对照可知,当代诗‘事’很多,‘情’不足,‘理’缺乏。”王东东近期的写作,力图从具体发生的事件入手,去获得超验性的感知与表达。对现实,他主张知识,然后行动。但不知道他怎样跨出这最后一步。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读书人都能感到诗人的苦闷。现实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方寸之间。仿佛,他在中心感受着人群的存在:“我的一点爱,一点恨都影响重大”。
今晚,它从书本的镇压中逃脱,
还是由无数作者的幽灵放出?
怎能不慎重:一种偏好让书架散架,
那是重力也没有做到的倾颓……
我们,与其说是要对一首诗做出评析,介绍一个真正有思想价值的诗人,还不如说是在对诗人的名声广为传播,因为这名声,并不一定就空洞无物:诗人的名声是苦恼的名声!
作者简介:陈家坪,本名陈勇,1970年4月出生于重庆。初中开始写诗。自印诗集《诗习作》、《主人与墓地》,出版诗集《吊水浒》。现居北京。
文章来源:作者微信公众号“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