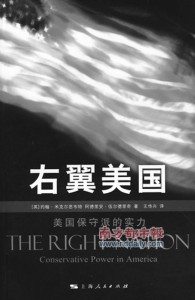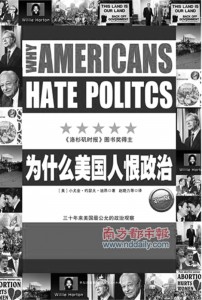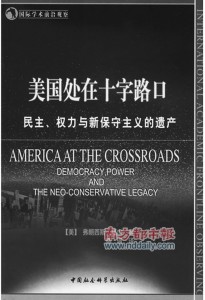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右翼美国:美国保守派的实力》,(英)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著,王传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40.50元。
《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美)小尤金·约瑟夫·迪昂著,赵晓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45.00元。
《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周琪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18.00元。
美国历史上有两场(而不是一场)内战:一是1860年代的南北战争,它改变了美国之前实行的“一国两制”,决定了之后一百年内美国的道路;第二场内战同样影响深远,但却相对地鲜为人知———那就是1960年代的文化内战。这场没有硝烟的内战孵化出一个新的美国,使它在各方面都和过去有了极大的差别(因而有本书的名字就叫作《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而且这场内战一直没有结束,因为它所激发的话题至今都仍然在争论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的主要意涵:1960年代的文化内战可能永久性地分裂了美国社会的共识和认同,使美国人围绕着一系列议题分别站在左右两边,而政治家们不是去弥补裂痕、解决争议,却相反只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一次次地重启同一批引起分裂的议题。其结果,这些议题没有得到任何新的解释和解决,只是旧有的憎恨和愤怒一遍遍地被搅起来,而左右两群美国选民之间的观点也愈加不可调和。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场文化内战的议题本身就很难给人有什么中间选择———你要么赞成,要么反对。新文化脱胎于一个富裕社会,认为公开的性欲、和平反战、平等主义都是美德,其道德命令是:“如果你感到不错,那就去做吧!”而在价值保守的美国人看来,这却是美国家庭价值观走向崩解堕落的征兆。在一个人看来是自由的爆发,在另一个人看来则是道德的崩溃。有几项备受争议的社会议题最受人关注:同性恋婚姻、死刑、枪支管制、学校祈祷、色情业,而最不可妥协的焦点,则是堕胎。在左派看来,妇女是否选择堕胎是她的基本权利;但对右派而言,堕胎则是对婴儿的谋杀。这两个立场之间没有达成一致的任何余地,双方也几乎不存在对话。
这样,这些议题实际上划定了美国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边界,政治主要变成了一个立场问题:你要么向左,要么向右。想要弥合两派分歧的结果多半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为难,不被任何一边接受。得克萨斯州议员Jim Hightower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政治格局:“在道路中间不会有什么,只会有一条黄线和一个死掉的犰狳。”
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之间的斗争,从两边的观点看,它们都是“正确路线”。那些倡导自由放任、要求允许堕胎、废除种族隔离、放宽各文化领域的限制的斗争(“别管我们”)听上去很有正当性,但反方也不无道理: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更不意味着做坏事的自由(保守主义的核心信念就是:人本身存在深深的缺陷,需要通过传统来约束他们胡作非为)。更复杂的是,很多人本身的理念也会发生变化,有句名言说:“所谓社会保守主义者,就是一个有女儿正在上高中的自由主义者。”———其意无非是:就算你年轻时向来支持合法堕胎、吸食毒品,但你现在可不希望自己的女儿那么干。
公众舆论也严重分裂了。在文化内战最高潮的1960年代就是如此:嬉皮士主导了当时的反战运动,但美国中产阶层却从来不喜欢这些人;参与反战的尽是中上层白人,但在前线作战的却绝大多数是劳工阶层。近五十年来,政治立场已经全面渗透了美国的各种媒体和传播渠道,使人们的观点更加分化:看CNN的美国人和看福克斯新闻网的人,通常在价值观和政治观点上相去甚远。
吊诡的是,正是左翼自由主义在文化议题上的胜利(成功推动妇女和黑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平等,使堕胎合法化等),导致了右翼新保守主义的反弹和崛起。在美国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几乎任何一种观点都会遭遇到它的反驳,从而保持整体的“生态平衡”。有人提出一个算数规则:反战集会上每出现一面越共旗帜,十个新保守主义的同情者就诞生了,十个已经信奉保守主义的人就更右了。尤其在美国西部和南部的白人聚居区,民主党支持民权和自由主义的立场使它的选票大量流失。事实是:自从1968年以来,保守倾向的共和党几乎垄断了美国总统这个职位长达40年之久(克林顿是期间唯一的民主党总统)。
保守主义或许赢得了选举,但在一些人(本书作者无疑是其中之一)看来,美国却失去了几十年时间。通过设定一系列虚假选择,整个国家陷入长期的意识形态争论之中,但既没有让争论获得最终的定论和平息(在民主政治中这或许也是不可能的),又延误了解决真正问题的时间。到1980年代,纠缠不休的争论已导致帮助黑人家庭的计划长达20多年不能列入国家日程,从而导致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在黑人获得平等权利之后,他们的生活处境反倒恶化了。许多美国人觉得国家过去20年被大大浪费了。
政治学者R·A·D ahl曾评论道:“所有竞争性政治的实质都是政治家对选民的贿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认定美国政治家只是不道德地迎合选民来获取选票而不去真正解决问题,可能也有点过分苛责。因为议员们也只能在这个体制的框架内进行政治博弈,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分裂的选民,如果他们不迎合其中一边,那么结果可能是得不到任何一边的选票,最终他也没有办法去解决困扰美国政治的问题。
问题在于,这样非此即彼的抽象命题框架面对的不仅是分裂的选民,而且还是观点复杂的选民:美国人既是个人主义者又是社群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喜欢“放纵”也不喜欢“自私”,他们同时信仰富有同情心的国家与自强自立。问题是一个政治候选人很难表述这样复杂的情绪,因为那会给人一种糟糕的印象:此人立场极不坚定或没有立场。其结果是一种两极化的政治对话,除了少数像尼克松那样表面极右,但事实上“同时向左向右”移动的政治家。
到1988年竞选时,选民投票率创下60多年来的最低值。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因为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大多数没有提出来讨论,许多年过去,他们发现自己仍深陷在1960年代文化内战的泥潭里。金钱却在选举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通过选举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少,相反,政治争斗通过法院裁决、国会调整、媒体披露获得解决。既然自己参与的结果不能改变什么,人们也就可以理解地表现出对政治的成熟的冷漠,转而表现出一种自恋的自我关注。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冷淡是民主政治中最值得警惕的讯号,使许多思想家为之忧虑。本书作者开出的药方是使两种价值和平共处———但现实可能更棘手,那可能要首先重塑美国的公共生活,而那,就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