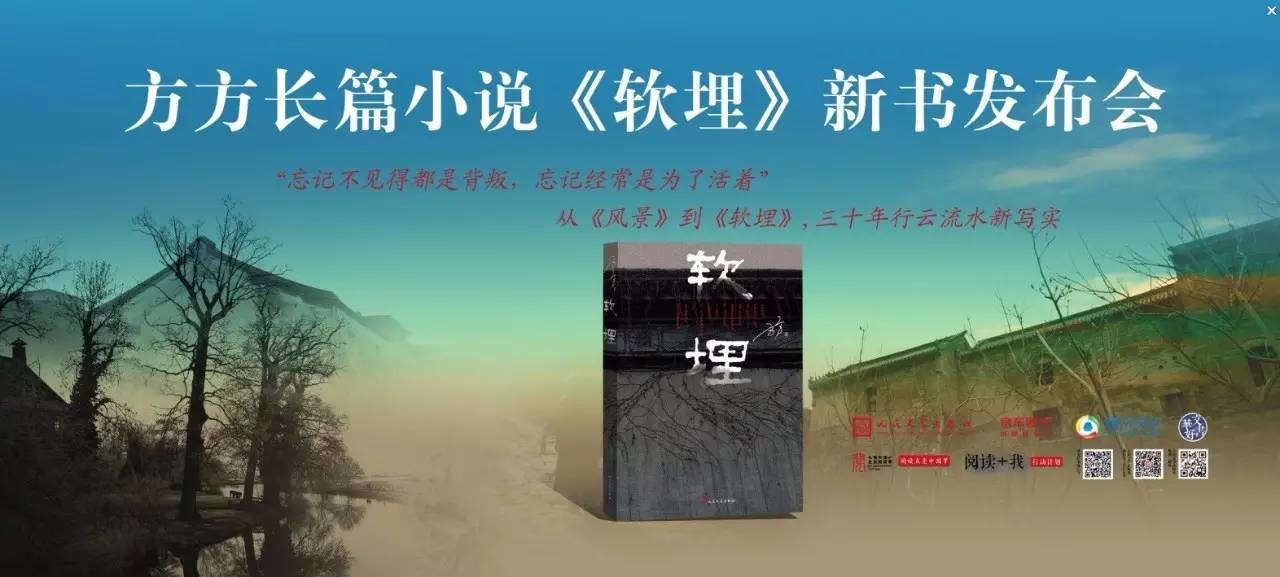第三章
第四章
17. 青林的惊愕
青林回到公司总部的当天即接到冬红电话,惊愕得手机几乎落到地上。
冬红说,老太太早上醒得晚,先是以为她头晚累了,后来发现不是。她整个人都发呆,不搭理人,怎么跟她说话,她都像没听见。跟昨天完全不同。她眼光是散的,不知道望着哪儿。有时嘴巴不停地动,像是说话,但又不发声。给她吃,她就吃,不给她吃,她就不吃。开始,大小便也不会自己上,一屙就一身。弄了几次,掌握了规律,就带她去厕所,帮她坐到马桶上。大声说撒尿或是屙(尸/巴)(尸/巴),她也还是会,但像是一个机器人。跟司机张师傅一起送她去了医院,不发烧不咳嗽,什么症状都没有,又查不出什么病。医生说先带回家观察观察。
青林一时间发蒙,不知道母亲出了什么事。他让冬红把电话放丁子桃耳边,心想母亲听到他的声音,应该会有反应。他对着手机大声叫,那头却悄无声息。冬红说:“老太太就跟没听见一样。”
青林赶上最后一班飞机回家,进门时几乎半夜了。
家里静得仿佛无人。冬红在自己房间,她关上了门。青林径直去到母亲屋里。看到丁子桃端坐在藤椅上,一动不动。青林大声说:“老妈,我回来了。”
依然无声。换作往日,丁子桃会迎上来,满面笑容,或是欣赏或是兴奋地围着他转。青林心一酸,他扑到丁子桃跟前,半跪下,说:“老妈,你怎么了?我是青林呀。你别吓唬我。你的好日子才开始哩。”
丁子桃并没有动,眼睛也没有朝他看一眼。冬红闻声而入,说整整一天都是这样。下午一直睡到五点钟,不叫她就不会起来。晚饭是我喂的,叫吃就吃,不叫吃就不吃。我没安排老太太睡觉,是想可能只有您回来才能叫醒她老人家。
青林便又大声地叫道:“妈,老妈,是我呀。我回来了、我是青林。”
丁子桃依然无动于衷。她一动不动,纵使有两个人在她的身边说话,于她来说,仿佛什么都不存在。她的眼睛望着墙,旁若无人,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能自拔。
青林急道:“你怎么发现我老妈这样的?”
冬红说:“早上十点都过了,我见老人家没动静,就过来叫她起床。结果发现她不对劲,床上身上都已经尿湿了。跟她说话,她就跟眼前没人一样。打电话给您,您可能已经在飞机上了,打不通。我急了,赶紧替她老人家换了衣服,让张师傅开车送去了医院。血压心脏都没事,也没查出个什么病来,医生说或许是受了什么刺激。又说不需要住院,没准过几天就会缓过来。”
青林摸摸母亲的脸,觉得体温正常,又听听母亲的鼻息,觉得她呼吸也还均匀,便小松了一口气,说:“也没出什么事啊,哪能受到刺激呢?难道是因为住进这新房子?”
冬红说:“是啊,我和张师傅都说没有什么事,只是搬进了新屋子。医生说,或者是换了新家不习惯。”
青林想了想,觉得母亲几十年没有自己的家了,突然这么大一幢房子成了自己的家,要说也算大事,兴奋过度也是刺激,便说:“但愿过几天能缓解吧。”
冬红说:“一整天也没其他事。只要定时叫她老人家上厕所和吃饭,她就这么一直安安静静地坐着。”
青林不解道:“这算什么病呀,老年痴呆症?那也得有个过程呀,是不是?”
冬红说:“可不?我奶奶老年痴呆是慢慢不认识人的,可老太太只一晚上就成这样了。”
青林说:“真是不明白。”
冬红又说:“对了,昨晚睡觉时,老太太就有点不太对劲。她好像管我叫小茶,还说我是她从娘家带过来的,自小在她家长大。”
青林大惊,说:“这说的什么话?”
冬红说:“是呀,我当时觉得老太太喝多了,说的胡话哩。”
说话间,冬红引领着丁子桃上厕所,又替她换上睡衣,扶她躺倒在床。然后说:“没准明天早上起来,老太太又恢复过来了。我奶奶以前常说,白天做不到的事,夜里能做到。”
青林说:“嗯,我妈以前也说过,一夜过后,人会变样。但愿她们说的都对。”
冬红指着墙角一堆纸箱,说:“老板,张师傅下午把老太太的杂物都运了回来,全放在这里。”
青林走了过去,用脚踢了踢说:“明天清理一下,把老太太的衣服都放到柜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扔掉好了。对了,那些鞋垫都留好。你现在先去睡觉吧。”
冬红应声后,便走了出去。青林拉了一张椅子,坐在丁子桃床边。他望着母亲,低声道:“老妈,什么困难你都坚持过来了,这一次,也一定能挺过去,对不对?明天早上,我想要看到老妈的笑脸。”
18. 一个藏有秘密的人
整整一夜,青林都没有睡着。他的眼前一直浮着母亲的脸庞,从年轻到年老。往事于是像一本书,在他的记忆里,随意翻页。
他从小到大的印象中,母亲就只为这个家而活。先是照顾父亲和他,父亲没了,便忙碌着他们母子的生存。他知道母亲因为当住家保姆之故,几乎没有什么朋友。父亲去世时,他刚上小学。他差不多忘记了父亲的一切,却始终保存着对父亲声音的记忆。那是父亲在世时常跟他说的话。父亲说,你长大了,无论做什么事,无论贫贱富贵,都一定要好好对待妈妈。她是个非常可怜的人,也非常特别。
以前,他从未在意父亲之语,只知父亲让他孝敬母亲。现在回想,忽然觉得父亲的话别有一番意味。母亲有什么特别呢?
还有一件事,也是青林一直有诧异感的:他家没有任何亲戚。无论父亲还是母亲,也无论远亲还是近亲,一个都没有。他的籍贯一直填的是湖北武汉。但他却从父亲和母亲的口音里,听出他们肯定不是武汉人。父亲有明显的北方腔调,而母亲说话则带有西南方言的尾音。大学时,有一次跟同学谈及此事,同学还笑说,没有亲戚,难不成你父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他问过母亲的老家在哪里。母亲说,就在武汉。他又问母亲,那你的武汉话怎么讲得不标准?母亲说年轻时一直在外面,后来给人当保姆,雇主都是北方人。他说,武汉怎么没有一个亲戚?母亲说,有你一个就够了。他说,我不是亲戚,我是亲人。母亲说,一个亲人顶得了一百个亲戚。
如此,他们的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后来青林忙碌自己的事,也无暇顾及打听这些。
现在,也就是昨天,母亲居然说起了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喜欢画鬼谷子下山?设若如此,母亲至少不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她的童年和少年是怎么过的呢?如果她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她怎么没有去读书?他居然也从未听母亲谈及过她自己,仿佛她不曾有过年轻的时候。
母亲识得一点字。青林是知道这个的。据说是在五十年代扫盲时所学。所以,母亲平常不读书不看报完全可以理解。但母亲怎么会念出那么雅的诗呢?“窗前一丛竹”,青林想起了这句。这是母亲看到门前的竹子,脱口而念的诗。
青林的脑子突然冒出个念头。他打开电脑,敲下了“窗前一丛竹”五个字,紧跟着跳出了“清翠独言奇”。他记得母亲念的后一句,正是这个。更令他发怔的是,他看到了“谢朓”二字,而母亲所说“谢朓的”声音也瞬间在耳边响起。他有一种非常的讶异感。
母亲居然知道谢朓。这个南北朝时期的诗人,用流行语说,是个冷门诗人。就算读了大学的青林自己,也从未听说。但是,识得少少几字的母亲却知道;非但知道,并且还能见景而脱口说出他的诗句。
母亲更多的异样,在青林脑海中一一浮出。母亲看到新房子,说了一句什么庐。且忍庐?还有个什么堂?母亲看到瓷瓶上的画,马上说出鬼谷子下山图。看到床上紫色的被面,又说,应该是红色的。母亲还说什么枪托打她的背,很疼。还有,适才冬红所说的关于娘家带过来的小茶,等等。这一切,都让他感觉到母亲十分陌生。昨天他还以为是自己对母亲了解太少,此刻,他却蓦然觉得,他的母亲,他的这个陷入人事不知状态的母亲,因了某个事情,已然发生了惊天异变。她并非是他心目中原有的那个母亲。她似乎是另外一个人,一个藏有秘密的人。这秘密使她有如一本大书。他此前所知,只是书的封面,而这本书的内容,他却从来未曾翻阅。
19. 她的灵魂不在现世
青林眼前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母亲能清醒。但他每天早上进到母亲的房间,看到的仍然是那一张呆滞的面孔。不哭不笑,没有任何表情。睡着了和醒着的差别,就是眼睛的张开和闭合,其他完全一样。
青林的生活呈现出一种乱象。他带着母亲四处问医求诊。拜了佛,也求了道。和尚做法,道士打醮,折腾了几个来回,甚至还请了大师来家里驱邪。人民币花了几十万,母亲却依然故我。
有一天,他的大学同学龙忠勇带父亲从上海回贵州老家,途中绕了一下,想去黄陂探望一下早年嫁在那里的姑姑,欲在武汉逗留一两日。青林便拉他住到家里。青林说:“讲什么客气?以前一个寝室也住多年了。住家里用车方便,也好聊天。”
龙忠勇觉得青林是真心,果真就带着父亲住了过来。龙忠勇的父亲患老年痴呆症有三四年了,他亲眼见到自己父亲慢慢的变化,却就此无奈。龙忠勇说:“那么智慧的一个人,变成这样,心里那份难过,真是无法言说。”
青林坐在客厅里跟龙忠勇诉说母亲的病状,说他原本一心想让母亲过得幸福。结果母亲来到新居,只一夜,便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不与现世任何人沟通的人。青林说完欲哭无泪,又道:“我妈妈如能像你爸一样,给我一个过程让我慢慢难过,也让我好受点呀。”
龙忠勇的父亲呆坐在旁边,一直垂头看着地面。这一刻,他突然说:“她的灵魂不在现世。”
他的眼睛仍然盯着地面,望都没望青林一眼,声音却响亮得有如人在敲钟,八个字的音响仿佛从地面弹到上空,嗡嗡地在客厅回荡。
青林和龙忠勇都大惊失色。龙忠勇说他的父亲已经很久不说超出三个字的话了。又说,他的父亲初病时经常说,他正在脱离现世,去另外一个世界;还说他在路上慢慢走。龙忠勇说:“他们所理解的可能跟我们常人不一样。这样的状态,或许是他们自己的意愿,而不是病。”
青林被龙忠勇和他父亲的话震到了心。他想,也许是,可能是,真的是。她不是病,她只是让自己的灵魂到另一世界走走,去看看那边的人事。之后,也许还会回来。不然,怎么理解母亲除了不理旁人旁事,只是沉浸在自己世界里,其他什么症状都没有呢?生命的需求,吃喝屙撒睡,一切都正常。
青林有一种释然感。他想,那么就听其自然吧。他还像以前一样努力工作,像以前一样好好生活。这也应该是母亲所希望的。
于是,他真的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像陀螺旋转一样忙碌不停的从前。
照顾母亲的事,便全都拜托给了冬红。冬红的工作倒变得简单起来。她除了打理屋子和花园,对于丁子桃,则只需按时喂饭,定时如厕,隔上几天,更换一下衣物,其他倒也没什么更多的事情。
20. 一只破旧的皮箱
有一天,青林回家,看到门口扔着一只很陈旧的小皮箱,深棕色,皮箱护角的铆钉业已生锈。青林觉得有些眼熟。这份熟悉非常遥远,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于是叫过冬红询问。
冬红说:“我今天清理老太太的东西。这小箱子放在一个纸盒里,上面还放着棉被什么的。我连盒子一起给收破烂的。可是那老头非要一样样拣出来重新打捆,这才发现里面有只皮箱。老头说,破箱子没用,要我给他,我没答应。箱子还锁着哩。”
青林突然就想了起来,这只皮箱在父亲去世后,母亲郑重其事地将它置放在衣柜顶上。母亲说:“这是你爸爸的东西,他一直锁着,也不知道是什么。他以前说过,等他死了,再交给儿子。你最好等我也死了再去看它。”
这么多年,他们早没了自己的家,青林也将它忘了个干净。这一瞬,母亲站在板凳上举它到头顶,一边摆放一边扭头跟他说话的场景,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种感觉,有一些亲切,又有一些玄妙。青林说:“这是我父亲的遗物,你放它到我房间去吧。”
晚上,青林先上网,用邮件写了几封工作函,又跟儿子打了一阵电话。然后到母亲房间,坐在她的床边,向她汇报自己一天的工作感想。他听同事说,一个植物人因为天天听到亲人的声音,有一天突然苏醒过来。青林觉得,如果他天天跟母亲说话,或许有一天她也会醒来,见到青林,她会高兴道:“嗨,青林,睁开眼就能看到你,我太高兴了。”
青林说着说着,突然想到箱子。他赶紧到自己房间,把箱子拎到母亲面前。箱子居然有点沉。青林举着它说:“妈,你看到了吗?爸爸的皮箱。我刚发现的。那里面装的什么.你知道吗?箱子的钥匙还在不在?”
青林面对的,仍然是母亲均匀的呼吸。这世界的一切,似乎都与她无关了,包括她曾爱过的两个人:她的丈夫和她的儿子。
青林决定打开箱子看看。他找来螺丝刀,撬开箱锁。箱子表层有几本翻旧的医学书,想必是父亲当年所读。而书的下面,居然全是笔记本。青林有些奇怪。他翻了翻,其中一部分是父亲的医学笔记和后来在医院的工作笔记。另一部分竟是父亲的生活记录,像日记,但又不是。有的写着日期,有的只写着年份和季节。想来是有年头了,字迹已显得非常陈旧。
青林心里突然涌出一些激动。他想父亲的这些记录里,会不会有着母亲的秘密呢?他好奇起来。便索性坐在地上,按照父亲日记本右上角的序号整理起来。
这些记录的起止的时间是从1948年的秋天到1966年。想必“文革”开始后,父亲就不再记录了。
青林伸出手打开第一本,他想从头读起。待他眼睛落到那一行行业已褪色的钢笔字时,突然间,他有些惶惶然。他不知道这里面记录着什么。不知道会不会从中看到他完全陌生的父亲和母亲。这种陌生,会不会对他的人生带来冲击呢?一种莫名的害怕,从他心里涌出。他想,当年母亲为什么要说,等她死了再去看它呢?
青林的心莫名地咚咚乱跳,他犹豫片刻,把日记放回箱子。他想,我恐怕还没有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