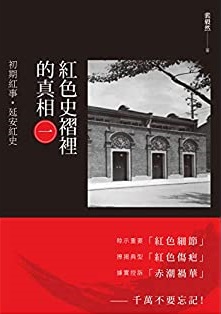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2)
《红色史褶里的真相》第一辑: 初期红事(2)
张申府与早期中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李大钊率先发表三篇介绍共产主义的文章——〈俄法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言治》)、〈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1918年11月《新青年》),共产主义赤色思想在京沪知识界开始流播。不过,及至1921年俄共一手扶立中共,赤火微如星粒。五四时期,共产主义在中国不过是北京大学两间小屋。校长蔡元培秉承“兼容并包”,为李大钊师生提供讨论交流的场所。 [1] 中共“一大”召开时,各省代表赴沪川资100元,出自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供的经费。[2]
北京三党员
那么,哪些人是中共最早党员呢?无论中共党史及市井坊间,一直不甚了了。事实上,中共最初实际创建人为三位:李大钊(1889~1927)、陈独秀(1879~1942)、张国焘(1897~1979)。张申府(1893~1986)乃北京小组最初三成员之一,另两位为李大钊、张国焘。根据多方材料印证,张申府这段晚年回忆大致可靠:
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开始创建,地点在上海和北京。在上海是陈独秀,在北京是李大钊和我。第三国际的魏金斯基当时来华,首先到北京,对我们讲,要我们建党。以后魏金斯基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陈独秀找过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谈过,他们都不同意。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李守常(按:李大钊)。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3]
河北献县小垛庄翰林之子张申府,原名张崧年,哲学家张岱年(1909~2004)长兄,周恩来入党介绍人。1962年3月2日,周恩来(1898~1976)在广州接见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当众向张申府、刘清扬夫妇示谢:
1920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4]
大革命发动之初,远在欧洲留学的周恩来之所以得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亦赖参与黄埔军校筹建的张申府向廖仲恺、戴季陶推荐。1925年,张申府因政治观点不合退党,转回书斋,从政治前沿舞台隐身淡出,社会知名度较小。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以学者身分在储安平《观察》上发表〈呼吁和平〉,要求国共停战,被认为有意袒护败势已定的国民党,遭到中共严厉批判。相恋27年的妻子刘清扬(1894~1977)登报斥为:“人民公敌张申府”,与之离婚。民盟也将自己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开除出盟。
1950年代初,章士钊替张申府当面向毛泽东求情,要求安排张的工作,参与政事,未获允准。1957年,张申府因支持章伯钧,划“大右派”。此后,张申府彻底淡出历史舞台。1980年代初,极左思潮败落,张申府“重出江湖”,成为“出土文物”,全国政协委员,其建党初期回忆录亦被中共接纳,十分珍贵的史料。
上海七党员
关于中共初始党员还有一说:茅盾乃最初七党员之一。此说有一定偏差。根据张申府回忆,因犯“生活错误”被逐出北大的陈独秀,这时去了上海。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一译维辛斯基,华名吴廷康),首先到北京与李大钊取得联系,提出建党设想,然后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
陈独秀热情极高,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留日生,其中有周佛海(1897~1948)、田汉(1898~1968)、李达(1890~1966),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1899~1970)、沈雁冰(1896~1981)、沈玄庐(1882~1928)。[5]
张国焘回忆录中,上海小组成员则为:
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玄庐)、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入组织。杨明斋由俄共党籍转入中共为党员,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一样,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两相对照,张申府其时不在上海,提供的名单准确度不高。张国焘因参与其事,提供的“上海小组七人名单”相对准确。应该说,茅盾是中共最早党员之一,但非最初“上海小组”七成员。
还有人说李震瀛(1900~1938)、陈公培(1901~1968)等人也是上海共产党小组发起时首批党员。陈独秀告诉张国焘,上海小组正式成立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正式表达加入组织的意愿。《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后为国民党理论支柱)表示自己与孙中山关系深切,不能成为中共党员,还哭了一场,说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不能如愿以偿。邵力子则正式加入。《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1886~1973)在酝酿之初也一度是活跃分子,但接触到组织原则与政治纲领后退出。张国焘回忆录认定中共最初诞生于上海,1920年5~6月间商谈筹备,8月下旬正式组建“上海小组”。
据张国焘回忆录,李大钊对立即建党有不同意见,认为暂时不应过问实际政治。1920年7月,陈独秀与张国焘在上海具体讨论建党细节,长谈中对具体而又重要的党纲政纲,深感茫然。
我们虽否定了李大钊先生所谓暂不过问实际政治的说法,但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习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6]
陈独秀与张国焘的讨论中,只是确定一些基本原则,如不采用党魁制而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不吸收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者加入等。
北京小组
北京建党稍晚于上海。1920年8月底,张国焘自沪回京,向李大钊汇报上海小组成立情况。李大钊听后认为在北京也应发动起来。张国焘说是他与李大钊“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 [7] 张申府则说1920年9月底,自己与李大钊在寻找发展“第三名党员”,首先想到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女性刘清扬。
刘在天津组织女界爱国同志会,领导天津青年团体“觉悟社”,1919年代表天津学联到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1920年6、7月间,她又参加学联组织与张国焘等人下南洋募捐。1920年9月,当刘清扬到达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动员她加入共产党。刘清扬个性独立,认为对党组织还不太清楚,要看一看,没同意。李大钊、张申府认为入党之事不能勉强,只能等刘有了认识与觉悟后再说。这样,李大钊再去找自己学生张国焘,因为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可能性较大,这样“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张申府说北京小组成立时间为1920年10月,此后李大钊发展一批北大学生——高语罕(1887~1948)、刘仁静(1902~1987)、邓中夏(1894~1933)、罗章龙(1896~1995)[8] ,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这批无政府主义者因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同年11月退出中共。[9]
张国焘回忆录中却说北京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于1920年9月中旬,到会者九人——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9月底,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在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到会者约40人,著名者: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等。无论如何,从时间上,“北京小组”的组建略晚于“上海小组”。
张申府认为北京建党设想与创始成员要早于上海,最早的两名中共党员应产生于北京——李大钊与自己,不是李大钊与张国焘来“发展”自己,而是自己与李大钊去“发展”张国焘。但根据张国焘赴沪日期,应该是李大钊与张国焘去找张申府,而不是倒过来。在此,张申府如果不是回忆有误,便是有点“贪功”。
1921年1月,刘清扬成为张申府情侣,与张申府同船赴法留学,并由张申府介绍入党。2月,两人再介绍周恩来加入,这样留学生中有了三位党员,成立中共旅欧支部。这只是一小群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自由组合,参加者并没有放弃旧有的组织与思想。其实,张申府的思想一直十分杂芜,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跳来窜去,还提出“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他毕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最新理念结合起来,尝试将儒家人文主义和罗素的数理逻辑建立共同立足点,以便东西新老文化能够达到他所希望的交融合流。张申府这一学术大方向还是正确的,“三流合一”在学界后辈中得到某些呼应。
中共建党初期,规模很小,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圈,真正发展要到1924年以后的大革命,独立发展则在1927年“四·一二”后。至于中共增员幅度最大时期,乃是抗战时期(1937~1945),三万余党员跃升120万。[10]
张申府退党
1920年9月20日,张申府致函少年中国学会:
吾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对于社会的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精华,对于共产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吾绝对信奉如要把现状改换,只有换改一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11]
按其思想,实在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他的退党,在于他的性格与“知识分子脾气”。
张氏退党,起因于1925年1月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要求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领导。张申府在这一点上与张太雷、彭述之、蔡和森等发生严重分歧,争论激烈。张申府知识分子脾气发作:“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 [12] 扔出此话,见自己确是少数,张申府甩手而出,盟友周恩来随他离场以示支持。但周恩来在门外劝阻张不可因一时冲动而退党,必须遵从党纪——返回会场商讨共同立场,适当妥协以求转寰。张申府不肯回头,怒然拔步,周恩来则返回会场。张申府晚年回忆:
我终于离开,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13]
1978年,张申府回忆中共“四大”为一篇党的纲领发生争论:
我认为那篇纲领,是绝对不妥的。有些年青党员乃说我幼稚可笑。我一气之下,表示退党。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14]
此后,张申府接受罗素思想,1928~29年组织第三党,要求独立国共两党之外,获得自由政治空间。1925~26年,张申府撰文:
我现在所要努力,究不在单纯的赤化上。我相信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要从人性上做点改人性的预备,从旁帮那直去变制度的。[15]
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16]
但第三党的活动并不如意,退出政界的张申府转入思想界,1930年代初为清华哲学系教授。1935年,日寇既得东北再窥华北,国势日危。张申府与刘清扬、姚克广(依林)、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张申府任大游行总指挥,1936年3月被捕,出狱后被清华解聘。抗战胜利后,张申府代表民盟出席政协。1946年国民党召开“国大”,张申府拒绝出席。1948~49年,张申府本有许多机会去香港,但他实在舍不得北京这块“牵系其根”之地,留了下来。
1949年后,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张申府被禁止发表文章和从政。此前,他之所以改名(“崧年”一名已用20年):
因为有许多官宦人家的儿子都用了这个名字。我是喜欢有分别的人,于是我再起了一个名字:申府,这是参照古时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官的名字起的,意思是治理国家。[17]
不能参政,十分憋屈。章士钊为他求毛泽东缓颊,老毛未允,说了一句:“当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张申府认为这是毛还惦记着1918年与1945年的两件事。1918年暑假,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回昌黎老家休假,助教张申府代主馆务,正值毛泽东入馆任见习书记。张申府拿一份书目交毛缮写,毛写完后交上,张一看,全写错了,退毛重写。1945年,毛泽东飞渝谈判,请张申府吃饭,席间张拿出自己的一本著作赠毛,毛见扉页上题词“润之吾兄指正”,顿露不悦。毛泽东认为张申府此时已不该与自己“称兄道弟”。
1949年3月25日,民盟成员宋云彬(1897~1979)在日记中评张申府:
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张申府于政协失败后,不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处捐款、以饱其私囊。彼苟不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岂肯出此。[18]
可见,张申府其时口碑不佳,处境尴尬。1949年2月,周恩来派秘书齐燕铭安慰张申府,每月送30元生活费。北京市长彭真亦请张申府吃饭,席间替他惋惜:“你要是不脱党就好了。”[19] 9月2日,张申府在北京副市长张友渔安排下,入北京图书馆任职,直至辞世。 张申府晚年说自己一生摔了三次大跟斗——1925年退出中共、1948年被逐民盟、1957年被划“右派”(此时仅为“农工民主党”中委)。
三好男人
1980年3月,87岁的张申府向美国女学者舒衡哲坦认自己是“三好男人”——好名、好书、好女人。
您知道,我有三个弱点,这就是我终生追求的三个爱好:书本、女人和名誉。1920年代我刻了一个章,就是刻了这三好。这三好我从没有放弃。我爱书,1948年我为这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爱女人给我的麻烦就更多,像刘清扬和其他女人。这三好使我难为情,但我不能自拔,没有办法。到现在还是这样。[20]
1926年3月,张申府在那篇〈自白〉中谈及与刘清扬的同居,观点至今十分前卫:
我和刘清扬的关系并非什么新鲜的事情。今天只有在中国才不能够承认一个已结婚的人还可以有爱人……我的意见是,性交、结婚和爱情是三桩不同的事儿。[21]
舒衡哲认为张申府“是他那一辈最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之一”。
说来令人惊讶,武昌首义后,入读北京顺天高等学堂的张申府,言出惊人。一篇命题作文〈拟官军谕武昌城内叛兵缴械免罪檄〉,要求学生以清军平叛将官身分写一篇战前檄文,测验学生对十九世纪国史的认识,特别是洪杨发逆引起的社会动荡。18岁的张申府当时不可能有革命意识,他从儒家立场出发,嘲笑“造反即英雄”,表述了以下内容:革命者并不具有代表人民利益的天然性,甚至并不比当权者更能代表人民利益。[22]虽说有点“瞎猫碰死耗”的偶然性,但也确实裹带十分深刻的历史内核,表明青年张申府的思想潜质,是他日后之所以步入哲学研究的“内因”。
2006年秋,上海·三湘;增补:2008-12
[1] 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页179。
[2]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页368。
[3]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载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220。
[4] 周恩来:〈论知识分子问题〉(1962年3月2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页357。
[5](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08。
[6]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一册,页101~103、95。
[7]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一册,页105。
[8](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09。
[9]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一册,页105。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页139。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北京)2008年,页56。
[11] 张申府:〈给少年中国学会的信〉,原《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1920-9)。收入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144。
[12]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554。
[13](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7。
[14] 张申府:〈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554。
[15] 张申府:〈报凯明先生〉,《京报·副刊》1925-8-19。转引自(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88。
[16] 张申府:〈自白〉,《京报·副刊》1926-3-14。转引自(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90。
[17]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24、29。
[18] 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115。
[19] 章立凡:〈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社会科学报》(上海)2004-12-16。
[20]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20。
[21] 张申府:〈自白〉,《京报·副刊》1926-3-14。转引自(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190。
[22]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李绍明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页24、30。
原载:《南方都市报》(广州)2014-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