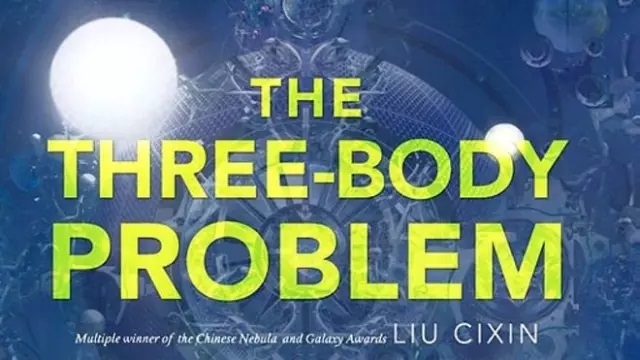近十年来,科幻小说《三体》风靡中国,漫卷世界。它的成功不仅在于让中国作品历史性的获得了世界科幻界最高奖项–雨果奖,更在于辉映、激发和宣示了一代国人(或者至少是很大规模的某一批某一类国人在某个特定时间段)的价值取向,在国人尤其年轻人中实现了一种广泛而颇有深度的共鸣。而作者刘慈欣,也成为了《三体》粉丝们的超级偶像,对其的膜拜、维护也达到了其他任何当代作家都难望项背的程度。
我自己阅读了《三体》多次,基本上可以说一句不落、没有忽视任何情节的看完了,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对作者刘慈欣的背景、言论、价值观念进行了有限但已相对充足的了解。相关结论本应在本文末尾讲,但不知本文何时才能完成,且需要先说个大概评价。所以,我先在本文开篇即此处对《三体》及刘慈欣做出整体上的评价。
《三体》一书假借科幻性质的人类与外星文明的斗争故事,反映了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一些本质特点,以及对人类乃至宇宙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对未来的预测,有着丰富的文学、科学和哲学思考,表现了作者深邃的洞察力、想象力,还有对其所揭示东西通过科幻化方式进行建构、喻示与表达的强大能力。但是,作品及作者的感情倾向和暗示的价值取向整体上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化的、非同情非人道非博爱的,贬抑进步主义与社会公正的,作者个人品格与道德操守也很有问题。该作品的水准可以跻身世界上从古至今数千部具有重大价值、启示和有影响力的文学著作中,但其暗示与导向的价值观念、蕴含的道德价值与人文精神,却完全不能与那些并列者比拟,甚至说是一种负面的有害的道德与人文价值。这是我的大略性评价,更具体的评价在文中和文末再写。
《三体》篇幅阔大、细节密麻,我自然无法在此做重述。因此,我写这篇书评,是预设读到本书评者通读过《三体》的基础上的。不过,我还是会在评议中夹杂一些背景和情节介绍,如引用《三体》原文,让本文能够被未读(起码未细读)《三体》者也能看懂。为方便行文,我会以《三体》人物和事件在书中提及的次序为序,以这些人物和事件为单元论述分析,并加以适当的总结与综述。
我会在文中对刘慈欣写作内容的情感、动机做出大量的评断。这种评断当然不可能有法律意义上的“确凿”证据,反而非常需要依靠推测和联想。而且,这种评断也不可能100%吻合刘慈欣的本意,也没有人有这样的本事,除非有人可以探测出刘慈欣的大脑在想什么。还有很多评断是基于刘慈欣和他的《三体》的客观影响、读者反响。一个作品表达的是什么意义,很大程度在于有自由表达权的读者中的主流所认为的意义(尤其在作者有能力否认却没有否认、否认但是不符合逻辑的情况下)。作者和读者、作品和反响是互动的关系,而非单向的灌输意义。作者在写作时也应该考虑到它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包括自认为的被“误读”。所以,我会通过它在读者中的认知和影响,反推刘慈欣在《三体》中内容情感为何,这并不是故意冤枉他。
还有,本文作为评论性的文章,当然以批判为主,即便我对刘慈欣的一部分观点赞同,也不会大篇幅的提及。对于刘慈欣塑造的一些争议不大的人物形象(或者说至少我觉得没什么特别需要批判的),如章北海、罗辑等人,以及一些没有特别喻示意义的事件、情节,也就不会费多少笔墨。我写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有异议的那部分。而从整体上,如前所述我赞扬其“能”批判其“德”。
(一)史强
《三体》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科学家汪淼,但第一个细致刻画的人物则是前来约谈汪淼的警察史强。寥寥几页,就刻画了一个粗鲁野蛮、具入侵性的人物形象。熟读《三体》的铁粉当然知道,开篇对史强的描写,以及后面类似的描写,都是在反衬史强精明强干、充满勇气与责任心做铺垫。
或者更准确的说,刘慈欣故意将奸狡顽劣与能干及有责任心联系起来,暗示有流氓习气的人物往往是“外冷内热”,本质是好人。
我们截取对小说中史强的描述,可以看看刘慈欣想表达、试图灌输一种怎样的价值观。
在《三体》开篇,史强与汪淼见面时:
(汪淼说)“‘科学边界’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组织,成员都是著名学者。这样一个合法的学术组织,我怎么就不能接触了呢?”
“你看看你这个人!”史强大声说,“我们说它不合法了吗?我们说不让你接触了吗?”他 说着,刚才吸进肚子里的烟都喷到汪淼脸上。
……
“我有权不回答,你们请便吧。”汪淼说着要转身回屋。
“等等!”史强厉声说,同时朝旁边的年轻警官挥了一下手,“给他地址和电话,下午去走一趟。”
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在稍后汪淼被三体人制造的幻象打击的几乎要自杀时,用巧妙的方式让汪淼鼓起了生的勇气,并振作起来参与破获了地球三体组织(ETO)的阴谋。再往后,史强还出奇策(即“古筝行动”)伏杀了伊文思和“审判日”号,以及多次搭救、保护了另一个科学家罗辑,可谓居功甚伟。此外,刘慈欣还描写了史强与汪淼、罗辑的深厚友情。正是在史强的鼓励下,汪淼才重新鼓起生的勇气,并且帮助政府和军警破获了“地球三体组织”的一系列罪案;对罗辑而言,史强更是挚友,一直保护罗辑,并且促使他有放荡不羁到负起保卫人类的责任。
我们一开始看到史强的形象,很像现实中滥用警权、欺压百姓的恶警。书中也的确列举了他的劣迹:处理劫持人质事件时不顾人质安危、鼓动黑帮黑吃黑、刑讯逼供……这样的“恶警”却挽救了一个重要的科学家,进而挽救了人类的命运。
刘慈欣在这里的暗示就是,德行不是重要的,才能才是第一的;滥用职权、违法乱纪没关系,最重要是“有用”。而且,这样的人虽然对陌生人、敌人残酷,但对待朋友还是可以肝胆相照的。更进一步,刘的春秋笔法在暗示,恰恰是史强这种恶人,才有常人所没有的狡黠、胆识、才华,彬彬有礼、遵纪守法的人反而做不到。这就很容易得出一个推论:人们要容忍恶人、恶警,容忍他们的不法行径,因为只有这样历经丑恶、一身匪气的人,才有保护我们的能力。或许,这正是刘慈欣想传达给我们的。这在《三体》中并非孤例,后面还有一些人物如托马斯维德,可以证明刘这种隐隐的暗示。
在全书中,还有许多对史强的正面描写,如前面提到的讲他和汪淼、罗辑的友情,可谓很感人。刘慈欣试图将史强的流氓色彩与侠义之心都强化起来,让人们形成一种印象,即这种看起来很坏(实际也有明显坏的一面)的人本质上是好的,人们应该理解、容忍、欣赏、赞誉他们。这有点像《水浒传》对那些既行侠仗义又杀人越货的好汉们的描写。不过水浒里那些“好汉”是反体制、反强权的人,刘慈欣笔下的史强和托马斯维德则都是穿着官衣、维护秩序的统治阶层,还都是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水浒传》歌颂的是反抗精神,《三体》则是赞扬“压迫精神”。且无论刘慈欣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为国家强力部门人员洗了地是事实。大多数文学作家都会在字里行间谴责暴力机器的野蛮、统治阶层的肮脏(包括格调并不高的黑帮小说《东北往事》,也是先谈了干部阶层的贪腐乃至政权对民主抗议的镇压,再讲民间社会的黑帮暴力),只有刘慈欣这样的会变着法的为体制及体制的附着物唱赞歌。
另一段对史强的描写,不仅再次充实了史强这个“流氓警察英雄”的形象,还透露了刘慈欣对社会中相对边缘的、不幸的家庭受害者的污名、怨毒心态。书中有一段史强与军警突袭ETO会议,遭遇一个年轻女孩持炸弹威胁时的情景:
“站住。”核弹女孩向大史抛了个媚眼警告道,右手拇指紧按在起爆开关上,指甲油在电筒光中闪亮着。
“悠着点儿丫头,有件事儿你肯定想知道。”大史站在距女孩七八米远处,从衣袋中掏出一个信封,“你母亲找到了。”
女孩儿神采飞扬的眼睛立刻黯淡了下来,但这时,这双眼睛真的通向她的心灵。
大史趁机又向前跨了两步,将自己与女孩的间距缩短至五米左右,女孩警惕地一举核弹,用目光制止了他,但她的注意力已经被大大分散了。刚才扔掉假核弹的两人中的一个向大史走来,伸手来拿他举着的信封,大史闪电般抽出手枪,他抽枪的动作正好被取信的人挡住, 女孩没有看到,她只看到取信人的耳边亮光一闪,怀中的核弹就被击中爆炸了。
……
“那个女孩子是谁?”汪淼问。
大史咧嘴一笑,“我他妈的怎么知道,瞎猜的,这样的女孩子,多半没见过妈。我干这行二十多年,就学会了看人。”
在刘慈欣笔下,妄图破坏现行秩序、采用极端手段对抗主流社会的人,往往都是社会的受害者、边缘人群(当然客观上也的确是这样)。而且,从上面借史强之口说出的对女孩的评价及语气,可看出刘慈欣对其并非抱以同情而是鄙夷、厌弃。这种语调就像保守社会里对被性侵的女性那样,不是深表同情,而是觉得受害者“脏”。在刘慈欣们眼里,这些走极端的、闹事的、反抗秩序的,就是被家庭抛弃的、“没妈”的可怜又可恨的虫子。
而这是很符合如今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浪潮下的价值观的。每当社会上发生极端事件,互联网上都是一片“我不想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只想要他死刑”的声音,仿佛有罪的不是蔡京高俅,而是杨志林冲(当然严格来说杨志林冲的确有罪)。而对于那些采取和平抗议、正规渠道上访的可怜人,人们也个个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受害者遭受苦难,而是高高在上的鄙视、排斥之,不仅不觉得自己要负上某种责任、参与社会某种必要的改变,还觉得这些弱势者碍了自己眼、影响了自己心情。刘慈欣的《三体》大火,正在于字里行间和中上阶层社达化利己主义化的心态形成互鸣。(当然我并不赞同伤及无辜,而且认为一旦做了这种事,无论原因如何都需要承担责任而不能脱罪,但是讨论原因和解决问题哪怕缓和矛盾,都是必要的,而不是只凭借暴力威压、灭杀反弹)
《三体》中史强这样的人物,欧美日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也有许多形似神也似乎似的形象,即一个看似不正派(或者也的确不正派)的人却在重要事情和生死关头表现出超凡的勇气与责任心,以反映人性的复杂、人性的光辉。但是仔细分析和感受,就会发现其实《三体》中史强、托马斯维德、罗辑等这样的形象及塑造目的,与大多数欧美日韩作品并不相同。后者(例如契诃夫、莫泊桑、雨果、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刻画的似乎相似的人物)是为了反映人性的复杂、正义的光辉,前者则更像在为强权与恶人洗白,在为压迫者与既得利益阶层贴金。这可以通过字里行间的感情倾向、细节描写、整体环境乃至作者的创作背景及可能的目的等,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推测,当然读者自身的价值观和经历也会引起不同感受。饱读中外文学与影视作品的,至少有一部分人应该会产生这种共鸣。
例如雨果最知名的著作《悲惨世界》,刻画了冉阿让这一“罪犯”身份的角色。但雨果并未将冉阿让描写的像“炸弹女孩”这样让人厌弃,相反刻画的颇为令人同情。而执行法律、抓捕冉阿让的沙威警长,并不像史强那样因坏而“酷”、坏的令人佩服,反而被雨果刻画的让读者感到痛恨。最后,沙威警长也良知苏醒,与冉阿让共同完成了救赎。在《悲惨世界》中,每个人都良心未泯,且正是由于都保有底线,乃至在可以达成目的时故意“放水(如沙威放走冉阿让)”,才让“悲惨世界”以走向光明而落幕(而非让法国乃至世界变成“黑暗森林)。
而莫泊桑的《羊脂球》、契诃夫的《万卡》、鲁迅的《祝福》,都以刻画一个弱势受害者为小说主题,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对当事人深深的同情,并将她/他们的遭遇归于环境的恶劣尤其他人的无情,鞭挞了社会的丑恶、纲常的虚伪。这三位作家的更多作品,也都是如此的感情倾向和道德立场。这与刘慈欣鄙夷乃至讥嘲弱者、称颂恶人、赞颂秩序的态度截然相反。
不仅这些名家名作如此,即便是一些并不那么伟大的文艺作品,也会保留许多基本的“人味”。例如曾经风靡中国的刑侦剧《重案六组》,里边的警察也是个性各异,但也都保留起码的人性良知。或许三体中史强的形象更符合部分警察的真实面目,但显然不应以称颂和鼓励的态度刻画之。《重案六组》中的警察或许理想化了,但这样的文宣也可以对警察队伍形成一种有益的引导,而非邪恶的暗示。
(二)文革
《三体》中提及文革,被一些书评人当成当代文学作品一大突破,也成为《三体》一大卖点。一些不怎么了解详情的人,还因此以为刘慈欣是敢于触及敏感问题、反思历史的伟大作家。据人推测,当年《三体》第一部获雨果奖,可能就与书中敢于提及这一中国的政治禁忌有关。
的确,文中提到的疯狂岁月、武斗场面,尺度之大令人震惊。在中国公开发行的畅销文学作品中,鲜有如《三体》这样直接的呈现惨烈的文革情景。书中也描绘了对知识的摧残、对学者的迫害,以及政治斗争下家庭离散、朋友背叛的人伦惨剧。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现象、现象。本质呢?原因呢?是谁造成了这样的悲剧?刘慈欣在书中和现实里都不曾对酿成文革的这个政权、这个统治集团做任何的不利评判。在描绘文革中种种现象的同时,完全回避了对相关的制度、人物、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只有陈述现象,这种陈述方式和语气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是一场历史中注定发生的悲剧,没有责任人。
如果刘慈欣对文革的冷静叙述还不能完全说明其政治态度,那么他对文革“始作俑者”的态度,足以反映问题了。
在关于“红岸基地”的一些文件中,我们可以找到一段显然暗示是毛所写的批语,摘录如下:
“【批示】已阅,狗屁不通!大字报在地上贴就行了,不要发到天上去,文革领导组今后不要介入红岸。这样重要的信件应慎重起草,最好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还有这一段:“这个年代,要搞倒一个位置很高的人,就要在其分管的各个领域得到他的黑材料,但两弹工程对阴谋家们来说是个棘手的领域,这个工程处于中央的重点保护之下,得以避开“文革”的风雨,他们很难插手进去。”
又是那套“都是底下人办坏事,皇上是开明的”的可耻洗地逻辑。改革开放后,“前三十年”将毛泽东塑造为“伟光正”圣人的崇拜模式结束了(虽然近些年又在冒起),取而代之的是将毛一些逸闻、个性化的言论加以编排,塑造一种平易近人、高瞻远瞩、棱角分明的形象,并巧妙回避他的巨大罪恶,以吸引不明全貌者对其的喜爱甚至崇拜。不得不说,这种描写方式很有迷惑性,远比“伟光正”、“高大全”的形象能俘获当代青年的人心。至于描述的对部分科学家“重点保护”,同样是洗地的惯常手段,在屎坑里捡米粒,歌颂“皇恩浩荡”,把责任都推给“阴谋家”。
何况,实际上研发两弹人员在文革中也并未幸免,同样受到了残酷迫害,一些科学家如姚桐斌被打死、赵九章被迫自杀身亡,“两弹元勋”邓稼先及其他许多参与工作的科研人员也遭批斗,《三体》中的描述是公然的篡改历史。同样,根据相关史实,毛也不可能对两弹领域做出那样“开明”的批示(周恩来有过相关保护,哪怕也不是一开始就保护而是发生了科学家被打死、自杀事件后),这段所谓“批示”也形同捏造(毛确实在其他事情上做过类似语气的批示,但一不能掩盖其滔天罪恶,二不能说明他在两弹事情上也这么做了,而且史实明确证明他没这么做)。文学作品当然可以有合理虚构,但是在涉及到具体的真实历史事件时,必须与基本事实相符合,否则就是在篡改和捏造。
刘慈欣在书中正是使用了这些手法,不仅将毛的滔天罪恶勾销,还赋予毛一种开明、务实、去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这样,刘慈欣的《三体》虽提到了文革的残酷,却不仅没引导反思毛的极权暴政,反为魔头增色、为黑暗年代贴金。这同样与当今许多不明真相的青年崇毛合拍,使得《三体》即便提及文革,仍然获毛粉众多的青年人好评。
刘慈欣这样描绘文革,某种程度比那些在作品中回避不谈文革的作者更可恶、影响更坏。借用毛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刘慈欣对那段历史的刻画很像“表面反红旗实际反而在打红旗”或者说“小骂大帮忙”,看似讲文革惨剧,实际上却在为相关责任人开脱,用高超的写作方式不回避敏感却得出相反结论,让人在知晓文革残酷的情况下,还觉得毛等人真是开明和无辜的。显然,这也正是该书对涉及文革的情节没有大量删改就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的原因。
书中还有段落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刘慈欣对毛的肯定态度,如联合国希望罗辑搬到一个更符合面壁者这样重要人物身份的居所时,罗辑说的话:
“知道西柏坡吗?离这儿不远,那是一个更小的村庄,两个多世纪前,这个国家的创始人曾在那里指挥过全国的战争,那些战役的规模世界罕见。”
从本段语气及结合上下文,又可以嗅出那股令人作呕的毛粉味。这个“国家创始人”的思想、政策和行为杀害和致死了数千万人(包括刘慈欣老家河南几百万人,且大多数死难者正是刘的籍贯地罗山县及该县所属的信阳市(当时叫信阳专区)的居民),破坏了成千上万乃至难以计数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也让中国陷入长达数十年的专制酷政,平民百姓权利丧失,弱势群体苦不堪言,这遗毒迄今犹存。毛泽东创建的这个窃取了“中华”之名、人民也不掌握权力和拥有权利、更无“共和”之实的国家,让十多亿乃至累计数十亿国民生活在有形边界和无形高墙构筑的世界最大监牢中。但刘慈欣不在乎这些,当今的既得利益阶层也不在乎这些,他们享受着优越的物质和非物质供给,再为骄奢淫逸披上爱国主义、宏大历史叙事的外衣,为大魔头兼民族罪人而自豪。这不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症状,更是奴才心理的典型表现。
当然,有人会以“当今中国是专制政治,刘慈欣是不得已”为之开脱。但是起码他可以使用中性词汇描述毛泽东及相关内容,而不是以赞颂方式描绘。这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可以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刘慈欣的这种赞颂是非常值得被批判的。
(值得提及的是,这部分还有一段内容,是在讲毛否定那段极左言论后,又让人撰写了一段向外星发射的信息,内容如下:
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
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我们珍视这一切。
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
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文明。
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这样一段话又是粉饰文革、为毛贴金的。事实上,文革中那种政治狂热下,更可能的是原来的极左狂热分子编写的那样:
收到以上信息的世界请注意,你们收到的信息,是地球上代表革命正义的国家发出的!这之前,你们可能已经收到了来自同样方向的信息,那是地球上的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发出的,这个国家与地球上的另一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企图把人类历史拉向倒退。希望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谎言,站在正义的一方,站在革命的一方!
这恰恰最符合文革时期的政治辞令、外交辞令。刘慈欣故意编写这两段内容及对比展示,意在讲“毛和政权并不坏不疯狂,疯狂的只是下面一些人”这套为文革辩护的旧伎俩。但是这种旧伎俩的确屡试不爽,且在刘的艺术加工下更能以假乱真,对于对那段历史史实并不特别清楚、只是一知半解的人,特别有迷惑性)
(三)叶文洁、绍琳和女红卫兵
刘慈欣本人及其作品《三体》都有很强的厌女情结。文中的反派人物或搞坏事情的,普遍都是女性;而拯救世界的,则都是男性(当然也有例外,但是大体如此)。其他人放在以后再说,现在只谈叶文洁及与叶文洁有关的人物绍琳、女红卫兵。
刘慈欣对叶文洁这个人物,刻画的还是很入骨的。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述叶文洁遭遇的种种迫害,如因文革丧父失母、被政审干部虐待、被记者白沐霖背叛等,塑造了一个苦大仇深、对人类充满怨恨与不信任的女性形象。刘慈欣一定是在现实中了解、接触过这种受害者,或者研究过相关历史档案、新闻资料,才能将叶文洁这样的人物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如前面提到的对炸弹女孩的刻画那样,刘慈欣显然对社会的受害者筹划报复社会的行为颇有研究。
不过,不像对炸弹女孩那样的鄙夷与厌弃,刘慈欣对叶文洁这个人物施以了一定的同情。但根本上,刘慈欣还是将叶文洁这样的时代受害者归为毁损主流社会秩序的人。刘虽然对叶这个人物多了同情的笔墨,但仍是站在主流社会、平叛者的角度来看待叶的,也就是他绝不会称颂受害者、弱者的反抗,反而在提醒世人提防这样的人。在刘的笔下,叶文洁残忍害死丈夫杨卫宁和领导雷志成,引三体祸水涌向地球,归根结底是个罪人、大罪人。单独看《三体》或许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和契诃夫、莫泊桑、巴金这样作者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抗争的讴歌比起来,刘慈欣对受害者的刻薄、对秩序的维护就无比明显的体现出来了。书中叶文洁被一个政工干部在冬天泼了一身和一被子冷水,刘慈欣同样在用笔往弱者心肝里注入冷水。
在刘慈欣笔下,叶文洁以给罗辑讲宇宙社会学的方式做了救赎,随后就被拘捕和审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于叶文洁所受的创伤,都归咎给了白沐霖等个体,而不会上升到制度与政权乃至文化与社会结构。即便书中恍恍惚惚提及了时代的大背景、人们在政治风暴大环境下的无奈,也谨守不涉及批判历史现实的红线。呐喊、反思、声讨,是万万不会碰的。
而且,纵观全书,可以合理假设,刘慈欣是将叶文洁引三体力量“改造”地球,暗喻为中国的社会受害者引美国的力量入侵。或者,至少其他人对此可以合理的这样理解。在《纽约客》一位华裔美国记者采访刘慈欣的文章中,就提及了对相关情节的这种理解。根据这样的暗喻推论,刘慈欣挞伐ETO引三体入地球,也就是在抨击一些“带路党”,或者说把中国自由派强行当成“带路党”,也是刘及《三体》得到中国既得利益群体追捧的一个原因。
刘慈欣刻画的另一个反面女性人物,是叶文洁的母亲绍琳。这个女性人物的形象负面,不仅背弃夫妻情分批斗自己丈夫(而且还睁眼说瞎话,作为物理学专家否定被公认的物理定理),还很有心机的勾上一个下放干部,得到荣华富贵后又和新丈夫一起疏远离弃叶文洁。这种情节在文革中应该并不鲜见,甚至说在许多灾祸发生时都不鲜见,刘所写的是一种事实的再现。但是问题是刘将女性这种迫不得已的自保丑化,暗示女性的忘恩负义。而且,这文章(也包括刘慈欣任何其他文章)中从没有出现男性对女性始乱终弃的人物形象,相反有罗辑那样看似玩世不恭却对妻儿非常忠贞和爱护的男人形象。当然,一部著作是没必要必须在性别议题上刻意保持平衡,但是文由心生,结合刘慈欣全书及其日常表现的价值观,有充足理由相信其是带有性别偏见的。
文中刻画的那三个女红卫兵,更能体现刘慈欣的厌女情结。文中特意写了三女两男五个红卫兵,三个女红卫兵是中学生,两个男红卫兵是大学生。三个女中学生红卫兵非常狂暴野蛮,完全不讲理,只会用口号否定叶哲泰基于事实的辩驳,然后将叶哲泰打的皮开肉绽,最终死去。而男红卫兵反而“对老师(有)一丝残存的同情”,并且在三个女红卫兵将要打死叶哲泰时喊出“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呃,这里又一处为毛辩解的)试图阻止悲剧。
文革中的确有不少狂暴的女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女性,打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就是以宋彬彬为首的一群女学生。除此之外,也有许多女红卫兵、造反派打人虐人杀人的记录,如季羡林就忆述女性造反派头目聂元梓指挥造反派迫害北大师生。青年和少年女性的狂暴,以及一些跻身红卫兵、造反派领袖的女性各种暴行,为杨继绳等正史学者特地提及,并诧异于女性尤其青少年女性的这种疯狂。在文革最激烈的首都北京及某些场合,女红卫兵的确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破坏力,其暴行也是有目共睹。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等暴力运动中女性比男性普遍更加残暴、反智。相反,文革中大多数打人杀人者仍然是男性,这同样有大量事实证明,尤其涉及各种变态凌虐的,大都是男性做出的。如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提到的大多数暴力案例或事件,都是男性做下或者主导的。而女红卫兵的暴力之所以非常引人注目,很大程度在于其暴虐举动与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位及暴虐前的表现形成巨大反差,比施暴的男性更不符合社会原有的期待,所以就显得更为突出和特异。这恰恰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和约束,让女性哪怕做一些和男性一样的糟糕行为,都会得到更多异议和谴责。当然女性的暴力也确有独特之处及某些时刻某些举动比男性更加激进狂热的情况,但是如果以此形成“女性更暴力更狂热更易被煽动”的印象,那就是进了男权主义建构的意识巢窠中了。或者说,即便这是部分时候存在的某种不应该剥离背景的现实,但也不应该以传统的偏见视角去评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