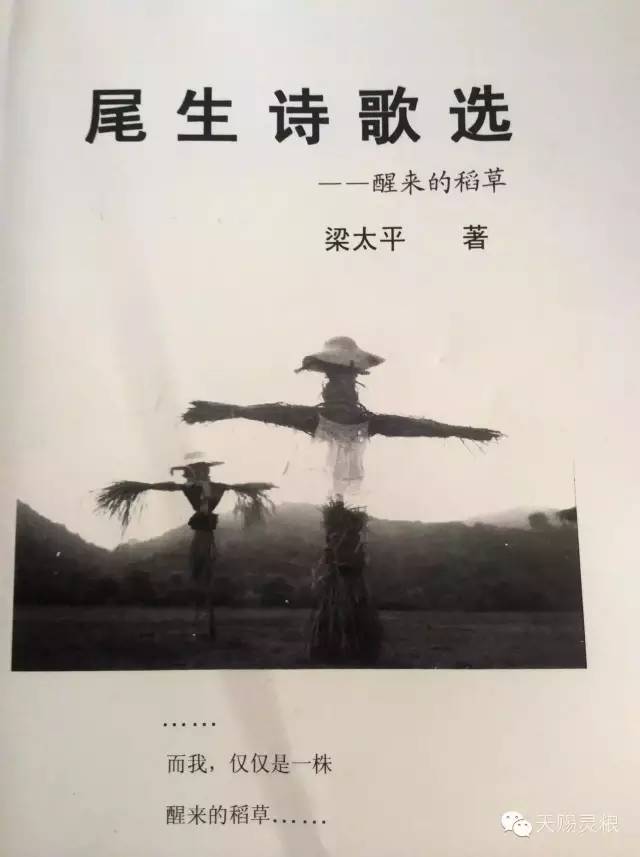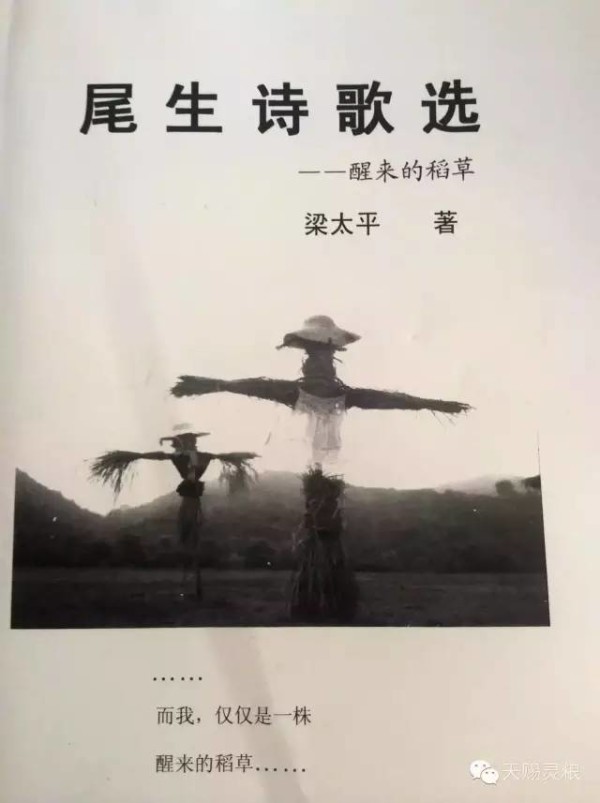 青年诗人梁太平,笔名尾生,《醒来的稻草——尾生诗歌选》是他自选自印的一本诗集,封面素雅,排版简洁,整个白纸黑字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让人一看就觉得喜欢。书名“醒来的稻草”即取自书中的一首小诗:“一株醒来的/稻草已经醒来了/他茫然四顾不知如何/我只是一株醒来的稻草/镰刀,在流血的/旗帜上挥舞它的镰刀/而我,不过是疼痛里/醒来的一株稻草……”(尾生诗歌:《醒来的稻草》)
青年诗人梁太平,笔名尾生,《醒来的稻草——尾生诗歌选》是他自选自印的一本诗集,封面素雅,排版简洁,整个白纸黑字散发着淡淡的油墨香,让人一看就觉得喜欢。书名“醒来的稻草”即取自书中的一首小诗:“一株醒来的/稻草已经醒来了/他茫然四顾不知如何/我只是一株醒来的稻草/镰刀,在流血的/旗帜上挥舞它的镰刀/而我,不过是疼痛里/醒来的一株稻草……”(尾生诗歌:《醒来的稻草》)
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中国社会并未随同科技的发展变得开放和包容,自由的空间日渐逼仄,从言说到写作,到处壁垒森严。然而,那些大专院校中格式化出来的年轻人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就不知道什么是“人类末日”或“社会危机”,随着“人民”的持续“币”化,他们要么自宫着奔走在报考公务员的路上,要么高唱着“没有祖国什么都不是”的腔调攀附朝廷,更多的则挥霍着过剩的青春把玩着手机和电脑,在各种虚拟的游戏中蠢蠢欲动或麻木不仁。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年轻人,他们克服恐惧,三三两两地走上街头,在广场、车站、地铁路口、人群密集的地方,拉横幅,举牌,演讲,公开表达自己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诉求。梁太平就是这部分年轻人中的一个。
梁太平原本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230所(长沙)的一名地质勘探工程师,属于国企高薪族中的一员,因为参与这些公民活动,2014年遭单位恶意开除。失业的日子是艰难的,此书近两百首诗作即记述着作者失业前后诸多的观察和思索,诗中充满了前进、犹疑和决断,时而得蒙光照心生喜悦,时而陷入黑暗忧心忡忡。在“醒来”的主题下,从悬崖上的野花、阴暗处的竹笋、笨拙的飞鸟、橙色的飓风、无辜的镜子、金黄的麦田,再到雨滴、霾、火、以及蚂蚁与阳光,在阴沉黯淡的社会表面,他不断地寻找和发现着每一丝微小的亮光,并赋予着更多的信心和热望,以致不厌其烦地自我宽慰和鼓励,“当良心在监狱里跳动/坐牢成为一种骄傲/恐惧正在退却/天就要亮了”(尾生诗歌:《天就要亮了》)。
“镰刀”本是一种用作收割稻麦的农具,然而在人类文化史中却是一个恐怖的意象。早在希腊神话中,天神克洛诺斯就是用镰刀割下了其父原始神乌拉诺斯的生殖器。而代表时间流逝的“死神”克洛诺斯也是手持镰刀作为武器。尤其上个世纪以来,众多共产国家将镰刀画上血红旗帜作为专政的象征,于是,阉割和杀戮扑面而来,杀人如草不闻声,成千上万的生命在无声无息中湮灭,化为泥土和灰烬。莫道春风吹又生,莫道人贱命强,稻草割了一茬又一茬,刮地三尺,连根拔尽,直至污水横流,山荒岭秃,人间沦为地狱,街市变作鬼城。没有任何“一株稻草”——单一的个人——能够独自抵挡或幸免,看着都令人蛋疼,令人胆颤心寒。
中国诗人对“草”常常情有独钟,如屈原以“芳草”自喻,时刻流露着对君王缠绵悱恻的忧虑和怀想;千年而后,这“草”终究在“镰刀”的“挥舞”中“醒”了,这是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而我,不过是疼痛里/醒来的一株稻草”,仅自己醒来是不够的,还需唤醒其他沉睡着的,以及装睡的同类。告诉他们,即便自己的身躯最卑微也有着微小的重量,而这重量只要不断地叠加累积,骆驼,这头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终会有被压垮的一天。而如果继续沉睡,则必然承受践踏、腐烂或被烧掉的命运。抗争,一个觉醒者必然的抉择。为揭示公权的营私舞弊的伎俩,也为公正起见,梁太平选择了湖南省人社厅申请劳动仲裁。
彻底被开除公职,“梁太平”名正言顺地成为了一名不受政府欢迎的“异见者”,一个世俗人眼中的“失败者”。作为一个基督徒,他颇为平静地接受着这些不公的对待。做出开除决定以及维持这个决定的人或所谓领导并非愚氓蛮众,他们一方面要执行当局的职权,一方面又害怕历史的清算或良心谴责,以致前后矛盾言不由衷。这恰如耶稣作为受难者的翻版。对于一个诚虔的诗人来说,信仰就是在缓慢和疼痛中寻找生命出口的过程。他显然是找到了,在《并不后悔》中,他写道:“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道/你就不会再问我什么了”。正如布鲁克斯评论弥尔顿的《失乐园》时所说的:“诗人努力给亚当和夏娃在乐园中一个最有意义的生活,但只有在悲剧的结尾,当他们被赶出乐园,才面临艰难不幸的但最有意义的生活。”
在一个如此道德沦丧,精神贫乏,各种丑闻迭出的时代,“诗人何为”?这不仅是荷尔德林地惊世之问,同样是梁太平无法绕越的问题。写作,这不仅是一项向黑暗和不公主动出击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成为他寻找答案的路径。梁太平失业后,开始了不间断地创作诗歌,几乎一日一诗。在对律师谢阳的思念和颂扬中,他写道:“公义不在法庭/公义在荒野里游荡/公义不在人心/公义已被人心所埋葬/这是一个日落的时代/然而你,像一个无药可救的病人/却执意走在了追逐日出/公义的路上……”(尾生诗歌:《致谢阳律师》)谢阳是他委托的代理律师,那天谢阳谈起这个仲裁案时还满怀信心,认为其单位如此弄虚作假违规处罚必败无疑。然而,7月10日便发生了震惊天下的“维权律师大抓捕”,谢阳被定点监视居住,成为煽颠犯嫌疑。虽然谢阳缺席辩护,仲裁案庭辩中被申请方仍在种种证据面前理屈词穷,但这些并不能改变结果。日前,人社厅违悖常情地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将这个怀着“宪政梦”的年轻人像一根肉刺一样从体制内硬生生地挤出。
谢阳是一名优秀律师,由于对司法的暗箱操作充满着种种担忧和疑虑,以致成为知名的“死磕”派律师代表。谢阳被捕后,长沙市公安局曾找多人问话,调查核实谢阳某次在法庭上有没有骂过某官员是某党的狗。作为律师,谢阳毫不讳言他的政治追求,他一句为人熟知的话就是这样说的:“你不允许我在法庭上抗争,我就把抗争摆上街头。”都是时代的勇者和义士,通过诗歌的语言,梁太平把抗争摆上自己印制的书页,摆上各种可能的网络平台。2013年1月,梁太平在参与声援《南方周末》的街头运动中被抓进了广州越秀派出所,关押当中,他写道:“他们把我推进一扇门/他们把我推出一个世界/”“四面虚白的墙/吞噬掉时间/我看那光,祷告/你的审判何时降临”。(尾生诗歌:《你的审判何时降临》)这读起来令人血脉贲张的诗句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荷尔德林的句子来,“待至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勇敢的心灵像从前一样,去造访万能的神祗。”诗歌之所以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这与诗人总是在专横的权力层面破除缄默而成为新的发言人息息相关。审判和公义从来就没有亦步亦趋,甚至背道而驰。
无权者的权力难道仅只能在神话故事中得以伸张吗?祷告、诅咒,抑或屈服、妥协,种种现实的窘况让诗人遭受着无情地撕扯。不仅房贷无着,连日常餐食都难以为继,梁太平从优裕的中产阶层一下坠落到社会底层。其实事情也并非毫无回旋的余地,条件是按当局的要求进行认错和保证,但他显然是拒绝了。“这种或那种野兽之所以能幸免灭绝,是因为它们具有躲藏的本领和能力。”维特根斯坦在笔记中写道,“当然,我并不以此作为称赞这种能力的理由,绝对不。”现代社会中,我们人比动物更不堪,所谓“委屈求全”或“忍辱负重”无不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对于既得利益,一方面沾沾自喜,一方面又讳莫如深。而对一个有着纯洁信念和坚定理想的人来说,任何与邪恶的妥协或同流都会让他无法忍受。何况在种种事实中,所有人性的不堪和苟且都将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纤毫毕露。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在精神上有着洁癖的人。
梁太平因为“醒来”而被开除。成为“异见者”,这是他自我选择的结果。在专制国家,异见者的遭遇是严酷和荒唐的。在前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就曾被官方判为“社会寄生者”而处以国内流放,去边远地区集体农场强迫劳动。到1972年,布罗茨基已三次入狱,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其作品只是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国内流传。甚至在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布罗茨基被当局塞进一架不知飞向何方的飞机驱逐出境。不过,梁太平却是想出境而不得,作为潜在的“危害国家安全者”,他屡次在机场的边检处频遭阻挠。尤为可笑的是,他被开除后首次远游上海,竟然遭到警方拦截并强迫乘坐飞机头等舱返回居住地。他不再有机会随地质勘探队出没于崇山峻岭、荒滩沙漠、丛林沼泽寻找矿藏了,但诗歌会陪伴着他走遍大地,因为布罗茨基说过,“一个阅读诗歌的人比不阅读诗歌的人更难战胜。”历史终会如大浪淘沙,在对人们量的存在进行了简化和取消后,一个庸人与千万个庸人是毫无区别的,而一个诗人永远是一个诗人,在时间的围猎中,他会如黄金钻石般愈加璀璨夺目,这也就是作为“一株稻草”“醒来”之后的价值所在。
2015年9月20日
来源:微信